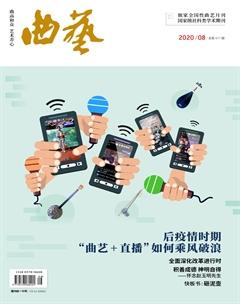曲藝直播是“生活中曲藝”的呈現與展開
耿波
一、直播是全面展開的媒體形式
從演出形式而言,近代以來,曲藝演出的載體有幾次變化:民國時期的演出形式以“撂地”為主,就是曲藝表演者拿漢白玉石粉在街頭邊撒邊念叨,以此“黏人”,然后展開表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曲藝演出慢慢走上了“舞臺”,這些舞臺包括劇場、體育場、廣場和一切有儀式性的場合,與曲藝演出舞臺化同時進行的是廣播、電視也成為曲藝的傳播媒介;在20世紀90年代,不少曲藝演員有感于曲藝上了“臺”卻遠離了觀眾,所以恢復了小劇場。截至現在,全國的演藝市場應是舞臺、廣播、電視、網絡與小劇場并行,而在這其中,效果最好的,還是小劇場。
事實上,曲藝演出在網絡上呈現已不是新鮮事,但大部分是錄播,主要借助網絡載體。2020年2月起,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小劇場舞臺等形式被全面禁止,曲藝網絡直播的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目前,杭州滑稽藝術劇院、上海評彈團的直播,還有演藝團體嘻哈包袱鋪從2020年4月開始的一系列直播等,影響比較大。另外,在網上還有一些個體曲藝行為的呈現,較為著名的比如西北藝人張尕慫在網上的演出等,網絡平臺基本是抖音、快手、嗶哩嗶哩等。
對曲藝演出而言,不管是觀眾還是演員,大家其實對“面對面”的演出更熱衷,對演員而言,面對觀眾,演起來其實是特別“有感覺”的。此次疫情來勢洶涌,應該說是它逼著曲藝與直播相遇了,那么,直播這種媒介是什么呢?
從傳播的角度看,如果說,網絡錄播主要借助網絡本身的彈性形式的話,直播則大不一樣,它借助網絡,卻有著與其他網絡播出形式完全不一樣的特點。曲藝直播就是曲藝演出通過網絡直接播放出去,從原則上來說,直播拒絕剪輯(盡管在國內的直播中也有剪輯的情況)。如果是舞臺演出,演出的作品會經過演出人員的精心組織,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個美的成品,如果出現了紕漏,觀眾就會不認同。而直播不是舞臺演出,雖然它同樣可以給觀眾完美的作品,但它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以作品為中心延伸開去的呈現形式,這種呈現形式中可以有:訪談、談論作品,甚至是后臺化妝等。如果曲藝的舞臺演出是“點”的話,曲藝直播則是“點—篇”,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也是曲藝直播的魅力所在。
所以我們可以說,直播是全面展開的呈現形式,曲藝直播與曲藝的舞臺呈現不是一回事,這是我們做曲藝直播要注意的事情。
二、曲藝遇上直播是曲藝的生活化
曲藝遇上直播,是不得不做的事情。當曲藝開始直播時,絕不僅僅是改換傳達載體的問題,它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曲藝的呈現形式。
以2020年6月上海評彈團主辦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直播專場的直播為例,我認為提供了很好的經驗。上海評彈團的這次直播,主線仍然是評彈作品,各位大師在鏡頭前的彈唱,一絲不茍,與平時的舞臺演出沒有區別。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作品之間,則是主持人對演員的訪問,或演員與演員之間的對談,或者是演員對某個作品的賞析,“作品+評論賞析”構成了整個直播的形式。這種形式雖然不算創新,有點類似于晚會的形式,但放在網絡直播中,卻是很恰當的。
然而,從直播的角度看,這場直播還是有問題的。正像我們說的,正常直播應該是從作品擴開,但這場直播還是像晚會。直播從演員的結對入場開始,從做派、言語很明顯都是精心準備好的。包括節目之間交叉的訪談與采訪,很明顯太精致了,少了隨意與日常。直播的魅力在于呈現作品本身的質感,也就是作品周邊的全面生活場景,從這個角度看,上海評彈團主辦的這場直播的確是邁出了可貴的一步,但并沒有把握好這一關鍵。
杭州滑稽藝術劇院的直播內容稍微放得開了。杭州滑稽藝術劇院直播的優點在于,沒有丟掉作品,作品仍然得到了完整的傳達,這一點很重要。在作品呈現之外,他們的直播還呈現了演員的化妝、閑聊等,作品展現周圍生活場景的尺度比較大,因此也比較吸引人。但是,杭州滑稽藝術劇院的直播仍然不能說是完美的,整個直播中,主辦單位沒有放下以前“國營劇團”的架子,表演得一板一眼很有尺寸,但也削弱著直播的魅力。
嘻哈包袱鋪是較早涉足直播的曲藝團體,表演很放得開:他們直播的形式沒有確定的線索,相聲、小品、滑稽戲等各種曲藝形式層出不窮,作品的完成度不高,但是包袱密集,笑聲不斷,使人聽得淋漓酣暢。個人認為,嘻哈包袱鋪的直播目前來看是相當成功的。
然而,嘻哈包袱鋪的直播也給我們提出了問題:我們知道,曲藝直播要想取得好效果,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直播的尺度放得越開,越能與觀眾打成一片,效果越好,但如此一來,曲藝網絡直播與咯吱觀眾有什么區別?所以,曲藝直播不能與舞臺表演一樣只是直播需要注意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曲藝直播又不能完全和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一樣,關鍵是呈現的尺度問題。下面我詳細論述這個問題。
三、直播中的曲藝不能丟了“魂”兒
曲藝直播不僅是換了載體的媒體呈現,當曲藝進入直播后,它要求曲藝突破以作品為中心的呈現形態,從作品擴展到生活,將“生活中的曲藝”呈現給我們,這是曲藝直播的最大魅力。
嘻哈包袱鋪等曲藝團體的直播,效果火爆,然而我們的疑問是:曲藝直播要展現立足其中的“生活”,但它是不是與生活本身完全一致就是最好的?
是從2008年以來,隨著各種曲藝綜藝節目的播出,曲藝尤其是相聲、小品與滑稽戲等開始有了巨大的受眾面。然而,隨著曲藝熱潮的到來,在這個消費時代,曲藝與笑聲聯系在了一起。為了能夠逗大家發笑,有些曲藝節目無所不用其極,倫理哏等原先在曲藝前輩那里可以避開的話題,現在卻在臺上出現。
曲藝首先是藝術。曲藝藝術在近代以來,經過曲藝大師的精心錘煉逐漸變成了美的藝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欣賞曲藝才是美的享受。然而,在消費文化的今天,曲藝是不是可以不作為“美”的形式,而是只作為引人發“笑”的形式就可以?如果是這樣,曲藝為何存在?一人一把癢癢撓就行了。
曲藝直播時代,仍然要堅持作品中心,堅持呈現美的、完整的藝術作品,這就是曲藝的“魂”兒。曲藝直播的核心,是要呈現出作品的生活形態。作品是中心,生活生態是周邊,兩者不僅是中心與邊緣的關系,也是高與低的關系,作品是高,生活是低。曲藝直播中的生活呈現應該有作品的維系,一切都是為了完整度很高的作品。
曲藝直播的時代,也是消費主義泛濫的時代。對曲藝作品而言,曲藝的“生活”在哪里,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曲藝演出中,完整的作品呈現和它所展現的生活其實是向兩個方向努力的,完整的作品遮掩它的生活,而生活卻是散漫無序的,完全看不出作品的影子。我們一般認為,曲藝是與現實生活中的人情世理相關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它基本的價值觀,因此,我們欣賞曲藝時,感覺它既離生活近又離生活遠。然而,在消費文化鼓動下的某些曲藝著意夸大其中的某些環節——按照行話說就是“絕活”,以此贏得最好的演出效果。在當前的曲藝直播中,我們看到了這種現象,而且越是受歡迎的曲藝團體,在直播時越熱衷于展示“絕活”,直播效果不錯。
但是,這樣在網絡直播中呈現出來的曲藝是“生活中的曲藝”嗎?它對人情世理精到的觀察與表達到哪去了呢?我們看這樣的曲藝直播作品,當時覺得節目效果不錯,然而,直播結束后能留下什么呢?這都是我們應該深思的。
曲藝直播的本質應該是“生活中曲藝”的呈現與展播,直播能逼著我們去發現和呈現曲藝的“生活之根”,讓曲藝演出具有質感,但也有可能讓我們把消費文化誤認為了生活,這就很成問題了。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