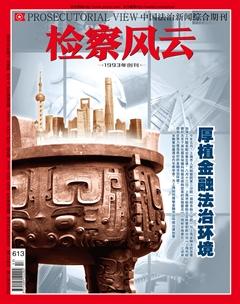不畏首,畏尾
王文昌

庚子鼠年與新冠疫情一起到來。百無聊賴,我一邊防疫,一邊重讀蒲松齡《聊齋志異》。每每讀到佳處,常有“浮一大白”的快慰,暫時忘卻洶洶疫情,自得其樂。
一日午睡之前,讀《董生》一章,其中的一句“不畏首,畏尾”,盤桓腦際,思緒聯翩,總有一吐為快的沖動。故事始于一個冬夜。董生展被于床,獨自赴友人處飲酒。夜半始歸,發現有人睡在自己的床上,點燈之后發現“竟為姝麗,韶言稚齒,神仙不殊”。董生大喜,“戲控下體,則毛尾修然”。董生大懼,轉身想要逃走。床上美女一把捉住董生,責怪董生何以如此。董生說:“我不畏首,畏尾。”美女嫣然一笑,“引董生復探,則髀肉如脂,尻骨童然”。董生大喜,心想是不是自己剛才“適然之錯”,眼前不是一個明眸皓齒的美女嗎?于是凡心大動,“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最后的結局,是董生不能自拔,“漸羸瘦”“吐血斗余而死”。
故事有點俗套,我獨喜董生初見美女的話:“我不畏首,畏尾。”畏首畏尾是一個貶義詞,出自《左傳·文公十七年》:“畏首畏尾,身余其幾?”形容膽子小,行事顧慮重重。蒲松齡很俏皮,賦予了它全新的含義,真是嘆為觀止的造句高手。
狐貍迷惑人,總能幻化出天生麗質,但是不經意間,會露出“尾巴”,那是本性,所謂本性難改。董生開始已經看到了這條“尾巴”,但是尾巴隱藏起來,“神仙不殊”的外貌讓董生不能自持。只見其“首”,不見其“尾”;不僅不“畏首”,也不再“畏尾”。接下來就是坦然與其共度良宵,樂此不疲了。
近日到佛教景點檢查防疫工作,一位七旬老僧說了一句話:“俗人畏果,菩薩畏因。經歷這場人間浩劫,我還是希望眾生多結善緣。”老僧口中的因果與董生的“不畏首,畏尾”不是有著天然的聯系嗎?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人們開始反思。我們做錯了什么,讓疫情如此瘋狂地報復,甚至連一年一度的春節都不得安生?也許是我們太恣意了。當我們把一個個新奇的野生動物按到砧板,開膛破肚,煎炒烹炸,端上餐桌,大快朵頤之時,怎能想到有朝一日,新冠病毒會氣勢洶洶地向人類清算?莎士比亞早就告誡人類:“這些殘暴的歡愉,終將以殘暴結局。”災難來臨,它和我們每個人有關,正如雪崩發生,每一片雪花都不能置身事外。
歷史不能忘記,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引用了一個案例,同樣值得警醒。住在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為了獲得耕地,砍光了北坡的樅樹林,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山泉在一年之內大部分枯竭,雨季到來,兇猛的洪水傾瀉而下,良田被毀,平原變成了沼澤,一片汪洋,美好的愿望最后演變成了災難。
“畏因”“畏尾”,是一種修煉,是一種眼光,是一種品質。曾有一個人拒收老板的貴重禮物,人們稱贊其品德高尚。這個人說了一句話:“我不收老板的東西,不是我有多高的思想境界,我是膽小,是‘怕,怕法律會找上門來,收了這點東西,我進了監獄,不值。”試想,有幾個人收錢的時候就想到監獄,想到人財兩空?
看到“尾”,很難,需要智慧;堅持正確的選擇,更難,它需要的是定力和勇氣。“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享樂慮及健康,則節制”。眼光放遠,會阻止許多看似正確卻十分愚蠢的事情發生。讓所有的開始都停一下吧,想想結局,想想后果,想想“尾”,三思后行。
畏首畏尾,不好;不畏首,畏尾,未嘗不好。
萬眾一心防“新冠”,靜下心來讀“聊齋”。讀讀“聊齋”,不僅可以緩解焦慮,還可以思接天外,嚴防“心疫”,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事情。
圖:劉昌海? ?編輯:夏春暉? 38675320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