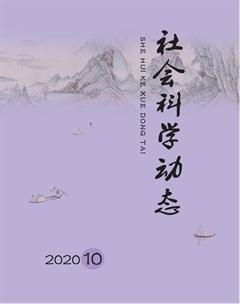論新世紀鄉土小說農民現代 體驗的“后尋根”轉向
摘要:“鄉下人進城”是新時期鄉土小說最突出的敘事主題,表征了農民追尋現代化的坎坷歷程。進入新世紀,鄉土小說呈現出與歷史反向、與現實同步的嬗變:書寫農民以“還”“歸”“尋”為主旨的“后尋根”現代體驗與實際行動,這是新世紀鄉土小說的新動向。小說里,農民在“后尋根”中化被動為主動,在平和、理性、現代意識的主導下,展開了新一輪“尋根”:尋土地之根、鄉村文化之根、“通體社會”之根、生態文明之根。新世紀鄉土小說中農民現代體驗的“后尋根”轉向,既體現了農民在歷經40年改革開放后對“進城”的重估、反撥以及主體的成長、人格成熟,也彰顯了新農民尋根扎根鄉土,以及鄉村振興的需要。
關鍵詞:新世紀鄉土小說;農民;后尋根;現代體驗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轉型視域下新世紀鄉土文學與農民現代體驗研究”(15BZW042)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0)10-0005-09
1990年代之后,新世紀鄉土文學逐漸從過去一味地吶喊、彷徨、訴苦、身份猶疑、城鄉怨憤發展到對土地、鄉村文化小傳統、生態等的清醒反思與體認,農民的情感嬗變和生命體驗在歷經40年的現代性櫛風沐雨,負面的怨恨情緒、對立的城鄉矛盾等漸漸趨于平和、理性,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新一輪的“尋根”:尋土地之根、鄉村文化之根、“通體社會”之根、生態文明之根……新世紀鄉土敘事中,如《戶口還鄉》(鐘正林)、《尋根團》(王十月)、《衣缽》(李耳)、《在天上種玉米》(王華)、《胡不歸》(侯波)等小說,不約而同地抒寫了以“還”“歸”“尋”為主旨的“后尋根”焦慮與實際行動。孟德拉斯曾以法國農民的變遷以及法國鄉村社會的“起死回生”,描繪了這個尋根成功的轉型:“10年來,一切似乎都改變了:村莊現代化了,人又多起來。在某些季節,城市人大量涌到鄉下來,如果城市離得相當近的話,他們甚至會在鄉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來了,一個擁有20戶人家和若干處第二住宅的村莊可能只有二三戶是經營農業的。這樣,鄉村重新變成一個生活的場所,就像它同樣是一個農業生產的場所。”① 當然,我們無法與孟德拉斯筆下的西方鄉村做簡單的比附,鄉土中國仍然具有自身強烈的色彩和個性。筆者將新世紀鄉土小說中這種集體無意識的、在歷經40年的現代化追尋之后重新對鄉土尋根、反顧的集中抒寫稱為“后尋根”,以示與1980年代“尋根”的區隔。筆者認為,這類鄉土小說映照鄉土敘事的內涵嬗變和農民現代體驗的全新轉向。
一
丁帆指出,自新世紀前后,“中國鄉土小說的外延和內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何對它的概念與邊界重新予以厘定成為中國鄉土小說亟待解決的問題”,并提出“典范意義上的現代鄉土小說,其題材大致應在如下范圍內:其一是以鄉村、鄉鎮為題材,書寫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其二是以流寓者(主要是從鄉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鄉村之間和城鄉之題材,書寫工業文明進擊下的傳統文明逐漸淡出歷史走向邊緣的過程;其三是以‘生態為題材,書寫現代文明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②。鄉土小說譜系發展到現在,丁帆先生上述“三個階段論”的分期,顯然已經無法延展性地涵蓋近年出現的寫作向度。
筆者認為,晚近的鄉土敘事路徑主要向以下幾個維度掘進:鄉村振興、扶貧攻堅、鄉村文化重建、鄉村生態文明建設、返鄉新農民及新生代農民人物塑造、農民“新國民性”型塑、鄉土“后尋根”等“新主題”。這樣的“敘事轉移”是一個很大的飛躍,它喻示了鄉土文學從難以在現實鄉村中找到創作資源,到幾乎不再拘泥苦難敘事、城鄉對立等“老”話題,而隨著鄉村事業的發展被敏銳的作家們賦予了時代性、進步性、豐富性內涵,其抒寫的重點既有直面當下的鄉村現實,也有耽于鄉村記憶回眸尋根——轉向鄉土精神等更深層次關系的關注與返鄉。正如美國評論家佩里·米勒在1950年代談到馬克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歸來》時曾經說過的:“這一出除根的戲劇——這種復雜事物對單純事物的沖擊,文明對自然狀態的沖擊;這種(多少注定要失敗的)美國對歐洲的抗拒,西方對東方的抗拒,鄉村對城市的抗拒——是美國文學的持續不斷的主題。”③ 當然,文學絕非政治、時代的傳聲筒,既不是無原則的“歌德”,也不是對現實的簡單摹寫,更不是社會學的注腳,其內里必然熔鑄著作家的思考和批判。
新世紀鄉土文學中農民的“后尋根”既是主動選擇也是被動使然,這牽涉到農民群體文化心理和城鄉矛盾、鄉村社會發展等異常復雜的面向。“被動”比較容易理解,那就是農民在“向城求生”的過程中遭遇到無數阻隔,渴望融入而不得,經過痛苦的反思后,開始向大地母親尋根。從我們熟識的小說《人生》中高加林撲倒在地,哽咽地喊“我的親人啊”,到康老犁(王梓夫《向土地下跪》)將土地比喻為老婆,到大學生陶麗(關仁山《紅太陽照樣升起》)畢業后返鄉興農的反思:田園把一切補償給她,自己一意孤行地熱衷于土地是對的,好好感謝它吧,感謝啊!她雙膝一軟,跪在了地上,像個淘氣孩子,雙手深深地插進蓬松的泥土里;再到賈平凹的《一塊土地》寫太爺在世的時候每天要用腳步丈量十八畝地,爺爺甚至貪婪地吃這塊土地的泥土——撲倒、下跪、擁抱、親吻、吃土……這些深具儀式感、畫面感、格式化的動作,仿佛是農民之于土地的標配,表征了異常頑強的土地意象。縱觀新時期以來鄉土文學系譜,農民的精神追求在于不斷的尋根之中,“鄉土”在現代性的追尋中被反復蹂躪、踐踏,又屢屢被悼挽、重用,“兜兜轉轉”成為農民往返城鄉的真實再現。利波維茨基認為,處于現代社會,“我們進入了意義的非神圣化和非實體化的無盡程序,這個程序確定了完全時尚的統治。于是,上帝死了,不是死在西方虛無主義的道德敗壞和對價值空虛的焦慮之手,而是死在意義的顛覆之中。”④ 換句話說,數代農民在從鄉進城到由城而鄉的尋尋覓覓中,不斷地在城鄉兩極之間像鐘擺一樣試圖校準自己人生的指針,渴望能按部就班地跟上時代高速發展的列車,可是,社會轉型之巨手影響操控著這些卑微的命運,他們不得不反反復復地體驗著鄉土意義的幻滅、重構與尋找。
所謂主動,就是新世紀的農民經過現代化的洗禮,初步具備了新的思想、現代觀念,以更加自主自愿的姿態返鄉。這是一種建立在某種自信基礎上的自覺選擇,包含著農民思想的現代嬗變——他們重返鄉村向土地尋根、扎根。鄉愁意識是人類植根心靈世界的本源性的心理機制和普遍性情緒體驗。在希臘語里,鄉愁(nostalgia)一詞含有回家、返鄉和思鄉的意思,是指對故鄉的人、事、物的悲欣交集、欲罷不能的懷慕、渴望。在中國文化語境里,“鄉愁”體現了游子思鄉、羈旅思歸與重返土地母親子宮的自然情愫,體現出人類最難泯滅的本性和返回家園的沖動。新世紀以來,由于社會急劇轉型,飽受頻繁遷移流動之苦之累的農民,開始質疑當下的城市化、工業化,深情懷想傳統穩定的鄉村生活,鄉愁的詞義也“隨之由個人的思鄉擴大為一種集體心理情緒,抽象為一種特定歷史語境下人群的漂泊狀態”⑤,農民開始渴望返鄉尋根、再度扎根。
筆者認為,在農民的根性里,有四個基本維度構建著他們鄉土世界的穩定框架,這猶如“禮義廉恥”的國之四維一樣,農民根性里的四維即土地、文化、人際、生態。土地是農民的皇天厚土,是扎根繁衍與最終復歸的地母之維;鄉村文化是“暗物質”,是他們的精氣神和魂靈所寄寓之維;人際是農民在鄉村通體社會悠游徜徉、得以自我認同的場域之維;鄉土自然生態是區隔于城市的特有標識之維。這四者構成了在鄉與進城農民苦苦尋根的秉性、根性、德性。
二
“‘后尋根是指90年代以來,新鄉土小說對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所面臨的一系列新問題進行的文化意義上的追問與探尋,既包括對于這一時期突顯的精神拔根狀態的關注,也包括小說家主體在新世紀前后所進行的精神文化的扎根。”⑥ 為了區別于此文學史意義的尋根文學,本文借用的“后尋根”概念是指新世紀前后產生的專門抒寫農民返鄉尋根、扎根的鄉土小說,包括農民的精神返鄉之旅和以實際行動進行的“還鄉”的抒寫。值得指出的是,抒寫農民返鄉尋根、扎根的鄉土小說在新世紀還只是零星出現,但筆者以為,這是農民在歷經40年在現代化的追尋之中,在城鄉之間、工農之間、文化之間反反復復咂摸、體驗、比較后做出的重大而痛苦的選擇,雖然未成為潮流,卻預示了農民現代體驗的新規律和新動向,潛在地表明了鄉村振興的光明前景。
新世紀鄉土小說中農民的“后尋根”有四個基本面向。
一是尋土地之根。費孝通用“鄉土中國”這一觀念類型來概括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特征,正是從“鄉”和“土”這兩個具體層面著眼的。“鄉”是傳統意義上的“俗民”,作為生存依托和保障的血緣—地緣共同體,農民之戀“鄉”是對其終生依靠的家、族群體的依戀;而“土”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最首要的謀生手段,在田里討生活的農民是“附著在土地上的”,其生存時的吃用是從土里來,死了也得“入土為安”。⑦ 當代文學中近40年的鄉土小說,總體上抒寫了農民從對土地的“熱戀”到“別戀”再到“失戀”的現代體驗軌跡,盡管如此,大部分農民身上仍然保有一種對土地發自生命根本意義的特有情感歸屬。正如趙園所說:“在自覺的意識形態化,和不自覺的知識、理論背景之外,有人類對自己‘農民的過去,現代人對自己農民的父、祖輩,知識者對于民族歷史所賴以延續、民族生命賴以維系的‘偉大的農民,那份感情。在這種懷念、眷戀中,農民總是與大地、與鄉村廣袤的土地一體的。”⑧ 這實際上說出了人類而不僅僅是農民,現代人而不單單是農民,對于土地尋根意識的穿越時空的亙古本源和精神文化眷戀,這一份生命中的尋根的原始沖動,就算是再過一百年,所有的人都完全現代化了,也無法抹殺。
新世紀以來,農民對土地的態度悄然發生著改變。土地的意義之于農民不再是生命的本源性存在,也不再是精神皈依之所、財富象征之物。土地對于農民而言,僅僅是其作為“現代”農民進行生產的眾多要素之一,與其他的、他們在城市經于擴大視野所見識的諸如技術、秘方、手藝、金錢成本、人力成本、股份甚至知識產權等等一樣,處于同一平等位置,農民會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合理配置這些的生產要素。在這個意義上,農民既看重土地,又理性對待土地——把土地當作多種謀生手段的一種;既不失農民之于“土地”的從內心升起的感情眷戀、生命意識,又因為具有了現代新質素而對土地持一種“職業性”看法,從而拉開了視距,學會以從容不迫的心態看待。“農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工業文明和商品經濟的沖擊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自給自足的自然農業逐漸商品化和機械化,這不僅從經濟關系上和生產力水平上逐漸改變農民與土地那種自然的、直接的聯系,而且必然使農民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逐漸擺脫對土地的依賴和崇拜,引起自然農業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心理習慣、文化內容和觀念意識的改變。”⑨ 20世紀末農民的“逃離廢鄉”化為21世紀初的“戶口還鄉”,古老鄉村再次成為“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熱戀著并充滿“希望的田野”。
早在1990年代,關仁山的小說《九月還鄉》就有了返鄉敘述:靠出賣色相的九月在城市賺了第一桶金,然后抱著改善鄉村、造福鄉村、提升鄉村的念想返回故鄉,在城市的生活使得九月具有了初步的商業頭腦、法律意識,她想成為農場主,想變成一個新農民的代表。但是,九月的還鄉之路并不順利甚至充滿坎坷,實際上她也是被迫而不是懷著自主自愿回到家鄉的。更為關鍵的是,在那個時候進城求生才是鄉村社會的“主潮”。九月的返鄉,有點“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味道,就像是堂吉訶德大戰風車,她得與村霸斗,與村民博弈,與看不見的頑固習俗落后思想斗……無論是動機和時機,都缺乏天時、地利、人和來加以成就,換而言之,當時以九月為代表的極少數返鄉農民實際上是以失敗告終的。但是,這樣的還鄉具有先聲意義,顯現了九月作為新農民嶄新的精神高度,宣示了一個時代的逐漸開啟。
到了新世紀前后,在政策支持和各種紅利面前,農民還鄉漸成潮流,農村戶口又成了香餑餑。鐘正林的《戶口還鄉》強烈地凸顯了這一主題。小說講述了進城后在城里下崗艱難討生活的大田與幫榮夫婦,因為政府在農村實施林權制度改革而產生返鄉的念頭,并為之付出了比當年逃離鄉土阻力更大、更加曲折心酸的努力與代價。大田與幫榮的離去/歸來仿佛是世紀輪回,又像是魯迅筆下的那只蒼蠅,飛出去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原點——造化弄人。在還鄉過程中,大田與幫榮重溫離土“農轉非”時的送禮、找關系、曲意逢迎的過程(點頭哈腰奔波了大半年,蓋了21個印章,農民一生的命運改變就濃縮在那張泛黃的戶籍卡紙片上),兩次折騰都為了同一個終極目標,那就是過上想要的美好生活。所不同的是,今天的還鄉,是基于與在城市生活過后的認真對比,多了一層對鄉村的重新打量和再認識,多了一份理性思考。也就是說,當年拼死進城,認準城市戶口是人上人的標簽,是因為從來沒有對城市生活的切實體驗和生活質感,僅僅是駐足在鄉村遠眺城市,更多的是以想象替代了現實。現在則是在耗盡生活精力想融入城市而不得之后,才生發了對鄉土的思念與尋根。當然,從現實層面看,大田與幫榮的還鄉固然有經濟利益的驅動,尋找的是生存之根,就像他倆最后認識到的:在城里每天都要開支,連上個廁所都要付錢,說是城里人卻沒有工作,說是農民卻沒有一寸土地……但從農民深層文化心理來說,則是農民精神世界的土地根性使然,因為回到了身心自在的農村,“心思兒才算真正踏實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算是從頭開始,如鳥兒歸林魚兒入水”。大田與幫榮在這一圈之于土地的生死輪回中,經歷了向往—離鄉—困惑—覺悟—還鄉的過程,就像幫榮細思起山村常開不敗的野花、青山綠水,后悔“當時自己怎么就沒有這些美妙的感覺呢”?而城里則是“一個巨大的束縛人的牢籠”。
實際上,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點,鄉土喻示著穩固的財富,在隱形意義層面還表征著母性、家園乃至歸宿——“土”“地”象征著皇天后土、大地母親,并由此衍生出家園、歸宿、子宮等終極內涵,且內化為一種無意識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葉舒憲認為,民間宗教習俗中,通過回歸子宮的象征性禮儀活動,生命得以重造。“歸返子宮禮儀所強調的不是生命之終止,恰恰相反,是生命的再造。子宮母體在這里充分顯示著生命源頭的意義”⑩。
三
段崇軒認為,農村社會經過幾十年的戰爭、革命、運動,固有的傳統文化早已破碎和消失,即便有一點殘存也已完全變味。而多年來的鄉鎮化進程,城市文化蠻橫入侵,無情地吞噬和異化這鄉村文化。農民紛紛逃離農村,農村文化棄之如敝履,鄉村成為一個個文化空巢。{11} 當代鄉土文學特別是1990年代之后的鄉土小說,其中的一個譜系就是“廢鄉”抒寫,這個“廢”既是外在土地、生態之廢,更是“精神文化”之廢,關涉到了鄉村生態因為工業化的長驅直入所導致的持續惡化、鄉下人進城帶來的空殼化、農業的凋敝引發的農田撂荒、鄉村小傳統和倫理道德的崩解而凸顯的人心無處安放等等。比如《秦腔》《我們的村莊》《遠逝的田園》《土門》等諸多文本淋漓盡致的揭示和為鄉村全面淪陷所唱的挽歌。廢鄉鏡像是如此觸目驚心,所繪就的就是為鄉村精氣神的失魂落魄以及曾經一度穩固篤定、富有滋養的鄉村文化的變異、坍塌、失落而進行最后憑吊,農民處于文化虛無的真空地帶。因此,尋文化之根是農民自覺不自覺的現代體驗之一。
侯波的《春季里來百花香》寫的就是鄉村文化失根的嚴峻現實,小說主要反映的就是鄉土中國的農民在解決生存與溫飽后,精神文化的空虛以及外來文化(邪教)的趁虛而入。小說的主人公之一紅鞋,是黃土高原上千萬萬普通農村婦女的代表,她精明強干、勤勞質樸,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在家里是頂梁柱,在村里婆姨中具有很強的號召力。但是在豬肥人壯家安之后,人心的安頓成了問題:人們的時間無法打發,生活的空隙缺乏填充,精神沒有寄托,苦楚無處排遣,于是男人打麻將賭博,女人信基督教唱贊美詩,試圖從對時間的消磨和對神祇的皈依中,得到暫時的充實、滿足與安寧。小說還潛伏了一條兩相對照的“暗線”:代表主流社會的村長侯方方,面對村里人心渙散的情況,其官方意志組織不起來一場秧歌賽,反過來求助基督教信徒紅鞋,才勉強拉起一支隊伍;一邊是鎮黨委建設“文化強國”以弘揚主旋律,另一方面是邪教在鄉村大肆拉攏毒害群眾;一邊是派出所警察在村里抓賭,另一方面是鄉鎮干部聚眾賭博安然無恙…… 現實生活中,社會學家所總結的農村新“四害”:賭博、邪教、彩禮、傳銷,在侯方方們的雙良鄉煙山村展現得淋漓盡致,也將古老鄉村文化傳統沖擊得七零八落。
可以說,在這個急劇轉型的時代,作為歷史的書寫者、建設者、繼承者、創新者,農民主動或被動地割斷了與鄉村歷史文化的血脈聯系,鄉村傳統文化、古老的風俗民情仿佛一下子停留在新世紀之交的“站點”而被拋下,成為可待追憶的歷史文物和展覽的文化遺產。農民成為前無鄉村文化源頭活水滋潤,后無新生文化涵養的物質人、過渡人、空心人。 露絲·本尼迪克特指出:“誰也不會以一種質樸原始的眼光看世界。他看世界時總會受到特定的習俗、風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編排……個體生活的歷史中,首要的就是對他所屬的那個社群傳統上手把手傳下來的那些模式和準則的適應。落地伊始,社群的習俗便開始塑造他的經驗和行為。到咿呀學語時,他已是所屬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長大成人并能參加該文化的活動時,社群的習慣便已是他的習慣,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已是他的戒律。”{12} 此間,鄉村小傳統會讓農民心領神會地認可自己和鄉土的親密關系,建構起水乳相融、相伴相生的依存感和歸屬感,正是代代傳承和共享鄉村文化讓農民不斷強化對自身生命來源和周圍世界的體驗,使得農民個體與鄉土自然而然地達成親如一家、久別重逢的默契,鄉土及其文化的遷延和凝聚得以保證與實現。
但是,嶄新的或古老的、成型或未成型的、現代的或后現代的、外來的或復活的、支流或逆流的文化及其表征:商業文化、封建意識、享樂思想、消費觀念、迷信思維……紛至沓來,又如轟轟作響的高鐵裹挾著農民風馳電掣而去。因此,“斷裂”成為鄉土文化在新世紀的關鍵詞和注腳,溫飽之余的農民面臨物質滿足和精神貧乏的悖反,具體表現為:一是曾經涵養農民的一整套傳統的精神支柱、穩固的文化心理、價值觀念被抽空和置換;二是外來的文化強勢侵入鄉村,不斷地刷新著農民的精神文化內涵。農民的文化心理、人格品質經歷著千年未有之變局。因此,用一句話來概括,鄉村面對的主要不再是物質之“貧”而是精神之“困”——自覺或不自覺的文化“困局”。當下的鄉村似乎失去了文化的“造血”功能,變成一個失血犯困、精神失調的現代化追尋者。作家胡學文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鄉村這個詞一度與貧困聯系在一起。今天,它己發生了細微卻堅硬的變化。貧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則顯得尤為突出。困惑、困苦、苦難。盡你的想象,不管窮到什么程度,總能適應,這種適應能力似乎與生俱來。面對困則沒有抵御與適應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鄉村茫然而無序。”{13}
但是,再失根的鄉村文化,也總會迎來她尋根的子民。盡管在眾多的新世紀鄉土小說中,大多數作家們表達了對鄉村文化“空心化”的失落與茫然、憂慮與批判。也有樂觀的作家預示和召喚了文化鄉土的重建及其可能,顯得彌足珍貴。田耳的《衣缽》就是一部這樣充滿文化自信和頑強鄉土意志的反抗遺忘之作、尋根扎根之作。《衣缽》講述的是一個“重返子宮”的故事。大學畢業生李可學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他的父親是一名出則為官——村主任,入則為鄉間道士的農民。道士這個古老神秘的職業在鄉村生活中廣為農民所尊重、倚重,但是子傳父業傳統背景下,因為李可的進城讀書而顯得后繼乏人,鄉村小傳統及其文化、民俗因為斷代而岌岌可危,未來充滿懸疑。小說中李可對父親的職業經歷了從蔑視到懷疑到旁觀最終到認同、主動融入的過程。這一個在現代進程、科學道路、城市之旅努力探索前行的青年人、現代知識分子、鄉村才子,不期然地“發現”了日漸凋敝的鄉村與自己精神的某些隱秘聯系,深思熟慮后做出了一個與絕大多數同齡人迥異的重大決定:訣別城市與戀人,返鄉繼承父親的道士職業——最后重拾了傳統,傳承了文化。如果將李可的抉擇置放在當代農民/鄉村的關系史、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科學的穩固結盟上進行考量,他的探索與發現則呈現出獨特的意義。首先,作為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當代青年農民,他沒有按照高加林等前輩蹚出的路數,進城去追求現代性的人生。他甚至與家境優渥、才貌雙全的城市戀人王俐維分手了。也就是說,某種意義上,他異乎尋常的選擇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他在高加林等進城農民的譜系上毅然“出軌”了,進而開掘出了另一條隱約可見的路徑,供日后的農民鏡鑒。其次,作為一個現代知識者,在現實的意義上,李可從敞亮的科學之路轉折到“迷信”“古舊”的道士行當,著實令人費解(文本沒有給出合適的動機、重大事件或者答案)。他在當下崇尚科學、鼓吹現代化、破除封建思想的語境中,顯得特立獨行,難以理喻。但是,從鄉村文化復興的角度,這或許是作家一次一廂情愿的想象,一次竭盡全力的鼓呼,其深沉的憂思、焦灼的呼喚清晰可辨。
五
對生態文明的重新尋找是“后尋根”的四維之一,體現在農裔城市人或者是進城農民身上就是近乎瘋狂的對綠色鄉土的復歸、自然鄉土的“復魅”渴求。西蒙娜·微依認為:扎根也許是人類靈魂最重要也是最為人所忽視的一項需求。這是最難定義的事物之一。一個人通過真實活躍且自然地參與某一集體的生存而擁有一個根,這集體活生生地保守著一些過去的寶藏和對未來的預感。所謂自然的參與,指的就是由地點、出生、職業周遭環境所帶來的參與。每個人都需要擁有多重的根。每個人都需要,以他作為自然成員的環境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靈性生命的幾乎全部內容。{18} 仿佛是一種心靈感應,作家趙本夫的“地母”系列小說就形象地抒寫了農民對扎根自然生態、返鄉尋根的極度熱望與追求。多年創作中,他一直思索著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系。他認為土地在中國人心中的情結是一種自然本性。一旦人們把土地當成財富,各種悲劇就會發生。歷史上的戰爭、殺戮、爭奪……都是想成為土地的主人。而當土地回歸自然,成為萬物的母親時,社會才會和諧美好。這是一個關于人類如何生存的根本話題。{19}
小說《木城的驢子》敘述了一個城市的變遷,它以“事實上, 木城人已經失去對土地的記憶”來反寫“莊稼化的城市”,表達了對鄉村記憶遺忘的抵抗,對生態自然的無限向往。小說寫了兩個人物。其中一個是木城出版社總編輯、政協委員石陀。他對“土地”“綠色”有著近乎病態的喜好,每天必干的事情就是用小錘子砸開城里的水泥磚,露出一小塊黑土地,幾天后便長出綠草。神經兮兮的石陀最大的參政執念,就是想喚起木城人對皇天厚土、對自然綠色的記憶。每年的政協會上, 他一成不變、怪誕不經的提案內容是:拆掉城市的高樓大廈、破除街上的柏油路水泥地,讓人們腳踏實地接地氣,種上四季分明的植物,讓草木花果自由自在生長。另一個人是在木城當綠化工的青年農民天柱。天柱有著農民的本色和野心,他揚言,總有一天要將整個木城變成一片莊稼地,這讓方村長全林膽戰心驚。因為,在天柱看來,莊稼不僅帶給人們種植的喜悅,而且它的歲月枯榮可以體現生命正常的生長韻律與生老病死。天柱堅守著自己的理想和本分,他認為,農民無論是進城還是在鄉,看見一塊土就想墾殖,恰恰符合農民的本分。所謂變態,就是改變常態,如果農民不事稼穡、遠離農事才叫變態。對于城里人喜歡在花盆栽花種草,沒有多少文化知識的天柱說出了極富哲理的分析。他說這叫記憶,是對人類祖先種植的記憶。而城里人以為歷經數代人更迭,自己已經洗腳上岸,早已疏離土地,把種植丟卻了,甚至還看不起農民。其實沒忘,這種記憶還殘存在血脈里,無意間就會表現出來,這是本能。石陀對名不見經傳、素未謀面、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作家柴門非常欣賞,也是源于他倆志同道合的鄉土情愫、后尋根心結。小說借助柴門的話說:“城市是個培育欲望和欲望過剩的地方,城里人沒有滿足感沒有安定感沒有安全感沒有幸福感沒有閑適沒有從容沒有真正的友誼……城市,那是個罪惡的淵蔽。”柴門號召都市人重回大地,與鄉土和自然為鄰,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小說的批判鋒芒和后尋根意味非常明顯。后來,石陀派剛入職的大學生谷子去“尋找”柴門。“尋找柴門”是故事發展的動力,實際上這個倔強、執著的尋找的故事與“尋找自然”乃至“尋根”是同構同質的。小說將谷子設定為無父無母的“孤兒”,她認為終其一生就是要上路尋找,在無根無依,沒有來處、缺乏滋養的處境中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尋找她生命的源頭,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緣此,我們看到,尋找柴門—尋找父母—尋找本源—栽種莊稼,在小說的寓言化敘事中融為一體,聚合在一起指證著人們心中那份永不停息的,關于生命、關于鄉土、自然的尋根,意義也就此明晰與升華:這是一個關于鄉土、自然、生命、發展甚至是人類生存的寓言。正如作者趙本夫說:“我們離開土地太久了。失去了人對自然宗教般的情感。文明在建立一種秩序,但是秩序又在束縛著生命的自由。所以現代人總是活在矛盾當中。既要吞噬土地去擴展城市,又要在花盆里種土,保持對土地和祖先種植的記憶。”{20} 在小說中,出版社社長達克將柴門視為反現代、反文明、反社會的糟粕;而谷子作為改革開放進程中成長起來的80后,她對以柴門為表征的鄉土之根、自然之維的絕不放棄的、永遠在路上的尋找,暗示了新生代農民對鄉土的認同,可以視為對達克等“現代人”、城市人之流的反撥,是新生代農民的返璞歸真和未來鄉土振興的希望所在。
趙本夫關注的始終是土地和農民。《地母》三部曲之《無土時代》,講述的仍然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小說以“無土”來命名恰恰說明了“無根”“無綠”,展示了這是一部關于“無土”焦慮、失根懸置、尋根渴望,試圖恢復生態自然的狂想曲。“作品把冷峻而又嚴酷、滾燙而又熾熱的城鄉生活進行變形和寓言式演繹,展現當代城鄉民眾對土地的執著與眷戀,表達現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躁和對美好田園生活的向往。作家把人類對大地的敬仰與回歸之情描寫得如此淳樸澄明,把對生存在歷史與社會夾縫中的各種人物刻畫得那樣獨特奇詭,令我們感動、厭惡而驚詫。”{21} 小說中,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淪為“荒原”,現代化繁榮的表面潛隱著眾多的危機,這就是“無土時代”里的景象,它成為對現代化、城市化表征最深刻有力的批判。“數萬只黃鼠狼”在街上亂串,這個數次出現的細節似乎在喻示危機的降臨。石陀的理想最終由天柱偷梁換柱地實現了。為迎接文明城市檢查,天柱趁機將小麥移植到城市的各處綠地。于是,“春風吹拂的時候,木城幾乎所有的綠地草坪上麥子欣欣向榮,莊稼猝然在城市大面積出現,引起市領導和木城人的陣陣騷動。后來換季時又栽上玉米,玉米棒子結實粗壯,茁壯成長,人們愉快地發現,玉米地里常常有市民出路玩耍,不知是有人偷情,還是有人偷玉米……”——這是一個浪漫的遐想,構建了一個屬于城市的美好童話。讓城市種滿莊稼,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它表達了城市人包括農民內心里對土地和自然的強烈渴望。或許,這真的是一種挽救現代病態城市人的妙法?小說的最后引述了一則新聞報道,說是全國其他十多個大中城市爭相效仿,也在城里空地種上了玉米、高粱和大豆。這是王華《在天上種玉米》的“2.0版”,也不啻為一個“綠色幽默”。顯然,這是作家、有識之士和農民對現實中病態現代化的極力糾偏,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保持一顆敬畏之心:感恩自然,敬畏土地。
六
斯賓格勒有一段話針對的雖然是西方農民,但在指涉當下返鄉創業、戶口還鄉乃至駐足城市回望鄉村的方面,同樣適合于中國農民:“農民是永恒的人,不倚賴于安身在城市中的每一種文化。它比文化出現得早、生存得久,它是一種無言的動物,一代又一代地使自己繁殖下去,局限于受土地束縛的職業和技能,它是一種神秘的心靈,是一種死盯著實際事務的枯燥而敏捷的悟性,是創造城市中的世界歷史的血液的來源和不息的源泉。”{22}
“對當下的懷舊”是杰姆遜提出的概念,因為后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使人在目不暇接的變遷過程中,感覺沒幾年的時間就仿佛超越了一個時代,懷舊感的產生不再僅僅是針對過去,也逐漸針對當下發生的事情。{23} 但是,新世紀農民的“后尋根”與杰姆遜提出的“懷舊”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已不僅僅滿足在文化及其精神、觀念意義上的尋根,而是奮起以實際行動做出了戶口還鄉的重大抉擇,也是他們實實在在的現代體驗的外化。費孝通先生當年痛惜的“鄉村又失金錢,又失人才”的狀況正在出現改變。我們也在《胡不歸》等鄉土小說中看到了“現代新鄉紳”等鄉賢由城返鄉逐漸向鄉村集結,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未來,隨著鄉村振興的全面展開,一個美麗鄉村會如孟德拉斯描繪的“起死回生”的法國鄉村一樣,呈現在世人面前。
注釋:
① 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李培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頁。
②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頁。
③ 佩里·米勒:《離去與歸來》,《民族》月刊(“Departure and Returm”, The Notion),1951年10月。
④ 吉爾·利波維茨基、塞巴斯蒂安·夏爾:《超級現代時間》,謝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頁。
⑤ 種海峰:《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化鄉愁》,《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⑥ 趙允芳:《90年代以來新鄉土小說的流變》,南京師范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
⑦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頁。
⑧ 趙園:《地之子——鄉村小說與農民文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1993年版,第21頁。
⑨ 張德祥:《論新時期小說的歷史意識》,見吳義勤主編《中國新時期小說研究資料》(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頁。
⑩ 葉舒憲:《高唐女神與維納斯:中西文化中的愛與美主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頁。
{11} 段崇軒等:《“新農村建設”與鄉村小說——山西評論家四人談》,《文藝報》2006年5月18日。
{12} 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煒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5頁。
{13} 胡學文:《高懸的鏡子》,《中篇小說選刊》 2006年第5期。
{14} 陳思和:《再論〈秦腔〉:文化傳統的衰落與重返民間》,《揚子江評論》2006年第1期。
{15} 費迪南德· 滕尼斯:《通體社會與聯組社會》,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3頁。
{16} 馬克科姆·考利:《流放者的歸來》,張承謨譯,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頁。
{17} 肖江虹:《觸摸那些看不見的疼痛》,《中篇小說選刊》2009年第3期。
{18} 西蒙娜·薇依:《扎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徐衛翔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4頁。
{19} 王蓬:《豐沛趙本夫》,《中華讀書報》2018年4月18日。
{20} 孫小寧:《趙本夫:為土地而歌》,《北京晚報》2008年6月1日。
{21} 聶震寧:《〈無土時代〉:一部憂思之作》,《人民日報》2009年1月18日。
{22} 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齊世榮等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08頁。
{23} 陳濤:《拆遷、搬遷與變遷:中國當代電影對城市拆遷的再現》,《文化藝術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簡介:廖斌,武夷學院人文與教師教育學院教授,福建武夷山,354300。
(責任編輯? 莊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