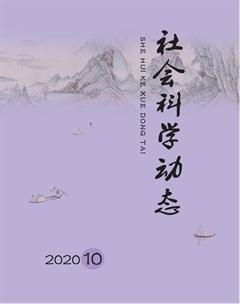紅色書信在“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中的運用探析
摘要:紅色書信不僅是革命者家國情懷的重要載體,也是鮮活、生動的珍貴史料,將其運用在“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中對提升課程的親和力和吸引力、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及增強學生對歷史的感性認識均具有重要作用。將紅色書信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中,既需要借助翻轉課堂的教學理念和實踐,也需要將紅色書信納入課程設計和課堂內容,并借助多媒體手段生動、靈活地增強表達效果,在對歷史的真實感悟中潛移默化地培養其家國情懷和對歷史選擇的認同。
關鍵詞:紅色書信;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家國情懷
中圖分類號:G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0)10-0055-04
當代大學生教育,不僅需要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更需要解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核心問題。這其中思政課無疑承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職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思想政治理論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思政課作用不可替代”①。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作為高校思政課程之一,其目的主要是引導學生認識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內在規律,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是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道路和改革開放。為了使學生通過課程學習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走向和選擇有更深刻的領會和認識,無疑需要在教學中融入更多鮮活生動的實例以增強學生對歷史的“同情之理解”,從而在內心深處深植情感,厚培情懷。
紅色書信,節選的均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做出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所寫的書信,以第一手資料展示了當事人的真情實感和相關事件的歷史背景,屬于“我們黨帶領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②,為后人認識歷史、深刻領悟四個選擇提供了豐富的佐證史料和精神食糧。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政課教師座談會上指出,“推動思政課改革創新,要不斷增強思政課的思想性、理論性和親和力、針對性”③。如何將紅色書信融入“綱要”課程教學中,乃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探索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關于紅色書信在“綱要”課程中的應用,部分學者做了研究(主要對象為紅色家書)。如蔡榕津在《紅色家書融入高校思政課教學的價值及路徑——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為例》(《集美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一文論述了紅色家書在思政課教學中蘊含的豐富教學資源、教學價值和融入路徑。其他成果還有賀超海《〈紅色家書〉誦讀社會實踐活動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西部素質教育》2020年第4期)、葉柳《紅色家書涵育大學生家國情懷:時代意蘊和路徑思考》(《經濟師》2020年第5期)等。總體而言,學界關于紅色書信在思政課教育中的功能、融入途徑等內容的研究明顯不足。本文以紅色書信(紅色家書側重于家庭成員之間的書信,而紅色書信則不限于家庭成員之間)為主要對象,探討其在高校“綱要”課中的價值和融入途徑,以期為提升“綱要”課程的教學效果和實現教學目標提供更多的選擇和探討。
一、紅色書信在“綱要”課程中的重要價值
紅色書信不僅是重要的歷史文獻和革命教育素材,也是當代高校“綱要”課程教育的重要資源。
(一)紅色書信是近現代革命者家國情懷的重要載體。歷史人物內心堅定的家國情懷,不僅是一種意識、價值觀和理念,也藉由實踐、談話、文章、書信等方式予以展現和傳播。書信作為一種私人之間的交流工具,更為真切和貼近書寫者的真實心境。紅色書信,恰恰是理解革命者追求國家獨立、民族富強和人民幸福初心和使命的重要史料。教師借助紅色書信能夠帶領學生更真切地體會到革命者對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篤定追求和矢志不渝的努力,以及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使命感、責任感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擔當與胸懷。如周恩來同志1921年在致表兄陳式周的信中說明了他赴歐洲勤工儉學的主要目的:“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潛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于吾民族間者。”④ 生動展示了周恩來為謀求民族自立、國家自強而求學、探索的革命自覺和實踐。再如1944年吳玉章致信侄子吳端甫,堅定指出:“我認為中國只有這一條光明大道”⑤,足見吳玉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發自內心的認可與堅定。
(二)紅色書信的真實性及情感的生動性,有助于提升“綱要”課的親和力和感染力。“‘綱要課又兼具歷史學的學科特點,在教學過程中要通過具體的、現實的、個體的歷史事件、人物故事來闡釋歷史邏輯”⑥。紅色書信是歷史人物在工作、生活場景下真實心境的自然流露和表達,“具有信息更集中、材料更真實、情感更真切的特點”,“主要是革命先輩之間或他們與親友交換看法、交流感情的親筆信件,留存至今則是真實的記載,是寶貴的歷史資料”⑦。
通過紅色書信我們能真切感受到歷史事件的真實場景、歷史人物的真實思想和情感生活,“不僅有正確的主張,有真摯的感情,還有美麗的文采”⑧,“從中可以看到那顆鮮紅的、彼時彼刻正在搏動的‘初心”⑨。這種鮮活感、現場感和真實感,有助于“充分利用人物的榜樣性和事例的生動性來感化學生,達到情感培育的最終目的”⑩,比普通的說教、宣傳更有吸引力,更能贏得學生的認可和引發共鳴、拉近教師和學生的距離,進而提升“綱要”課的親和力。如1936年趙一曼在獄中致信兒子,開篇即說:“母親對于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際行動來教育你”{11},讀來令人深刻感受到革命烈士對家庭的深情,革命人物的形象更為豐滿、真實和立體。再如1935年劉伯堅在艱難困苦和嚴刑拷打的背景下在獄中致信妻嫂鳳笙等人,劉伯堅表明心志:“弟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12},革命者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躍然紙上。
(三)紅色書信是一手史料,是歷史人物的真實表達,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有助于提升“綱要”課的感染力和喚起學生的情感認同。相比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等內容,書信更多的私人之間真情實感的自然表達,“通過原信不加粉飾的敘述,透過濃烈的情感色彩,更好更準確的體會作者當時所思所想、所喜所憂”{13}。信息更集中、材料更真實、情感更真切,有助于提升“理論的解釋力、說服力與感召力”{14}。紅色書信作為一手史料的真實性、權威性,教師藉由紅色書信引導學生“走向歷史現場”,有力地提升了“綱要”課的感染力和說服力。當前隨著意識形態斗爭的日益復雜,在社會上存在著一定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否定歷史、否定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紅色書信則是反擊“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武器之一。歷史人物的革命抉擇和奮斗,不是后人捏造、粉飾的,而是真切發生、自然表達的,不僅體現在歷史人物的公開行動中,也體現在其個人書信中,有力佐證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國家和人民的歷史選擇。另一方面,當代大學生基本都是“95”后甚至是“00”后,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生活環境往往容易造成當代大學生對真實歷史比較無感。部分歷史劇為了賺取流量嘩眾取寵,既未能真實反映近代中國社會的艱難探索和轉型,亦未能真實展示革命者為理想信念所付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紅色書信作為真實歷史的自然體現,對于引導當代大學生真切認識歷史、理解四個選擇具有重要意義。如1929年共產黨人何叔衡致信義子何新九,言明:“我的人生觀,絕不是想安居鄉里以善終的,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的”{15}。借助此書信,我們能真切感受到共產黨人一心為國的責任、擔當和歷史使命感。再如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江姐致信譚竹安,表明他對生死的態度:“我們到底還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萬一他作破壞到底的孤注一擲,一個炸彈兩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這可能我們估計的確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沒有。假如不幸的話,云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16}。書信展示了江姐在生死面前大無畏的精神和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革命意志,與歷史教材、影視劇中江姐的形象一致,可促進大學生自覺理解和接受四個選擇。
(四)紅色書信教育可以引導學生掌握歷史研究方法、培養歷史思維。“綱要”課程不僅需要向大學生闡述四個選擇的歷史邏輯和理論基礎,也需要引導學生思考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關于歷史研究方法,陳春聲指出:“在現階段,各種試圖從新的角度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歷史的努力,都不應該過分追求具有宏大敘事風格的表面上的系統化,而是要盡量通過區域的、個案的具體事件的研究表達出對歷史整體的理解”{17}。個案、具體事例的理解和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宏觀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綱要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能簡單地向學生復述 ‘既定的史實和結論,而是要借助史料分析的方法,引導學生透過歷史現象,了解歷史的內在聯系及其本質”{18}。
概而言之,紅色書信蘊藏著豐富的史料,生動、鮮活、真切而權威,“閱讀書信,有助于以點帶面,觸類旁通,把握真實”{19}。借用紅色書信,對提升“]”課程教學效果有著積極的價值和作用。
二、紅色書信融入“綱要”課程教學中的路徑和方法
宏大歷史敘事需要借助區域、具象、微觀的歷史人物和實踐來豐富和完善。“綱要”課程,不僅需要介紹宏大歷史,介紹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轉型、變遷,介紹中國人民為了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所付出的艱苦努力,亦需要借助多種手段將紅色書信納入教學,以期提升“綱要”課程的效果。
(一)借助翻轉課堂教學方法將紅色書信納入“綱要”課程教學。翻轉課堂教學是近幾年較為盛行的一種教學方法,是“將傳統的課堂教學結構翻轉過來,讓學生在課前完成知識點的學習,在課上完成知識的吸收并掌握的新型教學模式”{20};其核心是改變過去教學的教師主導、學生被動的單向傳播局面,借助師生互動和學生主動、提前熟悉知識基礎,“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加強生師互動,注重調動學生積極性”{21};營造教學相長、互動的氛圍引導學生參與教學,構建“學生主體、教師主導”的教學模式,從而提升教學效果。借助翻轉課堂教學方法,紅色書信既可由教師誦讀給學生,引導學生領會、理解和消化吸收,也可以發揮學生的積極性,通過問答式教學、情景劇場、組建學習小組自主學習分享等方式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思考問題,在不斷啟發中讓學生水到渠成地得出結論,激發學生事先、主動去學習、理解紅色書信的內容及其背后蘊含的家國情懷。如理解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持久戰”,可以借助左權1937年9月18日致叔父左銘三的信函,其中提及盧溝橋事變爆發已兩個月,左權堅信:“這一戰爭必然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22}。藉此引導學生了解抗戰爆發前中日雙方的競爭態勢、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具體思想,再結合左權的信件組織學生討論持久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讓大學生更全面認知持久戰是基于中日雙方的競爭態勢、發展趨勢和國際趨勢做出的既非悲觀亦非盲目樂觀的明智判斷,其對指導抗戰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節選紅色書信佐證“綱要”課程教學內容。紅色書信是家國情懷的主要載體,也是開展家國情懷教育的重要抓手,可以“將家國情懷的理論知識轉化為青少年喜聞樂見的教學教材內容,便于接收、理解和把握,提高培育的有效性”{23}。如關于中國人民為什么選擇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可以引用周恩來1921年致表兄陳式周的信,周恩來在比較了各國革命方法、路徑后堅定認為,“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24},說明周恩來1921年在經過深思熟慮后已堅定選擇了共產主義。在介紹革命者堅定選擇馬克思主義時,可以引用夏明翰1928年致母親的信,“相信你會看到我們舉過的紅旗飄揚在祖國的藍天”{25}。此時正是革命的低潮,夏明翰身處獄中但并未悲觀,在致母親的信中表達了對共產主義必勝的堅定信念。在介紹革命者胸懷天下的使命感時,可以引用俞秀松1923年致父母的信函,俞秀松寫道:“做官?我永不曾有這個念頭!父親也不敢有這種希望于我吧”,“我的志愿早已決定了:我之決志進軍隊是由于目睹各處工人被軍閥無理的壓迫,我要救中國最大多數的勞苦群眾,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勞苦群眾的仇敵——其實是全中國人的仇敵——便是軍閥”{26}。在介紹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時,可以引用1949年毛岸英致表舅向三立的信,背景是新中國成立伊始毛岸英的表舅向三立寫信給毛岸英“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的位置”。毛岸英回信說:“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于父親,他是這種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因為這種做法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27}。
(三)運用多媒體手段增強紅色書信在“綱要”課程教學中的效果。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當代大學生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元化,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的單向和說教式的教學越來越難以解決大學生“隱形逃課”與“抬頭率”的問題,課堂中存在大學生“不看”、“不聽”、“不想”的困境,“綱要”課程的效果容易遞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運用新媒體新技術使工作活起來,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傳統優勢同信息技術高度融合,增強時代感和吸引力”{28}。在工具方面,“綱要”課程教師可以大膽引導學生運用PPT、情景劇、微博、微信、QQ、抖音、今日頭條、B站、在線K歌(朗誦)、慕課、微課等大學生更容易接受的工具介紹、傳播紅色書信的內容,使知識生動化、鮮活化、在線化,“為學生提供‘真學的資源,創造‘真懂的環境”{29}。在形式方面,除了傳統的圖文、誦讀外也可以借助影視視頻、紅色書信涉及的文化類綜藝節目(如2016年國內開播的首檔明星書信朗讀節目《見字如面》、重慶衛視《品讀》等)、學生拍攝的小視頻、歷史博物館現場教學等多種形式。
(四)古今融合引導大學生理解四個選擇、增強四個自信并正確認識當代社會。鄧小平同志強調:“要懂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大學生是祖國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各條戰線的主力軍,學習“綱要”課程不僅需要領會和理解四個選擇、增強四個自信,也需要以史為鑒更好地認識當代社會,“通過對有關歷史進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運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分析和評價歷史問題、辨別歷史是非和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30}。增強對當代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將個人理想從理念轉化為社會實踐,成長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接班人。在運用紅色書信開展“綱要”課程教育時,教師不能簡單地就史論史,還應結合中國當前社會的發展引導學生汲取紅色書信的力量和營養,辯證認識當前社會的各種現象,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把思政小課堂同社會大課堂結合起來,教育引導學生立鴻鵠志,做奮斗者”{31}。如在介紹共產黨人不畏艱難、置個人生死于不顧的時候,可以引用王若飛1933年在獄中致表姐夫的信函,信中寫道:“弟處逆境,與普通人不同處,即對于將來前途,非常樂觀。這種樂觀,并不因個人的生死或部分的失敗、一時的頓挫,而有所動搖”{32}。這種革命樂觀主義和為了革命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擔當和胸懷并不只停留在戰爭年代,可以結合今年突發的新冠疫情進一步闡述紅色書信傳達出來的革命精神。面對新冠疫情,在黨中央的領導和號召下數十萬共產黨員積極奔赴一線,齊心協力、共戰疫情,展示了共產黨員的大無畏精神和中國人民的凝聚力及戰斗力,也充分展示了中國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和文化優勢,對于提升中國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紅色書信作為鮮活、生動的第一手史料,具有較強的說服力,蘊藏著豐富的教學價值,也是引導學生培養歷史思維的重要手段。綜合運用多種方法、手段和工具,大膽探索、創新,才能更好發揮紅色書信的價值和作用。
注釋:
①②③{28}{31} 習近平:《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④ 《周恩來致表兄陳式周》(1921年1月30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⑤ 《吳玉章致侄子吳端甫》(1944年12月8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
⑥{18} 蔡榕津:《紅色家書融入高校思政課教學的價值及路徑——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為例》, 《集美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
⑦⑧⑨{13}{19} 《從紅色書信中看到堅貞不渝的初心》,《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2、3、2、2、2頁。
⑩ 魯濤、張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中“家國情懷”教學專題設計的探索》,《長沙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11} 《趙一曼致兒子陳掖賢》(1936年8月2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頁。
{12} 《劉伯堅致妻嫂鳳笙等》(1935年3月16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頁。
{14} 王道紅、王永章:《“四維”并進:提升思想政治理論課親和力》,《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15} 《何叔衡致義子何新九》(1929年2月3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頁。
{16} 《江竹筠致親友譚竹安》(1949年8月27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0—81頁。
{17} 陳春聲:《走向歷史現場》,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和實踐》,三聯書店2010年版,“叢書總序”,第Ⅱ頁。
{20} 張金磊、王穎、張寶輝:《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研究》,《遠程教育雜志》2012年第4期。
{21} 《教育部關于印發〈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工作基本要求〉的通知》,教社科〔2018〕2號。
{22} 《左權致叔父左銘三》(1937年9月18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頁。
{23} 王芳儀、劉珍:《淺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融入高校思政課教學的培育途徑》,《知識經濟》2017年第1期。
{24} 《周恩來致表兄陳式周》(1921年1月30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25} 《夏明翰致母親陳云鳳》(1928年3月),《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26} 《俞秀松致父親俞韻琴等》(1923年1月10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27} 《毛岸英致表舅向三立》(1949年10月24日),《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頁。
{29} 唐登蕓:《論推動信息技術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融合向深度發展》,《思想理論教育》2019年第4期。
{30} 《開篇的話》,本書編寫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32} 《王若飛致表姐夫熊銘青》(1933年1月),《初心——紅色書信品讀》編寫組:《初心——紅色書信品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5頁。
作者簡介:楊洋,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湖北宜昌,443002。
(責任編輯? 江? 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