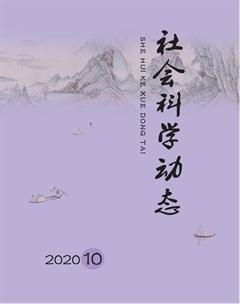湖北城市創新效率測評與提升策略研究
張靜 劉威



摘要:通過構建創新效率評價指標體系,使用2013—2017年市州面板數據,采用三階段DEA測算湖北長江經濟帶各市(州)創新效率,結果發現:(1)從空間格局看,武漢、宜昌、襄陽、鄂州、黃石的創新綜合效率位于前列, 而恩施、仙桃、潛江和天門等市則處于末端。(2)從時間演變看,綜合技術效率變化趨勢存在區域差異,各市(州)變化趨勢大致可以分為穩定型、上升型和下降型。基于以上結論,提出綜合施策優化城市創新生態、構建產學研良性互動循環、優化各類人才“引用留育”機制和完善創新投入機制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創新效率;三階段DEA;湖北長江經濟帶
基金項目:湖北省軟科學研究項目“湖北長江經濟帶城市創新效率評價與提升策略”(項目編號:2019ADC129);湖北省重大調研課題基金項目“湖北省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發展的熱點、難點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J23)
中圖分類號:F01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0)10-0087-09
引言
創新能力是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和增加區域競爭能力的關鍵要素,而創新效率的高低綜合反映區域創新系統對資源的配置能力與使用效率,進而成為評價該區域能否持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準。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時明確提出:以長江經濟帶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湖北是長江干線流經里程超千公里的唯一省份,科學評價湖北長江經濟帶城市創新效率,對湖北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走在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前列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從已掌握的文獻資料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關于不同測度方法比較研究。創新效率測度方法主要有以隨機前沿模型(SFA)方法為代表的參數方法和以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為代表的非參數方法。隨機前沿分析(SFA)方法是評測決策單元有效性的常用方法。李婧在考慮空間效應的基礎上,應用隨機前沿模型對各地區創新效率進行實證測評與分析①。曹霞結合投影尋蹤模型處理高維數據的特點,改進隨機前沿模型,對中國各區域創新效率及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②。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是評價多投入—多產出模式下決策單元間相對有效性較為常用的方法。時鵬將③、孫凱④等運用DEA模型對我國區域創新效率進行靜態分析。隨著對區域創新過程及創新價值鏈理解的逐步深入,既關注區域創新科技投入產出情況,又關注科技成果經濟轉化情況的二階段DEA模型受到關注,如馮志軍⑤等。劉鳳朝⑥、徐小欽⑦、韓先鋒⑧、劉明廣⑨等分別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對創新效率進行動態分析。李蘭冰⑩基于DEA模型和Tobit模型、陳偉{11}基于規模報酬可變的鏈式關聯網絡DEA模型、劉偉{12}將三階段DEA模型與Bootstrap方法相結合、分別對我國省級區域創新效率進行測算與比較分析。
二是關于區域創新效率實證研究。國內學者基于省際面板數據,對各省區的創新效率值進行測算、評價與比較,研究成果頗豐。劉順忠{13}、池仁勇{14}、官建成{15}分別采用DEA方法實證測算了中國各省區的創新效率值,并考察影響創新效率的關鍵因素。岳書敬{16}等應用SFA方法研究1998—2005年我國區域研發效率差異及其影響因素。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無論是從研究方法還是從研究范圍上,學者對我國區域創新效率問題都已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探索。同時,已有研究對創新效率的評價多側重于國家及省際之間,對省內各城市創新效率的研究不多,而恰恰是省內各城市的創新效率影響了省級層面的整體創新能力。學者大都對創新進行階段劃分,但是對研發資本存量在創新過程中起到的累積作用、創新產出對下一次創新產生影響等涉及較少。因此,本文選擇三階段DEA,引入資本存量指標,以湖北省各市(州)為對象分析其創新效率,旨在為政府制訂有效的區域發展政策、合理配置創新資源、提高區域創新能力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以創新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一、方法與數據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三階段DEA模型測算湖北省16個市(州)創新效率。考慮創新過程的連續性,引入資本存量作為創新投入指標,構建創新效率評價指標體系。根據Fried等提出的模型,三階段DEA構建過程如下:
第一階段:利用BCC模型測算效率值。經典的DEA模型分為CCR模型和BCC模型。CCR模型是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BCC模型則可以處理規模報酬變動下的效率問題,且BCC模型計算的綜合技術效率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這有助于分析區域創新效率受純技術因素或規模因素影響。由BCC模型計算出投入變量的松弛變量,作為第二階段的投入變量。
第二階段:構造相似SFA模型。Fried等(2002)指出第一階段的投入松弛量是由管理無效率、環境因素和隨機噪聲造成的。第二階段以第一階段求出的松弛量為因變量,以環境因素為自變量,通過構建相似SFA模型,將環境影響和隨機噪聲剔除,僅保留管理無效率造成的投入松弛。
以投入變量的松弛量為因變量,環境因素為自變量,構造模型,如式(1)所示:
Sni=f(Zi;βn)+νni+μni;i=1,2,3……,n=1,2,3……(1)
其中,Sni是第i個決策單元第 n項投入的松弛值;Zi是環境變量,βn是環境變量的系數;νni+μni是混合誤差項,νni表示隨機干擾,μni表示管理無效率。其中ν是服從N(0, σν2)是隨機誤差項,表示隨機干擾因素對投入松弛變量的影響;μ是管理無效率,表示管理因素對投入松弛變量的影響,假設其服從在零點截斷的正態分布,即μni服從N+(0, σν2),νni和μni不相關。采用極大似然技術估計未知參數,剔除環境因素和隨機因素對效率測度的影響,以便將所有的決策單元調整于相同的外部環境中。調整公式如下:
ΧniA=Χni +[maxi(Zn)- Zin]+[maxi(ni)-ni
n=1,2,3……,N;i= 1,2,3……,I? ? ? ? ? ? ? ? ? (2)
其中,ΧniA是調整后的投入,Χni 是調整前的投入;[maxi(Zin)- Zin]是對外部環境因素進行調整;[maxi(ni)是將所有決策單元至于相同運氣水平下。
上式中,ni可由條件估計?魯[ni丨ni+μni]估計得到。?魯[ni丨ni+μni ]可以根據下面公式計算得出:
?魯[νni丨νni+μni]= Sni- Znin-?魯[μni丨νni+μni]? ? ? ? ? ? (3)
第三階段:調整后的BCC模型。在第三階段,利用經過第二階段調整后的投入和原始產出重新帶入BCC模型進行效率測算。由于剔除了環境因素和隨機噪聲的影響,調整后的效率值能更為客觀準確地反映決策單元的創新效率水平。
(二)變量選擇
一般而言,運用三階段DEA模型進行效率測算時,應明確對應的指標體系。本文從投入、產出和環境變量三個維度來構建區域創新效率的變量體系。
1. 投入變量
勞動力和資本是經濟投入產出系統研究中的兩個基本投入。在對區域創新效率進行測度時,其投入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衡量。(1)在人員投入方面,本文主要采取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X1來衡量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的實際投入水平。鑒于十堰和潛江市相關指標數據的缺乏,本文分別采用科學家和工程師人員數、科學研究與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予以代替。(2)在資本投入方面,本文采取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R&D)內部支出X2衡量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究與開發機構當年用于企業內部的實際支出。
2. 產出變量
本文從區域創新創造的價值或潛在價值方面選擇。國內專利申請授權數(Y1)代表區域創新能力的潛在產出,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額(Y2)和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Y3)代表區域科技創新能力的直接產出,反映區域科技與經濟相結合、技術成果轉化為市場價值的水平。
3. 環境變量
環境變量是指對創新效率產生影響但不是決策單元可控制的因素。本文從五個方面考慮影響地區創新效率的環境變量。
(1)經濟發展。地區經濟發展與創新投入密切相關。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創新投入也會越多,因而也越有能力進行創新活動。本文采用地區人均GDP(Z1)來表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2)政府資助。政府對創新活動的資助主要體現在實行撥款資助和稅收優惠等政策來扶持創新活動,降低企業開展研發創新活動的成本和風險,激發企業開展研發創新的積極性。本文選用科技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Z2)來表征政府資助這一指標。
(3)開放程度。對外開放是保障區域可持續發展重要因素。本文用各區域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Z3)來表征區域開放程度。
(4)金融支持。金融機構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亦為創新主體提供金融信息和咨詢服務。本文采用區域年末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占GDP(Z4)的比重來表征其對創新金融環境的支持。
(5)基礎設施。區域創新中基礎設施的能為創新提供必要的物質、交通、信息等支撐條件,基礎設施條件越完備越有利于創新的發生。考慮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選取互聯網用戶數量(Z5)來表征區域基礎設施發展水平。
(三)數據來源
本文原始數據來源于2014—2018年《湖北省統計年鑒》和湖北省各個市州(不含神農架林區)的《統計年鑒》,研究對象為湖北省16個市(州)(神農架林區數據不全,分析中暫時不予考慮)。文中的投入、產出和環境變量如表1所示。其中個別缺失數據本文采用線性插值法補齊。
二、測算與分析
遵循三階段DEA的分析步驟,本文分三步給出每階段的估計結果。
(一)第一階段DEA結果
在第一階段,通過所獲取的相關數據,借助軟件DEAP2.1,選擇BCC模型,對2013—2017年湖北省16個市州的創新效率水平進行了測度。其中綜合技術效率(TE)反映各個市州的綜合績效;純技術效率(PTE)反映剔除規模報酬影響后的各個市州的創新技術效率,也可以理解為受管理水平和技術影響的生產效率;規模效率(SE)是指各個市州投入規模變化對綜合技術效率的影響,反映各個市(州)創新規模的優化程度。結果如表2所示。
省域創新效率分析。2013—2017年,湖北省整體創新綜合效率和純技術效率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規模效率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其中綜合效率均值為0.608,純技術效率均值為0.781,規模效率均值為0.768。2013—2014年,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呈現上升趨勢,且規模效率要低于純技術效率,說明該時段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促進了綜合效率的提升,且造成綜合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問題是規模效率偏低。從2015年開始,綜合效率呈現先增后減的趨勢,純技術效率開始遞減,規模效率則遞增,且規模效率已經高于純技術效率,說明該時段主要是由規模效率促進綜合效率的提升,而純技術效率則造成綜合效率下降且處于較低水平。
規模報酬分析。2013—2017年,16個市(州)共80個評測單元中,處在最沿面的有22個,其中有1個規模報酬遞減,21個規模報酬不變。非有效單元有58個,其目標值有5個是規模報酬遞增,53個規模報酬遞減。整體來看,規模報酬遞減的有54個,占比67.5Z%,規模報酬遞減的有5個,占比6.25%。可見,實現規模報酬遞增的市(州)很少,說明各個市(州)的創新規模沒有實現最優狀態,且近年來這種狀態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地級市差異分析。(1)從時間趨勢看,鄂州、恩施連續五年達到效率前沿面;武漢、潛江和天門的創新效率呈現上升勢態,分別在2015年和2016年達到效率前沿面;仙桃從2013—2016年連續4年處于效率前沿面,于2017年開始下降。黃石、十堰、宜昌、襄陽、孝感和咸寧呈現出螺旋上升勢態;荊門呈現出逐步下降趨勢;荊州、黃岡和隨州均呈現出波動變化,且處于無效率狀態。(2)從空間格局看,效率值較高的地區分別是武漢、鄂州、恩施、仙桃和潛江,較低的地區有黃石、十堰、宜昌、襄陽、荊門和孝感。可以看出,各市(州)創新效率值的空間分布與各自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文認為DEA的測算結果可能存在偏差,這種偏差的原因可能在于沒有考慮各個市(州)的環境差異。三階段DEA可以有效克服這一缺陷。
(二)第二階段SFA回歸結果
通過SFA回歸,可以剔除環境因素和隨機噪聲的影響。基本思路是將各個投入指標的松弛變量作為因變量,環境指標作為自變量,進行SFA分析。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來看,2個投入的松弛變量均通過LR檢驗,說明整體來看外部環境明顯影響投入松弛變量。gamma值分別為0.824和0.69,且均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在各個決策單元中管理無效占主要因素。因此,為剝離管理因素和隨機因素,對投入變量進行第二階段的調整顯得十分重要。
在考察環境變量對投入松弛量所帶來的影響時,若系數是正數,則意味著環境變量數值上升將會使投入的松弛變量增長,或者使得產出下降,造成浪費,對環境效率產生不利影響;若系數是負數,則表明,環境變量數值上升將會使得投入松弛量下降,產出增加,產生節約現象,對環境效率產生有利影響。下面具體分析對投入松弛變量產生顯著影響的環境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與R&D內部支出的松弛變量回歸結果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經濟發展對與R&D內部支出的投入冗余帶來的影響是顯著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使得R&D內部支出投入冗余上升,從而降低R&D內部支出的利用效率。(2)政府資助。政府資助與R&D內部支出的松弛變量回歸結果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負,這說明政府資助對R&D內部支出的投入冗余具有負向影響,政府資助增加使投入的冗余降低,有利于資源的合理利用,提升決策單元的創新效率。(3)開放程度。開放程度與R&D內部支出的松弛變量回歸結果在1%的置信水平下為正。這說明開放程度的增加將會導致投入冗余的增加,造成資本投入的浪費現象。
基于上述分析,各個環境要素對決策單元的影響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不控制這些環境因素,就使得決策單元處于不同的環境之中,從而造成效率估計結果誤差。本文應用相應的公式對原有投入變量進行調整,從而剝離環境因素和隨機噪聲的影響,使各個決策單元處于相同的外部環境條件下,以便提高估計結果準確性。
(三)第三階段調整后DEA結果
上述第二階段得到剔除環境因素和隨機噪聲后的原始投入的調整值,本部分將調整后的投入值和原始產出值再次帶入傳統DEA模型之中進行分析,得到第三階段各個市(州)的創新效率和規模報酬狀態,如表4所示。
調整前后效率值比較。(1)從整體趨勢看,綜合效率由調整前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變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趨勢,且數值有所下降。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均值走勢未發生變化,但數值分別有所上升和下降。(2)從各市(州)看,武漢、黃石、十堰、宜昌、襄陽和荊門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均出現明顯上升,說明這些地區不僅外部環境好,而且管理水平也較高。而鄂州、孝感、荊州、黃岡、咸寧、隨州、恩施、仙桃、潛江和天門的綜合效率均出現下降,說明效率低水平并非單純由環境因素造成,應該進一步加強自身創新實力,尤其是加大研發投入總量,調整企業規模,引進高端人才提升創新競爭力。考慮環境因素和隨機噪聲后,湖北省各市(州)的創新效率值有所變化,說明傳統DEA方法傾向于高估或低估各市州的創新效率值,不能真實反映各個市州的創新效率水平。
規模報酬分析。16個市(州)在2013—2017年80個評測單元中,處于前沿面的有6個,均為規模報酬不變。非有效單元有74個,其目標值均為規模報酬遞增。整體來看,規模報酬遞增占比92.5%,規模報酬不變占比7.5%。武漢長期處于規模報酬不變的階段,其他市(州)大部分年份均處于規模報酬遞增。說明武漢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規模相對已經比較優化,而其他市(州)地區還處于規模不優的階段。
市(州)差異分析。(1)從空間分布看,區域之間綜合效率和規模效率差異明顯,而純技術效率比較接近,說明各市(州)之間的效率差異主要是由規模效率引起的。各市州創新綜合效率從大到小依次為武漢、襄陽、鄂州、宜昌、黃石、孝感、十堰、荊州、荊門、黃岡、咸寧、隨州、仙桃、潛江、恩施和天門。其中,武漢在三種效率評價中均名列前茅,天門則處于效率評價的末端;恩施、潛江、隨州和咸寧的純技術效率表現突出,但規模效率拉低了綜合效率。(2)從時間趨勢看,綜合技術效率變化趨勢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種是穩定型,武漢的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連續五年均處于前沿面,決定其綜合效率也處于前沿面;恩施、仙桃和天門長期穩定處于低位,這是因為規模效率也基本呈現長期穩定低位態勢。第二種是上升型,如荊州、咸寧和潛江,這些城市主要是因為規模效率的上升。第三種是下降型,如黃石、十堰、宜昌、襄陽、鄂州、荊門、孝感、黃岡和隨州。其中黃石、宜昌、孝感和隨州等市是由于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均下降引起的,十堰、襄陽、荊門和黃岡主要是由于純技術效率下降導致的,鄂州主要是由于規模效率的下降。
三、結論與建議
基于2013—2017年湖北省市級層面的數據,本文使用三階段DEA模型對16個市(州)的城市創新效率進行了測算。研究發現:一是環境因素對創新效率產生顯著影響。三階段DEA剔除了環境因素,分離了管理無效率,在創新效率評價上更加準確。從調整前后結果比較來看,武漢、黃石、十堰、宜昌、襄陽和荊門的綜合效率值出現明顯的上升,而鄂州、孝感、荊州、黃岡、咸寧、隨州、恩施、仙桃、潛江和天門的綜合效率均出現下降,這說明有利的外部環境對效率有提升作用。二是創新效率和規模效率存在區域差異。從時間演變看,綜合技術效率變化趨勢存在區域差異,主要原因是各個市(州)的規模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和各地的管理水平有所差異,其變化趨勢大致分為穩定型、上升型和下降型。從空間分布看,武漢、宜昌、襄陽、鄂州、黃石的創新綜合效率位于前列,而恩施、仙桃、潛江和天門等市則處于末端,這基本與現實經濟狀況相符。
應著眼于打造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激活區域創新發展潛力,轉變思維路徑和發展模式,以湖北一圈(武漢城市圈)兩群(宜荊荊和襄十隨城市群)為載體,加強部門間、市(州)間協調聯動,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開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改革先行先試。一是建立開放合作創新生態。整合知識、技術、資本、人才等創新資源,引導“一主兩副”高水平創新區域與低水平區域的創新合作與交流,發揮國家級高新區溢出效應,引導高新區內主導產業的部分配套產業轉移至周邊腹地,支持其對區位相鄰相近、產業關聯同質的產業園區進行空間整合、資源整合和產業整合。推進區域人才柔性交流。加強人才政策銜接,探索專業技術職務聘任職業資格互認、畢業生實習創業互補流動、互派科技管理干部等人才流動新模式。省、市相互選派科技、商務、教育、衛生等領域優秀黨政干部交流掛職和異地培訓。依托企業創新平臺,組織動員高校院所科技人才、創新團隊跨區域到園區、企業掛職兼職。支持科技人才在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之間流動或雙向兼職。二是強化財政金融支撐功能。充分發揮政府資金對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的引導和拉動作用,加大對基礎研究、產業技術聯盟、科學儀器設備共享、國家級和省級創新平臺、對外經貿合作區等財政經費投入。提高引導基金規模、出資比例及讓利,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探索建立投融資服務平臺,推動武漢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提檔升級。試行科技企業信用貸款及科技企業聯投聯貸聯保機制。推廣東湖高新區“投貸聯動”模式和宜昌自貿片區“小微快貸”模式。建立創新券通存通兌試點,建立統一的創新券服務平臺。
注釋:
① 李婧:《考慮空間效應的區域創新效率測評》,《研究與發展管理》2011年第1期。
② 曹霞:《創新驅動視角下中國省域研發創新效率研究——基于投影尋蹤和隨機前沿的實證分析》,《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5年第4期。
③ 時鵬將:《R&D投入產出效率的DEA分析》,《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4年第1期。
④ 孫凱:《基于DEA的區域創新系統創新效率評價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馮志軍:《我國區域科技創新二階段效率評價及策略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年第6期。
⑥ 劉鳳朝:《基于Malmquist指數法的我國科技創新效率評價》,《科學學研究》2007年第5期。
⑦ 徐小欽:《專利產業化示范項目扶持建設的重點產業選擇——以重慶市為例》,《科技進步與對策》2008第9期。
⑧ 韓先鋒:《我國區域科技創新效率、模式與收斂性分析》,《統計與決策》2010年第16期。
⑨ 劉明廣:《區域創新系統的創新效率動態評價——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1期。
⑩ 李蘭冰:《我國區域科技創新效率評價——以省際數據為樣本》,《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9期。
{11} 陳偉:《中國區域創新系統創新效率的評價研究——基于鏈式關聯網絡DEA模型的新視角》,《情報雜志》2010年第12期。
{12} 劉偉:《中國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效率的區域差異分析——基于三階段DEA模型與Bootstrap方法》,《財經問題研究》2013年第8期。
{13} 劉順忠:《區域創新系統創新績效的評價》,《中國管理科學》2002年第1期。
{14} 池仁勇:《我國東西部地區技術創新效率差異及其原因分析》,《中國軟科學》2004年第8期。
{15} 官建成:《基于DEA的國家創新能力分析》,《研究與發展管理》2005年第3期。
{16} 岳書敬:《中國區域研發效率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基于省級區域面板數據的經驗研究》,《科研管理》2008年第5期。
作者簡介:張靜,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湖北武漢,430077;劉威,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湖北武漢,430077。
(責任編輯? 辰?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