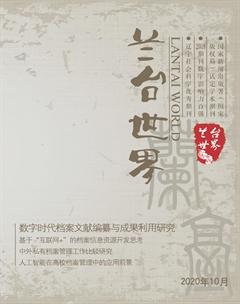檔案學(xué)的后現(xiàn)代主義視角
摘 要?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廣泛滲透,使我們重新分析和理解我們已經(jīng)建構(gòu)的科學(xué)、社會、組織、商業(yè)活動以及其他種種。以特里·庫克為代表的檔案學(xué)家們也開始將后現(xiàn)代主義引入檔案理論與實踐的思考。享譽國際的檔案學(xué)者特里·庫克的宏觀鑒定思想、后保管思想以及檔案學(xué)范式思想,無不體現(xiàn)了其對于傳統(tǒng)敘事的解構(gòu)和批判以及對于多元化的后現(xiàn)代主義精神的倡導(dǎo)。
關(guān)鍵詞 特里·庫克 檔案學(xué) 后現(xiàn)代主義
中圖分類號 G270 文獻標(biāo)識碼 A 收稿日期 2020-02-10
★作者簡介:王安祺 天津師范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 碩士研究生。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widespread penetration of postmodernism has allowed us to reanalyze and understand science, society, organizatio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so on that we have constructed. Archivists represented by Terry Cook have also begun to introduce postmodernism into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macro-appraisal idea, post-preservation idea and archival paradigm idea of Terry Cook,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rchivist, reflects his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and his advocacy of the spirit of diversified postmodernism.
Keyword Terry Cook; archival science; postmodernism
一、特里·庫克后現(xiàn)代主義檔案學(xué)思想根源
特里·庫克(1947—2014)雖是加拿大檔案學(xué)家,但他的專業(yè)地位和影響早已超越國界,成為北美乃至國際檔案界普遍尊崇和敬仰的檔案大師,其開創(chuàng)性的檔案思想也對我國影響深遠[1]。特里·庫克于1969年至1977年先后求學(xué)于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xué)、卡爾頓大學(xué)、皇后大學(xué),分別獲得歷史學(xué)學(xué)士、碩士及博士學(xué)位。從求學(xué)經(jīng)歷來看,庫克的專業(yè)一直是歷史學(xué)。而歷史學(xué)作為一種敘事科學(xué)也最先被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所波及,這也為其日后對于檔案學(xué)的后現(xiàn)代主義詮釋埋下了種子。在其工作生涯當(dāng)中,庫克曾于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從事檔案的鑒定和處置工作,而后又擔(dān)任多部學(xué)術(shù)雜志主編及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xué)歷史系檔案學(xué)的客座教授,可見庫克在檔案實踐和檔案理論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貢獻。正是深厚的史學(xué)修養(yǎng)為庫克檔案學(xué)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豐富的實踐經(jīng)歷為他檔案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長期的學(xué)術(shù)編輯經(jīng)歷使他對檔案職業(yè)中存在的問題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加拿大獨具特色的檔案理念及做法為他開辟了理論研究的發(fā)展空間[2]。
后現(xiàn)代主義發(fā)端于20世紀(jì)40—50年代、傳播于60—70年代、盛行于80年代之后[3]。20世紀(jì)90年代,一些后現(xiàn)代主義學(xué)者將關(guān)注的焦點轉(zhuǎn)向檔案,其對檔案內(nèi)涵以及檔案起源的討論將檔案學(xué)拉入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的大潮之中,著名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家雅克·德里達于1996年出版的《檔案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4]。
生活在一個時時處處受到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挑戰(zhàn)的世界中,檔案人員也開始反思他們的理論與實踐。首先關(guān)注到受到后現(xiàn)代主義影響的檔案學(xué)家是加拿大的布萊恩·布羅斯曼(Brien Brothman)和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5]。布萊恩·布羅斯曼在1991年發(fā)表的文章《價值的秩序:探索檔案實踐的理論術(shù)語》(Orders of Value: Probing the Theoretical Terms of Archival Practice)以及1993年發(fā)表的文章《限制又限制:德里達的結(jié)構(gòu)主義與檔案制度》均提到了“后現(xiàn)代主義”。尤其在他1999年發(fā)表的文章《衰落的德里達:正直、張拉整體,以及結(jié)構(gòu)主義中的檔案保存》(Declining Derrida: Integrity,Tensegr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Archives from deconstruction)中,布羅斯曼對于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檔案熱》(Archive Fever)進行了探索性的討論。
二、特里·庫克后現(xiàn)代主義檔案學(xué)思想內(nèi)容
同為加拿大籍的特里·庫克也逐步發(fā)覺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傳統(tǒng)檔案學(xué)的影響,并將后現(xiàn)代主義總結(jié)為檔案職業(yè)范式轉(zhuǎn)換的基本原因之一。庫克于1994年發(fā)表的文章《電子文件與紙質(zhì)文件觀念:后保管與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中提出了“后保管”的觀點,并在第五部分中論述了“后保管”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關(guān)系。這些觀點在他1997年發(fā)表的文章《過去是開場白:自1898年以來的檔案思想史,以及未來范式的轉(zhuǎn)換》(What is Past is Prologue: A History of Archival Ideas Since 1898, and the Future Paradigm Shift)中得以延續(xù)。在這篇文章中,特里·庫克談到檔案人員不應(yīng)忽視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檔案學(xué)范式轉(zhuǎn)換的影響,并且認(rèn)為“后現(xiàn)代主義”與保管載體的變化、文件數(shù)量的激增等應(yīng)成為檔案學(xué)范式轉(zhuǎn)化的基礎(chǔ)。在1996年中國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的開場演講《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的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作用》中,特里·庫克也提出了他對于“現(xiàn)代主義”背景下的檔案學(xué)的質(zhì)疑:檔案人員在建造記憶宮殿時是怎樣廣泛地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呢?檔案人員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用什么樣的設(shè)想、觀點、概念、策略、方法和實踐呢?為什么采用它們?又為什么發(fā)生這些變化?我們?yōu)槭裁礃拥慕y(tǒng)治政權(quán)服務(wù)?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呢?是什么社會力量影響著我們的認(rèn)知模式……[6]
他于2001年發(fā)表的《檔案科學(xué)與后現(xiàn)代主義:舊意新解》和2002年與瓊·施瓦茨合作的《檔案、記錄與權(quán)力:從后現(xiàn)代理論到檔案現(xiàn)象》更是直面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檔案學(xué)理論與實踐的沖擊。他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使我們開始反思檔案和檔案工作者以及檔案職業(yè)的理論假設(shè),重新審視這些思想是如何塑造我們的身份認(rèn)同以及我們在社會中的作用的。
通過文獻梳理,本文將特里·庫克的后現(xiàn)代主義檔案學(xué)思想總結(jié)為以下三個部分。
1.后現(xiàn)代主義對檔案的本質(zhì)屬性發(fā)起挑戰(zhàn)。后現(xiàn)代主義者對檔案的本質(zhì)屬性,即“原始記錄性”提出疑問。眾所周知,檔案是在規(guī)范業(yè)務(wù)活動中產(chǎn)生的,是溝通過去與現(xiàn)在、溝通歷史與現(xiàn)實的最真實、可靠的媒介。而后現(xiàn)代主義學(xué)者認(rèn)為,檔案在生成之初就是有意識的構(gòu)建品,雖然這種意識可能通過半意識甚至是無意識的社會行為模式、組織過程來體現(xiàn)。正如特里·庫克在第十三屆檔案大會上談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歷史學(xué)家十分審慎地看待歷史進程,他們認(rèn)為社會記憶和歷史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就如法國歷史學(xué)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提到檔案的記憶和政治功能時說到:‘自古以來掌權(quán)者決定誰可以說話,誰必須保持沉默,在檔案材料的保管上也是如此。”[7]
權(quán)力與話語的斗爭問題也是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的核心。任何科學(xué)話術(shù)的創(chuàng)建、形成、建構(gòu)和擴散都離不開權(quán)力的力量,沒有脫離權(quán)力運作的純學(xué)術(shù)的話語體系[8]。處于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中的檔案學(xué)受到了質(zhì)疑:“在不能脫離權(quán)力控制的背景下,檔案是否還能保持“原始記錄”的純真和中立?檔案是否原本地反映了事件發(fā)生的本來面貌?這種反映是否全面和客觀?記錄者是否基于特定的目的進行創(chuàng)作?這種創(chuàng)作會不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的影響……”[9]以上的問題開始使檔案工作者認(rèn)識到檔案并不如詹金遜所說,是“無辜的副產(chǎn)品”。
2.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新時期檔案理論與實踐的啟發(fā)。在新的世紀(jì),由于受到文件記錄方式變化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雙重影響,檔案學(xué)應(yīng)該轉(zhuǎn)換其研究思路,從原來對單份文件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的分析轉(zhuǎn)向?qū)ε课募a(chǎn)的過程和功能的分析。隨著檔案管理的關(guān)注重點從記錄產(chǎn)品轉(zhuǎn)移到記錄產(chǎn)生的過程和行為,檔案學(xué)核心理論的構(gòu)想與專業(yè)實踐也必定會發(fā)生變化。
在理論構(gòu)想方面,特里·庫克在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上提出,檔案人員的關(guān)注焦點應(yīng)是“從以等級結(jié)構(gòu)中原始文件生成部門為中心的實體來源轉(zhuǎn)變?yōu)橐宰儎优R時甚至‘虛擬的機構(gòu)文件形成者的職能和業(yè)務(wù)活動為重點的概念來源”[10],即來源的本質(zhì)將從文件直接關(guān)聯(lián)于單一的、傳統(tǒng)的組織結(jié)構(gòu)變成反映文件形成的功能和過程的虛擬的、靈活的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組織結(jié)構(gòu),這樣的來源能夠適應(yīng)不斷變化的客戶、反映不同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文化。簡單來說,來源不僅反映結(jié)構(gòu)和地點,更反映功能和機構(gòu)。這種來源應(yīng)該是虛擬的,而不是實體的。檔案全宗理論作為來源原則在實踐中的具體應(yīng)用也同樣發(fā)生了變化。傳統(tǒng)的全宗理論起源于轉(zhuǎn)讓、整理和收集一組檔案的過程中,按照某種規(guī)律形成的靜態(tài)的物理順序。但現(xiàn)在,它已經(jīng)發(fā)展為以文件的體系和功能為核心,反映多重形成者和利用者的動態(tài)的虛擬整合。這種全宗能更精準(zhǔn)敏捷地捕捉信息社會中的檔案文脈關(guān)系。
在專業(yè)實踐方面,檔案人員應(yīng)認(rèn)識到,在技術(shù)革新的背景下,檔案的儲存介質(zhì)已經(jīng)由實態(tài)的紙張、膠片轉(zhuǎn)變?yōu)樘摂M的數(shù)據(jù)儲存庫或軟件程序。傳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和背景信息由元數(shù)據(jù)來體現(xiàn),并且當(dāng)文件的系統(tǒng)聯(lián)系和使用狀況發(fā)生變化時,這種元數(shù)據(jù)也會隨之發(fā)生變化。記錄不再是長期固定的,而應(yīng)該是動態(tài)的。記錄不再是一種被動的客體,而應(yīng)該是在個人、組織和社會中不斷發(fā)揮主動作用的主體。原始順序不再指按某種登記原則或分類標(biāo)準(zhǔn)而賦予檔案的實體排列順序,而是成為一種借助軟件系統(tǒng)形成的概念化的產(chǎn)物。這種文件存儲的地點是隨機的,是沒有實體意義的,它可以為不同的使用者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通過不同的形式所使用。原始順序能夠滿足不同的工作需求,并反映出工作對檔案需求的多層次性。人們可以把一組同樣的數(shù)據(jù)按照不同的方式排列,以滿足不同的用戶需求。在這種背景下,檔案人員不應(yīng)再局限于對實體檔案及全宗的整理和著錄,而是更注重檔案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更注重理解檔案的背景、環(huán)境,同時把相關(guān)的檔案體系和功能性的元數(shù)據(jù)相結(jié)合,作為描述檔案的工具。
3.后現(xiàn)代主義重新塑造檔案學(xué)范式。受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影響,特里庫克深入梳理了1840年以來檔案學(xué)理論與實踐發(fā)展歷程,并借助托馬斯·庫恩的范式思想將西方檔案學(xué)的發(fā)展總結(jié)為歐洲檔案學(xué)觀念與戰(zhàn)略的四個范式,即證據(jù)、記憶、認(rèn)同、社會[11]。證據(jù)范式起源于法國大革命,在民主與自由呼聲中作為國家公共機構(gòu)的檔案館誕生了,盡管這些檔案館中保存的主要是官方檔案。此時檔案工作者的職責(zé)是對司法遺存按其背景信息進行整理和編目,其工作信條是“維護證據(jù)的神圣性”。記憶范式發(fā)展于20世紀(jì)30—70年代,強調(diào)檔案作為歷史和文化遺存的記憶資源。此時檔案工作者已變成積極的檔案塑造者,透過學(xué)術(shù)歷史這個過濾器有意識地構(gòu)建公共記憶。認(rèn)同范式是在檔案學(xué)專業(yè)學(xué)者的身份認(rèn)同與后現(xiàn)代思潮的雙重力量下催化形成的,檔案開始更直接地反映社會生活,呈現(xiàn)其復(fù)雜性和模糊性。此時的檔案工作者已經(jīng)從文獻管理中解脫出來,成為幫助社會通過檔案記憶資源形成多元認(rèn)同的中介人。21世紀(jì),社會/社區(qū)范式正呼之欲出。面對日益復(fù)雜的社會生活,我們認(rèn)識到館藏收集能力的不足——“沒必要把所有的檔案產(chǎn)品收集到我們的檔案館”。從而鼓勵檔案人員放棄“專家、控制及權(quán)力”而成為輔導(dǎo)員、宣傳員與教練員參與社群建檔工作。在后現(xiàn)代的背景下,檔案工作者們也意識到目前檔案館收集范圍的狹隘與局限。檔案已從人類行政活動被動產(chǎn)生的遺留物轉(zhuǎn)變?yōu)闃?gòu)建人類文明與集體記憶的積極元素。這種范式或觀念的轉(zhuǎn)變引導(dǎo)了檔案實踐領(lǐng)域的變革。
但庫克也清醒地認(rèn)識到,后現(xiàn)代觀念的影響并不是檔案學(xué)科的原則重新塑造的唯一原因,檔案館服務(wù)模式的變化、記錄的本質(zhì)以及其他因素,聯(lián)合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觀點,構(gòu)成了檔案、檔案機構(gòu)、檔案職業(yè)轉(zhuǎn)變的基礎(chǔ)。
三、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帶給檔案學(xué)界的啟示
1.對檔案本質(zhì)和“檔案科學(xué)”形成的重新認(rèn)識。后現(xiàn)代主義使人們對科學(xué)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那些曾經(jīng)被認(rèn)為是客觀的、公正的、無私的東西,人們開始認(rèn)識到其中的主觀成分。檔案科學(xué)也不例外,知識和理論的產(chǎn)生是建立在已經(jīng)預(yù)設(shè)了絕對正確的理論基礎(chǔ)上,但后現(xiàn)代主義讓我們對“真理”的絕對正確產(chǎn)生懷疑——真理或許是特定的、相對的,并非普遍、絕對的,因此假設(shè)的真理未必絕對正確。用庫克的話來講,就是要研究:“我們檔案人員在建造記憶宮殿時是如何反映廣泛的社會現(xiàn)實的呢?檔案人員自覺和不自覺地采用什么樣的設(shè)想、理論、概念、策略、方法和實踐呢?為什么采用它們?它們多年來有何變化?又為什么發(fā)生這些變化?我們?yōu)槭裁礃拥慕y(tǒng)治政權(quán)機構(gòu)服務(wù)……”[12]
對于檔案工作來說,不同時間、地區(qū)和發(fā)展階段的檔案管理原則均存在著差異,從任何一種檔案實踐中總結(jié)、歸納、概括的理論都并不足以指導(dǎo)全部的實踐。從這種角度出發(fā),檔案工作者應(yīng)當(dāng)冷靜地反思自身的職業(yè)形成,并形成發(fā)展的、不斷更新的檔案職業(yè)規(guī)范。
2.正視電子文件對檔案學(xué)的沖擊。電子文件對于檔案界發(fā)起的挑戰(zhàn)是檔案工作人員重新定義職業(yè)范式的根本依據(jù)和出發(fā)點。在未來迅速變化和組織錯綜復(fù)雜的信息背景下,將產(chǎn)生大量的、分散的紙質(zhì)文件和大量短暫的、虛擬的文件。檔案工作者作為典型的信息工作者,也必須要重新定義自身的工作方式和社會角色。
對此,特里·庫克在其1994年發(fā)表的文章《電子文件與紙質(zhì)文件觀念:后保管與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中介紹了后保管時代檔案工作的核心:檔案工作者應(yīng)該把工作方向和研究的重點由檔案實體轉(zhuǎn)向其形成過程,從而轉(zhuǎn)向文件形成過程中的具體的舉措、規(guī)劃、職能關(guān)系等等。這樣一來,我們鑒定、保護、著錄、提供利用的對象將不僅僅只是一些事實和數(shù)據(jù),而是揭示整個活動來龍去脈的事實還原[13]。同時信息與儲存媒介的可分離性也應(yīng)得到重視。在電子文件時代,實體介質(zhì)和文件的記錄將會在幾十年或者幾個世紀(jì)的時間后變得毫不相關(guān),因為記錄本身會被遷移,實體儲存媒介會不斷惡化。重要的“原始”記錄必須要在新的軟件中重新配置,以保持其記錄的功能以及其證據(jù)價值,這個問題檔案學(xué)界也需加以重視。
3.建立保存完整集體記憶的公共檔案館。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權(quán)力的解構(gòu)以及去中心化的觀點,又為檔案實踐的發(fā)展擴展了空間。特里·庫克提出要構(gòu)建多元的社會記憶,塑造多樣化和差異化的檔案,要關(guān)注邊緣和弱勢群體,記錄更廣泛的歷史,要求檔案工作者由被動的文件遺產(chǎn)的保管者向積極的社會記憶的塑造者轉(zhuǎn)型。檔案工作者同時要鼓勵大眾為集體記憶的構(gòu)建貢獻力量,即“人人成為檔案工作者”。
而檔案館應(yīng)該成為包含全世界歷史和記憶的有機實體。讓·皮埃爾·瓦洛寫到,我們“要為歷史建立一個生動的記憶儲存空間”。他強調(diào):“這項建筑工作是壓在檔案工作者身上的沉重負擔(dān),因為檔案包含了國家和民眾記憶的核心,這種來自過去的持續(xù)經(jīng)驗帶給我們一種幸福感、一種根源感、一種歸屬感和一種身份感。”[14]
這種變化也鼓勵普通的百姓利用檔案,檔案館不應(yīng)是一個私人的花園,而應(yīng)該成為一個保存著可信的社會記憶的莊嚴(yán)的公共機構(gòu)。檔案人員要盡可能地為社會服務(wù),而不是為政權(quán)服務(wù)。
參考文獻
[1]黃霄羽.致敬特里·庫克——特里·庫克的專業(yè)經(jīng)歷、成就和影響評析[J].中國檔案,2014(8):68-71.
[2]閆靜,徐擁軍.后現(xiàn)代檔案思想對我國檔案理論與實踐發(fā)展的啟示——基于特里·庫克檔案思想的剖析[J].檔案學(xué)研究,2017(5):4-10.
[3] 屈菲.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演進及影響[J].北方論叢,2007(3):127-130.
[4]何嘉蓀,馬小敏.德里達檔案化思想研究之一——從檔案概念說起[J].檔案學(xué)通訊,2015(4):23-27.
[5][9][14]Terry Cook. Archival science and postmodernism: new formulations for old concepts[J]. Archival Science, 2001, Vol.1 (1), pp.3-24.
[6][7][10]特里庫克.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影響[R].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文件報告集,1996.
[8]嚴(yán)翅君 韓丹 劉釗.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家關(guān)鍵詞[M].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147.
[11]特里·庫克,李音.四個范式:歐洲檔案學(xué)的觀念和戰(zhàn)略的變化——1840年以來西方檔案觀念與戰(zhàn)略的變化[J].檔案學(xué)研究,2011(3):81-87.
[12] 陸陽.后現(xiàn)代主義對檔案學(xué)理論的影響[J].檔案管理,1999(2):9-10.
[13] 何嘉蓀,史習(xí)人,章燕華.后保管時代檔案學(xué)基礎(chǔ)理論研究——簡評文件構(gòu)成要素論[J].檔案學(xué)研究,201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