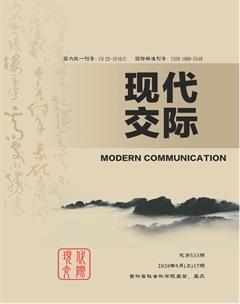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研究
孫偉
摘要:作為老年人救濟申請權的特殊權利形態,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對老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作用尤其特殊。與一般救濟申請權不同,緊急救濟申請權的“緊急”屬性在客觀上產生了三種法律隔絕效果,這使得在適用一般救濟申請權時暢通無阻的意思自治理論、民事代理制度、訴訟救濟機制和司法調解救濟機制在處理特殊救濟申請權時產生了適用不能的危局。為了破解危局,全面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通過對法律謙抑性價值和法律維護公序良俗之功能價值的論衡,構建了意思推定的理論設想,并基于該設想為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利機制在民事及行政救濟領域提出了相應的完善路徑。
關鍵詞:老年人 緊急救濟申請權 權益保障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17-0062-03
長期以來,構建完整而精密的老年權益保障法律體系一直都是我國老年立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標,而明確老年人救濟申請權則是完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律體系的基礎和前提。目前我國已經通過立法構建了老年人救濟申請權制度,然而,該制度在實際適用方面卻有著明顯的局限性,這種權利局限主要表現為“緊急”情況下的范圍不可及性。為了擴大老年人救濟申請權的實際適用范圍,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構建與細化應當為相關立法所重視。
一、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概念
老年人救濟申請權是指老年人基于《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所享有的在受到家庭成員的暴力、遺棄和虐待時,向被侵害人單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等有關機構尋求救濟,以期擺脫不法侵害的權利。而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是老年人救濟申請權在特定情況下的特殊權利形態,其縱向歸屬于老年人救濟申請權。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雖然歸屬于老年人救濟申請權利,但其“緊急”屬性的特殊性決定了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又區別于一般情形下的救濟申請權,緊急救濟申請權與一般救濟申請權相比,呈現出了特別狀態下的特殊性。
認識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在特別形態下的特殊性需要正確定位“緊急”的概念。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中的“緊急”是指老年人在無法客觀表達自我意思時的緊急狀態。這種“緊急”狀態在客觀上產生了三種法律阻絕效果。
第一,它排除了意思自治原則的適用。老年人在客觀無法表達自我意思時,意思自治原則將在客觀上執行不能,此時的權利主體無法通過法律行為引發權利行使效果。
第二,它排除了民事代理法律制度的適用。傳統民事代理法律制度的適用可以緩解老年人在意識清醒,但行動不便時的權利行使危局。但是民事代理法律制度的適用前提是被代理人通過客觀行為向代理人表達了代理訴求。這也就意味著難以客觀表達自我意思的老年人無法通過傳統的民事代理法律制度得到有效救濟。
第三,它排除了訴訟救濟機制和司法調解救濟機制的適用。訴訟救濟機制和司法調解救濟機制比行政救濟機制更具程序上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決定了訴訟救濟機制和司法調解救濟機制無法于“緊急”狀態下發揮效用。因此,本文中的緊急救濟申請權僅指行政救濟機制中老年人享有向行政機關申請行政救濟的權利。
二、我國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法律依據
我國現行《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條和第七十三條對老年人救濟申請權的行使主體、行使對象和行使前提都做出了較為細致的規定。基于這兩條規定,老年人救濟申請權的行使主體是被侵害人本人;救濟申請權的行使對象是人民法院及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等有關組織機構;權利行使前提是老年人受到了以虐待、遺棄、家庭暴力為主要內容的現實不法侵害。由此可以看出,老年人救濟申請權是主動性權利,它以老年人的救濟申請行為為觸發權力運行機制的前提,其運作機理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和行政法的法律優先原則。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作為老年人救濟申請權的特殊權利形態,其行使主體、行使對象和行使前提與一般情況下的老年人救濟申請權一致。
三、我國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運作存在的問題
1.緊急救濟申請權運作客觀執行不能
在民法意思自治原則和行政法法律優先原則的影響下,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法律定位是主動性權利,其行使的前提是老年人受到了以虐待、遺棄、家庭暴力為主要內容的現實不法侵害。但是,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法律定位卻與緊急救濟申請權的客觀存在前提相沖突。一方面,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運作的客觀前提是作為被侵害人的老年人無法表達自我意思,也即無法通過語言及動作實現自我表達或是委托他人代為表達。這種表達困局使得緊急救濟權的運作在救濟請求發出時即告終結。而另一方面,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法律定位又為權利行使劃定了嚴格的主體范圍,也即緊急救濟權的行使主體只能是老年人或是老年人委托的代理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法律定位與客觀前提之間的沖突使得緊急救濟申請權運作存在客觀執行不能的窘境。
老年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伴隨著自身各方面機能的下降,在自身權益維護方面也不斷遭受到侵犯[1]。而另一方面,大部分老年人在面對自己的權利遭到侵害時,他們的選擇方式則是能忍則忍[2]。這使得很多遭受不法侵害的老年人不愿起訴子女,更不愿意在“非緊急”情況下行使救濟申請權。然待緊急情況出現時,老年人卻又無法向有關機關表達救濟訴求,也就無法獲得法律的有效救濟。這種現象在廣大農村地區更為常見,就目前而言,法律所規定的救濟申請權力運行機制尚未發揮到最優狀態。
2.緊急救濟申請權運作缺乏現有法律制度的保障
緊急救濟申請權現有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雖然相關法律對老年人救濟申請權的行使主體、行使對象和行使前提均做了較為細致的規定,但是,這兩條規定卻忽視了救濟申請權在“緊急”狀態下的客觀適用問題。如果僅僅適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規定,那么,“緊急”狀態下的老年人救濟申請權機制恐將形同虛設。事實上,解決老年人緊急救濟權行使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通過法律制度幫助“緊急”狀態下的老年人有效打通申請意思與申請行為聯系的閉路,幫助老年人擺脫現實而緊迫的不法侵害。然而,就總體上來說,涉老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需要在立法層面做出更大的努力[3]。
3.緊急救濟申請權的執行力缺乏現有理論的支持
目前,我國法學理論界對青少年法學、婦女法學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系統,但對老齡法律問題研究還不夠重視,成果也不多,老齡法律研究在我國還是個有待開發的新領域[4]。研究成果的匱乏使得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執行力缺乏現有民法理論和行政法理論的支撐。
緊急救濟申請權的執行力缺乏現有民法理論的支持。我國民法理論尤其強調意思自治原則,也即權利的行使應當忠實于權利人的真實意思。基于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公民有權行使自己的權利,也有權放棄自己的權利。事實上,真正觸動法律關系變動的并非公民頭腦中的意識,而是意識作用于行為的意思表示,公民權利的行使應當以必要的意思表示為前提。然而,公民的法律表示行為往往受到相當一部分客觀要素的制約。為了實現意思自治理論的現實化、減少這些客觀要素的影響,我國法律還規定了民事代理等制度以銜接理論與現實的落差。但是,即使法律規定了民事代理制度,也無法排除客觀要素對于意思自治理論現實化的影響,因為民事代理法律效力的產生應以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為必要。由此可見,“緊急”情態下的老年人無法通過現有的民法理論得到有效救濟。
緊急救濟申請權的執行力缺乏現有行政法理論的支持。我國行政法理論尤其強調“控權”,行政法本身也是控權法。由此我國行政法確立了法律優先原則,并基于該原則,我國明確了行政機關“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基本態度。然而,老年人的救濟申請權是主動性權利,該權利需要老年人自己行使或是委托他人行使,如果老年人不行使救濟申請權,這種對于權利的不作為將被視為放棄權利的行為,行政機關無權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干預老年人的權利放棄行為。由此可見,“緊急”情態下的老年人無法通過現有的行政法理論得到有效救濟。
四、老年人緊急救濟申請權的完善路徑:基于意思推定的理論構想
1.意思推定理論構想的主要內容
意思推定理論的主要內容是,當老年人處在無法表達自我意思的緊急狀態時,在“行使權利”與“放棄權利”的選擇中推定無法表達自我意識的老年人選擇前者并積極尋求他人代理其行使《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賦予老年人的救濟申請權。設立意思推定原則的目的在于擴大緊急救濟申請權的行使主體范圍,進而達到對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進行救濟、對家庭成員的不法侵害行為進行懲處的現實目的。
2.意思推定理論構想的邏輯推論
當老年人處在無法表達自我意思的緊急狀態時,老年人對于是否行使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意思處在客觀不可知的特殊狀態。在這種特殊狀態下,一方面,法律不應當通過緊急狀態出現前老年人放棄行使申請權的意思表示推定老年人出現緊急狀態后依舊選擇放棄行使權利。另一方面,法律也不應當僅就“生命至上”原則直接推定老年人在這種特殊狀態下選擇行使救濟申請權。就客觀現實角度而言,法律推論老年人在緊急狀態下選擇行使權利和選擇放棄權利都是存在疑義的,這就使得法律推論形成了邏輯閉路。筆者認為,法律價值的判斷方法或可為疏通這一邏輯閉路另辟蹊徑。就價值判斷的角度而言,解決老年人緊急救濟權行使問題的關鍵在于衡量法律的謙抑性價值與法律維護公序良俗的功能價值。筆者認為,在緊急救濟申請權的行使方面,法律的謙抑性價值主要體現于法律不應當在老年人真實意思不可探知的情況下擅自對老年人的真實意思進行推斷。這種謙抑性實際上抑制了法律在“老年人行使權利”與“老年人放棄權利”之間做出偏向性選擇。然而,法律不在這兩種判斷之間進行選擇將在客觀上導致“老年人放棄權利”成為適用我國法律的唯一結果,這與客觀事實顯然不符,因為老年存在著兩種意思可能,而非一種。另外,法律謙抑性的功能在于阻止法律對兩種選擇進行判斷,其直接目的在于維護私權,阻卻公權對于私權的不正當滲入。然而,阻止的結果卻是使得法律被迫做出了“老年人放棄權利”的選擇,這本身便與法律的謙抑性所堅持的價值目標不符。
在緊急救濟申請權的行使方面,法律維護公序良俗的功能性價值主要體現為:法律應當在老年人真實意思不可探知的情況下基于“老年人行使權利”這一選擇符合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而推定處在緊急情態下的老年人選擇行使救濟申請權并積極尋求他人代理其行使救濟申請權。雖然法律無法判斷老年人具有行使緊急救濟申請權的意思,但是法律卻可以明確,如果老年人在“緊急”狀態下選擇行使救濟申請權將會對公序良俗起到極好的維護作用,因此法律肯定了在特殊情況下推定“老年人行使權利”的正當性。當“私權行使與否”無法被推知時,“意思自治”將客觀執行不能。這時,為了擺脫因“意思自治”客觀執行不能所造成的危局,充分發揮法律定紛止爭的作用,法律應當考慮通過對于其他的法律價值的衡量走出危局。在上述情況的討論中,法律所具有之維護公序良俗的功能性價值便是解決“意思自治”客觀執行不能的關鍵所在。
如果推定當老年人處在緊急狀態時,其在“權利行使與否”的選擇中選擇前者并積極尋求他人代理其行使《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條和第七十三條賦予老年人的救濟申請權。那么,緊急救濟申請權的實際行使主體將從被侵害人本人和其委托的代理人擴大至一切愿意接受“緊急”狀態下老年人委托請求的法律主體。接受委托的主體便可以通過民法的民事代理制度代理老年人行使緊急救濟申請權,進而觸發公法的權利保護機制。
3.意思推定理論構想的現實化路徑
保障公民的權利是法律的重要任務和法的價值之一[5]。為了擺脫老年人在緊急情況下“意思自治”客觀執行不能的危局,發揮民法公序良俗原則的維穩作用,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應當對處在緊急情況下的老年人做出“行使權利”的意思推定,進而將緊急救濟申請權的實際行使主體從被侵害人本人和其委托的代理人擴充至一切愿意接受“緊急”狀態下老年人委托的法律主體。事實上,意思推定本身就是對民法意思自治的突破,之所以在老年人緊急救濟權方面做出對民法意思自治原則的突破性規定,筆者主要基于兩方面的考慮。其一,處在緊急狀態下的老年人無法通過意思表示行使救濟申請權,也即陷入了“意思自治”執行不能的危局。由此可見,傳統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在緊急狀態下已經陷入了失靈狀態。其二,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則要求子女在老年人處在危急狀態時對老年人施以有效救助,當子女違反救助義務時,效率高而見效快的行政救濟手段應當發揮應有的作用。在特殊情況下貫徹意思推定原則,并不意味著在一般情況下也應貫徹意思推定原則,意思推定理論的適用是被嚴格限制的,只有在老年人處于無法表達意思的危急情況下才能適用。
參考文獻:
[1]楊軍,羅遐.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現狀與應對策略研究:基于安徽省的調查數據[J].安徽行政學院學報,2017,8(5):108-112.
[2]劉曉梅,汪宇梅,成虹波.居家養老中老年人權益保障問題及對策研究[J].長春大學學報,2019,29(1):1-6.
[3]梁紅梅.論老年人權益的法律保障[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7,28(20):175-176.
[4]吳國平.老年人權益的法律保障研究[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6(3):28-33.
[5]蔡宏偉.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律制度構建研究:以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視角[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6(1):16-19.
責任編輯:趙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