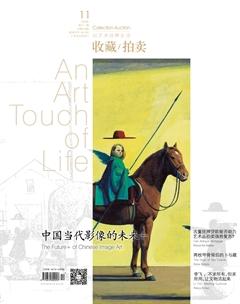西遼花錢初探
段立瓊 朱滸



辯證看待西遼花錢
首先,要進行一下科普。西遼(1124-1218)是古代契丹族建立的政權。創立者耶律大石,原系遼朝貴族,因與天祚帝政見不合,遂于遼朝滅亡前夕的1124年率部西走,1130年到達葉密立(今新疆額敏縣),在這里修筑城池。1132年,耶律大石稱帝,改元延慶。建立了西遼王朝。隨后耶律大石西征東伐,相繼征服東、西喀喇汗王朝和中亞諸國,不久又臣服高昌回鶻,其疆域東起蒙古高原的土拉河,西至中亞花刺子模海(今咸海),南到昆侖山,北達巴爾喀什湖以北。西遼王朝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它將中原漢文化傳播至中亞地區,西遼王朝創建者耶律大石本身就是一位具有高度漢文化修養的契丹貴族,史稱其“通遼、漢字”天慶五年(1115)考中進士。因此,有學者稱,西遼時期是繼漢、唐之后漢文化向中亞傳播的又一高峰。
但學術界一直對西遼的研究有所欠缺,而這一王朝的錢幣更是模糊不清。從現存實物與資料來看,西王母人物生肖花錢,是業內公認的遼代花錢。存世量并不多。而帶掛孔應該是此類錢幣的完整原始形態。也不排除存在帶掛與不帶掛兩種形態。光從錢幣部分看,直徑5.5厘米,是遼代器具中一個經常出現的尺寸,不止在遼代花錢中常見此尺寸,在遼代官印中也存在5.5厘米現象。這一尺寸有何具體含義與用意依舊成迷,而一些帶有中亞元素西王母人物生肖花錢能否被定為西遼花錢,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從現存一枚西王母生肖人物花錢( 圖1) 來看,中間是一個主尊,左側有一個供養人持下跪姿態,右邊有一個類似樹葉或狐貍尾巴的物件。穿左右,各自布列三個供養人,穿下三人,左右協侍,中間為尊者,但體格比穿上主尊略小,可見整體而言,穿上主尊為整個畫面的最尊貴者。
同類花錢多自東北三省及內蒙古赤峰一代,屬于遼錢范疇。還有一類帶有“胡騰舞”圖案的花錢(圖2、圖3),學者劉春聲認為,它們非但屬于遼代范疇,也屬于西遼錢范疇,原因是它的出土地點在西北地區,第二個是“胡騰舞”花錢背后的十二生肖的形象和西王母人物花錢背面十二生肖的圖像十分神似。
不過,同類型花錢在多地出現與收藏中轉手流動是有關的。花錢收藏家尹寧認為,假設一類花錢,如果中亞出現,東北也出現,則應該不是西遼,很可能是蒙元的。如果確切出土地就是中亞,其他地方不出,則西遼的可能性上升,但也需要排除是蒙元早期的。蒙元早期蒙古草原上早已漢化到一定程度了。西遼之前中亞的主人是塞爾柱帝國,屬于伊斯蘭文化,這些花錢和伊斯蘭文化不搭界,可排除掉。西遼被乃蠻部所滅,過了沒幾年乃蠻被蒙古所滅。如果東北也出現的話,則可以斷定不是西遼的,東北不在西遼的版圖內。
也有觀點認為,錢幣的制作地與錢幣的流通地應該辯證看待,即制作地未必一定是流通地,可能是遼代制作,帶去西遼使用,也可能最初的時候,西遼還在使用原來遼代的模具,但是逐漸被當地的文化轉變了風格。這都是可能的,有些花錢一看就是中亞風格,很可能是西遼。但是像一些中亞風格不明顯的錢幣比如西王母錢,也不能排除隨著遼代殘部往西去的過程當中,途經遺留也是可能的,西遼錢一是西遼鑄造,一是西遼使用,這要分開。至于鑄造中是否因襲,還是創造,可以再研究。
西遼花錢判斷依據
那么,真正在西遼統治范圍內,生產的花錢到底有多少品種,持有多少特色風格,都是收藏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困惑。有一種西遼花錢從圖案上來看,一面是龍(有別于我們常見的遼代龍),另一面可能是野豬與棕熊(圖4)。此外,由于西遼當時有自己的“行用錢”,“胡騰舞”“胡旋舞”(圖5)這種題材在中亞地區也是很常見的。這些結合中原與中亞元素的花錢都體現出西遼在文化上的融合,也成為西遼花錢的重要判斷依據。
此外,近年拍賣會也拍賣過一些出自中亞的西遼錢(圖6、圖7、圖8),花錢收藏家胡堅對其與宋遼錢做了檢測,發現宋遼錢總體上看成分比較單一,常見的是鉛、錫、銅三種元素。而對西遼錢的檢測來看,里面普遍含有鋅元素。因此,某些獨特成分確能指示年代、地域等特征。比如,鋅的含量,應該是一個可參考的指標,同期遼錢以及金、元鑄幣中鋅含量極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自明始,鋅含量才逐漸上升并趨穩,到清代成為鑄幣成分中的一個主要配比
古代有一種珍貴的礦石叫“鍮石”,是一種銅鋅合金,從西域進貢過來的,在明朝做宣德爐也有用到,是暹羅從泰國進口的。唐代有記載,當時很多佛像是用“鍮石”做的,包括宋元時期的一些高檔的金屬制品也是。因此,從成分來看也表明這類錢應不是中原。
遼代西王母花錢應為道教題材
西遼花錢的另一爭論點,在于上文所述的西王母圖案到底為佛教還是道家題材。關于這一問題,有學者認為,此錢應該并非佛教范疇,它雖然采用了佛的雙手合十的姿勢,也不一定就是“佛”,道教也有這種姿勢。其屬性確定還要進行圖像學的分析,這個圖像中上側人物明顯是頭上有某種裝飾,應是一個女性。佛教圖像中主尊不太會有女性的,菩薩不會當主尊,而且它上下各有一個神,是典型的配偶神,應該是西王母和東王公,上面是西王母,下面是東王公。
每一種周圍有七個供養人,是我們常說的“五男二女”(圖9),尤其中央明顯是一男一女,女性頭上戴頭飾,男性是光頭,可以確定是孩童。其背后圖像—十二生肖也有道教的屬性,十二生肖在宋遼時期的民間信仰中也是道教題材。道教和佛教在早期相互排斥,后來為了發展,道教在形式上受到佛教的影響,比如雙手合十的手印也是一種例子。
西王母圖案花錢是佛或道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確定每一個人物的性質,究竟是東王公、西王母,還是佛像。如果是佛的話,是什么佛?是如來佛、彌勒佛?還是菩薩之類的,這個比較重要。另外,常說的嬰戲題材其實就是“五男二女”的來源,在北魏時期就很多,如“永安五男”。北魏時期鮮卑人建立的“東胡”,遼,也就是契丹,民族源于東胡的鮮卑部落,所以這種題材是鮮卑傳統,同時又有儒家的色彩,儒家講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所以總體上來說應是儒家和道家融合的結果。
學者劉春聲曾經撰文專題探討過錢幣上出現“勝”的符號(大泉五十、五銖錢等)或者西王母形象,他指出,如果我們確定這枚錢上面是西王母,下面是東王公,那么它就是道教或者是中國早期神話崇拜的人物,那其他的幾個人物就不能考慮是佛教中的了,應該從世俗的角度去看。如果從西遼政權來看,它偏安一隅,從北邊跑到西邊在那里割據,地位岌岌可危。從這個生存的角度講,是五男二女的話也是說得過去,西遼政權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是希望人丁興旺、多子多福。
收藏家尹寧從本錢風格中提出了與唐代藝術的繼承關系,他指出九子母錢是公認的遼代花錢,那么像胡騰舞花錢這樣“ 有遼風”,出自中亞西遼疆域,就離西遼近了。遼代藝術風格直接繼承自唐代,或者說和唐代是一脈相承的。十二生肖在唐代,特別是中晚唐已經大行其道了,而且道教肯定也輻射到了契丹,所以遼代花錢出現道教人物也不奇怪。而遼代是晚唐東北區域文化的自然延續和自由發展。故其藝術相較宋代保存了更多的唐風。藝術史中有邊疆文化延遲說,西王母在邊疆也正常。
上述幾點僅為根據當前實物資料對西遼花錢作出的初步探討,其背后仍有許多謎題值得進一步研究,隨著學術界對西遼文化的研究不斷深入,西遼花錢背后蘊藏的豐富歷史信息,也將不斷被解讀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