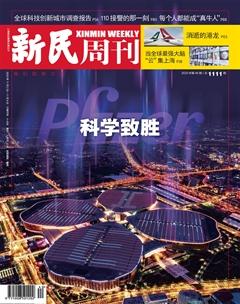內卷化的修辭與顧影自憐
沈彬

想不到10年前評論圈里借用的學術術語——內卷化,這兩天徹底破圈了,成為了全民熱詞。
單位競爭越來越激烈了,大家都憋著不肯下班,是內卷化;公職單位考試題目越來越難,越來越刁鉆古怪,是內卷化;大學生 “績點為王”,也是內卷化;培訓機構忽然打出的廣告旗號,就是“你來就培養你的孩子,你不來,就培養你孩子的競爭對手”,更是內卷化。
沒有創新之下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有人類學家將之稱為 “不斷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環”, 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
內卷化其實是發達國家、成熟社會的常態。
從“社畜”“隱形貧困”“小鎮做題家”到這幾天大火的“打工人”,“城會完”又掏出了一件顧影自憐的小道具——在“我怎么長得那么好看”的魔性BGM中,發出靈魂的叩問:我為什么沒有錢?我為什么還要去上班?
其實,內卷化有修辭的成分,也有真問題所在。
內卷化所呈現的賽道越來越擁擠,競爭越來越激烈,這背后很多問題:有的是社會發展階段的問題,有的是社會公平問題,也有代際的問題,不應該全歸因于“資本集中”“階層固化”的名頭。
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面臨巨大的人才缺口,所以在那個時候文憑顯得特別吃香,大學生顯得特別金貴。在1980年代,隨便哪個大學的法科生畢業之后,進了當時“退伍軍人當法官”為主流的政法系統,當然就是業務骨干。如今,名校的法學碩士可能只是進入一般法院的敲門磚,進去之后還得老老實實地從訂案卷做起,做到獨當一面的審案法官,還得等好些年之后。女作家王小鷹有一部小說叫《你為誰辯護?》,在1980年代曾經紅極一時,小說當中為殺人犯辯護的女律師,居然是一個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這個現在看來就是一個笑話。
如果從“代際公平”角度說,同樣是法學院的畢業生,一個一進單位就獨當一面,一個還在做打雜。這個能歸結于流行詞“代際剝削”嗎?是前一代故意為后來者“挖坑”嗎?其實,還是源于中國在這40年中的跨越發展,大學的大門越開越廣,大學生的身份不再“金貴”,學歷事實上在貶值。不是說你業務能力、水平不如30年前的大學生,而是人才供需關系發生了改變。
所以,當下年輕人,有很大的落差感,緣于時代的落差,還緣于社會發展路徑日益明晰,競爭賽道更“堅固”,而旁逸斜出、打破天花板的機會越來越小。這也是“打工人”“小鎮做題家”背后那股喪喪的氣息所在,似乎打工沒有出路,996也沒有福報。
這背后還是中國從之前的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經濟進入L 形底部,之前社會經濟高速乃至“野蠻”成長,科技樹、商業模式高速分蘗、房價的高企,你很容易就站上了潮頭,坐上向上的電梯;而如今社會的競爭更庸常化,一夜暴富的機會更少了,賽道更擁擠了。
但是,內卷化其實是發達國家、成熟社會的常態,很多移民到海外的中國人的一個感覺,就是“海外適合養老,發財機會還在中國”。只是當下中國的機會(風險)紅利也在齊常化。內卷化也不是“不能退出的競爭”,世界上沒有不能退出的比賽,只是你的競爭比30年前的上代人更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