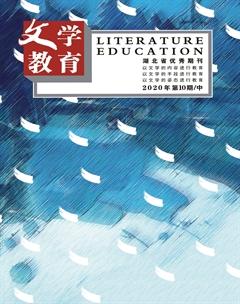黑人族內女性刻板形象表征與顛覆
內容摘要:存在于黑人種族內部刻板形象給黑人女性造成身心傷害,加劇了她們社會地位的惡化。奇爾德雷斯的《荒野葡萄酒》戲劇化地表現了黑人族內強加給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并通過女主人公對刻板形象的顛覆抨擊了黑人中產階級的虛偽和偏見。
關鍵詞:刻板形象 表征 顛覆
從美國奴隸制一開始,白人主流社會就給非裔強加上多種負面刻板形象,變成了扭曲和篡改黑人文化及其表征的政治工具。然而,刻板形象還存在于黑人種族內部。上世紀60、70年代的黑人權力運動中,一些黑人男性作家結合白人社會強加給黑人的刻板形象,把黑人女性描寫成女家長、不道德、專橫、無助的形象,重新定義和縮小了黑人女性的角色。[1]一些黑人女性也內化了這些刻板形象。許多黑人女性劇作家對此做出了回應,奇爾德雷斯的《荒野葡萄酒》是最具代表性的戲劇之一。該劇審視了黑人族內彼此看待對方、反抗白人時出現的貶損女性的刻板形象及其給她們造成的身心傷害,呈現了女主人公對刻板形象的顛覆。
一.黑人族內女性刻板形象表征
該劇寫于1969年,正值黑人權力運動高潮階段,講述的是1964年的一次騷亂期間發生在一位黑人藝術家比爾的公寓里的故事。比爾計劃完成以“荒野葡萄酒”為主題的三幅畫,涉及黑人女性身份。他目前已經完成第一幅“黑人少女時代”和第二幅“非洲母親”,她們“就是那個女性……就是天堂……完美的黑人女性。”[2]
畫像中的少女是天堂的體現,代表男性對女性的幻想,暗示比爾理想化意識中的黑人女性形象。這種理想化的黑人女性形象實際上是黑人族內強加給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具有明顯的欺騙性。比爾并未捕捉到真正的黑人女性特質。而他尚未完成的第三幅則是明顯帶有黑人族內性別和階級偏見的女性刻板形象,表現的是迷失的黑人女性,“那種草根小妞……迷失的女人……無知、沒有女人味、粗魯、野蠻、庸俗……一個可憐、愚蠢的小妞……不新潮。”[2]這充分證明了黑人男性的權力和對黑人女性的歧視和貶損。雖然比爾提到社會歧視對黑人女性的壓迫,但并不同情她們的困境;這個女性只是他達到目的的手段,利用后丟棄。沒有受過教育、穿著不得體、外表寒酸的湯米看起來符合比爾及其朋友們的“迷失的女性”標準。但湯米熱情、友好、討人喜歡,有道德,并不是他們臆想的那種刻板女性形象。無疑,劇作家把湯米的良好品性與男性的偏見和自我為中心并置和對比。
對黑人女性的歧視和貶損還體現在比爾對湯米知識的嘲笑上。因為受教育少,湯米就向比爾請教,但比爾卻拷問她有關道格拉斯、塔布曼、約翰·布朗這些黑人歷史人物以顯擺自己知識淵博,并用歧視性言語羞辱湯米和所有黑人女性。“寶貝,為啥要折磨自己?麻煩我們的女性……她們都想有了不起的大腦。把事情留給男人去做吧”的本質是表明女性智力不如男性,暗指她們想以“女家長”姿態削弱男性興趣,包括求知欲,支配他們。他認為女性只應關心家務,讓丈夫高興,養育孩子。當湯米想穿著不得體的衣服擺造型時,比爾非常生氣:“我們的女人該死的沒有一點女人味。不知道讓步……太他媽的自以為是了。”[2]這證明了男性權力與在培育這種權力的社會政治結構中構建女性溫順之間的關系。[3]顯然,比爾構建了湯米的身份形象,他要創造的是溫馴的女性身體。
這些言論表明比爾已經接受了黑人女性刻板形象:飛揚跋扈、不溫柔、渴望閹割黑人男性。他宣稱“黑人是美麗的”僅僅指那些符合他的行為準則的黑人女性,僅僅是因為黑人權力運動的政治氣候,只想在作品中利用這個概念,他對待湯米以及與她的交流也沒有傳遞該概念。他宣稱湯米有一種自卑感,但他并沒有意識到他貶低她的自尊的行為應該為此負責。
歧視和貶損還體現在以辛西婭為代表、內化了社會偏見的黑人女性身上。湯米因為相信辛西婭受過良好的教育就向辛西婭征求建議,后者則給了她一長串有關傳統女性的溫馴、無私、性感方面的訓導,實際上就是黑人女性刻板形象。她指責湯米太過關注自己,喪失了女性的溫柔本性,冷酷無情,認為女性必須讓黑人男人重新找回他的男子氣概,“讓他說話。你學會傾聽。別太顯眼。”[2]顯然,她相信黑人女性削弱了他們的男子氣概,有必要讓他們恢復在家庭和社群中的優越地位。此外,辛西婭還把“女家長”,一個有權力、統治家庭的“當家女人”概念強加給湯米,結果卻與湯米的社會現實相矛盾,因為湯米一無所有。辛西婭的話似乎與她生活中的男性的話相呼應,表明她已經接受了黑人女性支配家庭的神話,內化了白人社會和黑人男性社會強加給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
二.黑人女性對刻板形象的自我顛覆
在黑人為種族平等和公正而戰的同時,他們也在維護黑人男性與女性之間不平等的關系,定義和強化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該劇戲劇化地表現了以比爾為代表的黑人男性試圖通過藝術定義黑人女性的企圖,這也是對60年代政治氣候的一種批評,對黑人中產階級虛偽和偏見的抨擊,這種抨擊體現在劇中湯米對黑人女性刻板形象的自我顛覆上。
首先,湯米對理想化的“非洲母親”或“明日瑪麗”給予了否定。比爾告訴湯米,因為她拒絕達到休斯曾經描述的美麗女性標準,穿著不得體,她就是湯米而不是“明日瑪麗”。但湯米以實際行動顛覆了男性認知偏見。明日瑪麗和湯米的不同之處在于她們的生活經歷。湯米將非裔美國人主體性歷史體現在其親身經歷之中。穿著不得體是因為騷亂中“黑鬼”同胞燒了她的一切。受教育少和貧窮并不是因為她懶惰或愚蠢,輟學是為了養活自己,減輕母親的負擔。當比爾炫耀他對黑人歷史的淵博知識時,沒有受過教育的湯米從她個人歷史角度解釋了她對約翰·布朗的認知。她告訴比爾,她家人都是一家黑人慈善組織的成員,該組織買下了布朗的農舍以便建造一個露天劇院來紀念他。她熟悉黑人歷史事件和黑人歷史人物。這表明湯米的知識源于她的活生生的生活經驗,而比爾的黑人歷史知識卻是源于書本。湯米的表現并不像比爾想象的那樣支離破碎或“不新潮”;相反,通過展示她的知識和對非洲女性歷史的把握,她表明比爾是支離破碎的,知識貧乏。他在抽象和理想化的非洲女性身上中尋找文化整體性的缺陷被揭示出來,從而徹底顛覆了黑人男性的認知缺陷及其對黑人女性的偏見。
階級差異也影響著性別政治。辛西婭試圖馴服和教育湯米接受中產階級黑人的意識形態,生活在蒙騙之中。但是湯米拒絕從男性的角度來定義自己,拒絕生活在男性眼中。她讓比爾意識到,與“不頂嘴的非常漂亮女士”相反,她是真正的、身體上被賦權的“荒野葡萄酒……明日瑪麗,罵人,打架,為自己著想。”[2]她的觀點不僅代表了真正的黑人女性身份,也是對理想化和浪漫化的非洲歸屬感的一種批判。
此外,湯米的知識和觀點也是對這些受過教育但有偏見的黑人美學中產階層的一種批判和顛覆。湯米對辛西婭的訓導的反應是“噢,嗯,哼”。這與早些時候她描述白人語言中模棱兩可的話語一樣,暗示她崇尚自己的話語風格,不喜歡白人語言和辛西婭模仿白人虛假的言語行為。比爾對“黑鬼”一詞的無知是對他吹噓黑人歷史和種族知識的明顯諷刺。作為一種挑戰行為,湯米后來再次使用“黑鬼”這個貶義詞語來描述比爾和其他人,暗示她不再想采用他們虛假的言語和行為。比爾認為“黑鬼”指的是“低級的、被降低身份的人”。然而,在湯米要求他查看白人編撰的字典后他發現其定義是“任何黑皮膚民族中的一個成員……粗俗、無禮、懷有敵意和蔑視”,一個明顯侮辱黑人民眾的輕蔑語。這表明比爾等人的教育是失敗的。湯米指出她使用“黑鬼”是出于痛苦,而不是敵意,而白人使用該詞時并不區分受教育和未受教育的黑人。因此,如果比爾這些人認為他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以及通過把他們與黑人大眾區分開來,他們就更容易被白人社會接受,那么他們就大錯特錯了。湯米認為他們接受了高等教育懂得多,她才表現得低人一等,逆來順受。但是他們擁有的只是族內自我憎恨和偏見,只關心自己而沒有真正關注黑人的困境,崇拜的只是死了的黑人英雄而不是活著的黑人民眾。
湯米也從剛剛經歷的痛苦中汲取了一些重要的教訓。雖然像她這樣的女性因為黑皮膚不符合歐洲審美標準,然而她懂得了自愛,學會了接受自己和看到自己價值的重要性,而不是他人的接受。她承認自己不是比爾繪畫中的“荒野葡萄酒”形象,但她對此有自己的定義,把它定義為一種不強調外在,而是強調善良、誠實、同情、寬容等內在品質。比爾問題在于他陷入外部因素、表面特征和刻板形象,這使他喪失了洞察力和判斷力,難以呈現一個真實的黑人女性氣質的畫像。
三.結語
雖然《荒野葡萄酒》以積極的調子結束,湯米不僅主張了自己的自主權,而且對劇中其他人物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該劇并沒有自認為解決了社會中黑人女性受壓迫問題。湯米以為僅僅在熟人小圈子內超越個人受壓迫現狀。奇爾德雷斯讓我們明白,黑人女性不僅面臨自己族群之外的種族和性別壓迫,她們還面臨著族群內部的性別和階級壓迫。
參考文獻
[1]Wattley, A. Yonder Comes the Blues: Sexual Politics, Womens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Plays of Contemporary Black Women Dramatists[D].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2001.
[2]Childress, A. Wine in the Wilderness[M]. NY: The Free Press. 1974.
[3]Khuzam, M. “A Black Play Can Take You There”: The Question of Embodiment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Drama[D]. University of Sussex, 2015.
(作者介紹:白錫漢,陜西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非裔美國女性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