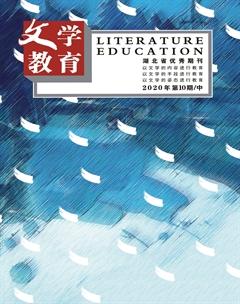果戈里和皮利尼亞克小說中的藝術空間
內容摘要:藝術空間在果戈里(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和皮利尼亞克(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Пильняк)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他們看來,藝術空間不僅僅是小說情節發生的背景,同時也是一個傳達某一觀念、表達某種看法的評價系統。在空間的范圍內,不同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反映的是對世界的不同理解或看法。通過空間各要素之間的組織性與無組織性、統一性與混亂性等關系劃分出不同的思想體系,這些體系覆蓋作品的其他非空間層次,完善世界模型,進而建立起作品的藝術整體。從作品內部體系的統一性來看,藝術空間在世界模型的建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除了可以對世界進行可感知的復刻之外,藝術空間也能表達道德方面的內容。
關鍵詞:藝術空間 果戈里 皮利尼亞克
在果戈里以及皮利尼亞克的小說中,空間的中心范疇是外省,即大城市向偏僻的小地方過渡的中間地帶。正是因為它的特殊地位,空間的比例、各層面之間的相互關系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增加或者減小空間的規模來破壞比例,通過各層次的變換來完成悲喜劇的轉換以及怪誕形象的創造。作家們通過藝術空間的變形來表達人類意識、世界觀的變化,正如洛特曼在自己的文章《果戈里小說中的藝術空間》中寫道的:“藝術空間對于建立各種模型,包括道德模型,成為一種形式上的系統,藝術空間通過符合人物的藝術空間類型來表現文學人物的道德特征,這種藝術空間可以作為獨特的雙層道德借喻”。我們對果戈里小說集《密爾格拉得》中的《舊式地主》和皮利尼亞克的小說《荒年》兩篇小說進行分析,探究藝術空間如何作為評價系統來表達人物的價值觀取向,表現事物的特征。
1.《舊式地主》中的藝術空間
果戈里的小說《舊式地主》主要描寫了亞法納西·伊凡諾維奇·托符斯托古勃和其妻子普爾赫利雅·伊凡諾芙娜·托符斯托古比哈簡單質樸的一生。小說中的空間以舊地主亞法納西·伊凡諾維奇的住宅為界限分為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內部空間在地理上形成一個環形的同心圓:“我有時喜歡遁入這異常孤寂的生活境界中去逗留一會兒,在那里,沒有一個欲望能夠飛越過包圍小小的庭院的柵欄,繁生著蘋果樹和李樹的花園的籬笆,圍繞花園四周的向一邊傾斜并且被楊柳、接骨木和梨樹蔭蔽著的鄉村茅屋”,一開始茅屋這一環有樹木作為界限,然后花園有籬笆界限,小庭院有柵欄界限;其次,整個房子被長廊圍住,“房屋四周圍繞著用細小的日久變黑的木樁搭成的回廊,在打雷和降雹的時候可以出去關閉板窗,不致被雨淋濕”;最后是唱歌的門作為外部寒冷和內部溫暖的界限,“進門處的小間的那扇門卻發出一種奇怪的、發顫而同時又在呻吟的聲音,你如果仔細傾聽,最后就會很清楚地聽到它仿佛在說:老爺子,我凍壞了!”。內部空間的封閉性、隔離性保證了這個世界不被破壞,所以這里的生活是安寧、有安全感、習以為常的。舊地主的生活是對過去的反照,是童話世界,這個世界本身被童話規則充滿,好像處在時間和空間之外。他們的生活單調幸福,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說永恒的話題就是吃。他們有時候會想“如果的話,會怎樣”,但是任何意外的外部現象對于他們而言都是不可思議的。舊式地主家宅的內部空間表現出來的固有屬性是無事件性以及時間的停滯性,這樣的世界是穩定的、安全的。小說平和抒情的基調從一開始就暗示著舊式地主平淡無奇、和諧的小世界被用來保存有價值的東西,比如互親互愛、淳樸的民風習俗。
在小說中還存在另一個空間——外部世界,但“無邊界的外部世界不是內部世界的繼續、數量或者距離的增加,而是形成另一種類型的空間”。正如字面意思一樣,這個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不是私人的,保證內部和諧的,而是他人的、古怪的甚至是有威脅性的。家宅以外的外部世界是某種開放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有事件性的,經常會“發生某些事”,所以外部世界被評價為危險的、不穩定的。
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沒有連接環節,它們彼此之間完全隔絕。當外部世界越過界限,侵入內部世界的時候,兩個空間的平衡性被破壞,內部童話世界遭到毀壞,并且最終導致悲劇。從小說腔調的變化中可以感覺到內部世界和諧的虛幻性,有時候是在隱藏的諷刺中,有時候是在公開的諷刺中,有時候是在展示這個小世界內部越來越多的不和諧中。雖然是以隱藏的形式,但是這些外部的、非童話的、同現實緊密相關的、影響內部世界的安寧與美麗的因素暗示著外部世界的入侵,比如老人的認真負責與周圍人的欺騙相對抗,“總管和村長串通一氣,殘酷無情地搶劫了個飽”,經常懷孕的少女,“使她大吃一驚的是,過不了幾個月,她的女仆中間就有人肚子比平時膨大了許多;尤其奇怪的是在這幢房子里,除了一個穿灰色燕尾服,光著腳,如果不吃東西,就準是在睡覺的小廝之外,幾乎連一個單身男人都沒有”,被蒼蠅弄臟的肖像、窗戶、鏡子,“窗戶的玻璃上有無數蒼蠅嗡嗡作響,卻被野蜂的粗嗄的低音、有時還夾雜著黃蜂的尖銳的吱吱聲,給罩蓋下去了”。通過外部世界的入侵,揭示出內部世界的虛偽性、不穩定性、無保護性。隨著情節的發展,思鄉的小說基調逐漸被悲喜劇取代,價值喪失的過程也逐漸顯現出來,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對內部世界統一性的破壞是必然的、合乎規律的結果。
外部世界的入侵是內部世界統一性最終崩壞的原因。在預示著伊凡諾芙娜死亡的偶然事件中,我們發現從一開始就被隱藏在事件深處的倫理問題:激情、渴望改變以及能夠應對周圍環境的變化是人類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些茅屋的儉樸的主人們的生活是這樣靜,這樣靜,使你暫時會悠然神往,覺得情欲、欲望和攪擾世界的惡魔所引起的騷亂不安的后果根本不存在,你只有在輝煌燦爛的閃爍發光的夢境里才會看見它們。”在小說中,這個充滿激情和愿望的世界是以濃密的有威脅性的森林的形式存在的,這個森林引誘著伊凡諾芙娜溫順的小貓,這只小貓被認為是封閉住宅里的“死亡預示”,也是內部世界唯一的“反抗者”,它“這忘恩負義的家伙大概已經十分習慣于和兇惡的野貓們做伴,再不然就是懂得了為愛情安貧實勝于崇樓玉宇這一戀愛法則”。眾所周知的是,老太婆收養小貓與其說是出于愛心,不如說是出于生活習慣,“不能說普爾赫利雅·伊凡諾芙娜過分地喜歡它,她只是習慣于經常看見它,所以就對它產生了依戀之情”。但是激情的力量要比習慣的力量更深入,所以追求更加完善的生活在這個神奇的、怪誕的偶然事件中表現了出來。內部世界由于外部世界的入侵發生動搖,統一性逐漸被打破,人的內心也不能夠應對外部世界的入侵帶來的變化,因此死亡成為必然的。
隨著伊凡諾芙娜的死亡一起消失的還有內部世界的保護性,以前看起來不變的周圍環境失去它的可愛之處,之前裝得過滿的空間好像變空了,“房間里的一切似乎都和以前一模一樣。可是我發覺一切都顯出一種古怪的雜亂,顯然是缺少了一點什么”。對于伊萬諾維奇而言,老伴的死亡意味著存在某種規律性,它們是某種決定人類生活的力量,而人類服從于這種世界通用的規律。對于他而言不熟悉的體驗、痛苦和悲傷使他變得消沉,但同時也將他從單調反復的日常生活中解脫出來,使得他發現人類真正的價值。
通過《舊式地主》,我們發現果戈里在研究人類生存價值的同時,也揭示出隱藏在和諧中的不和諧,以美為借口所表現出來的庸俗性和無意義,以及人類行為的不可靠性,對世界所發生的變化的不敏感性。在小說的最后作者將讀者帶到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用單調的描寫來暗示密爾格拉得的無希望性,強調外省生活方式以及觀念的不變性。正如洛特曼提到的:“在藝術模型中,空間有時借喻性地擔負起完全不是世界模型結構中的空間關系的表達”。
2.《荒年》中的藝術空間
皮利尼亞克對藝術空間也有類似的觀點,這并不是巧合,因為他有意識地繼承果戈里的文學遺產。在皮利尼亞克介紹文學先驅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果戈里作品中的藝術空間。但是皮利尼亞克走得更遠,他認為,密爾格拉得中的空間不僅僅是有限性的代表,也是象征著一個大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注定滅亡的舊世界以及與此相關的存在形式和世界觀將徹底垮臺。他強調物理空間的重要性,因為對某一事件發生的地點進行詳盡地描寫是與思想層次有直接關系的,同這個偶然事件中集中表達的主題相聯系的。
《荒年》在皮利尼亞克的創作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小說故事發生于1920年的奧爾津,奧爾津是一個典型的外省小城市,這個數世紀都不曾發生變化的地方成為革命事件的交叉點、各種思想、世界觀沖突對抗的領域、生與死交織的悲喜劇舞臺,奧爾津見證了舊世界與新世界的更替。在這里,貴族王朝命運的垮臺、更迭、家庭及其存在形式的最終消失成為價值體系被破壞的顯著事例。皮利尼亞克從奧爾津分離出奧爾德寧“毫無生氣”的家這個空間,正是沿著這條線(家宅的歷史以及它的住戶),小說《荒年》的主題同果戈里的小說主題相聯系。
小說的第二章主要圍繞奧爾德寧家族的歷史展開,在奧爾德寧一家的生活中,平靜、堅守自己的原則、對世界秩序不變性的堅信是他們生活的典型特征,整個家族是狹隘的父系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家庭為單位,堅守傳統與社會制度,彼此之間關系嚴肅,個體有意識的與他人保持距離。但隨著革命的發生,所有這些都遭到懷疑,革命不斷地動搖、消滅這些傳統習俗和生活方式,并且逐漸侵入到奧爾德寧與世隔離的日常生活中,變革對以家庭為基礎的牢固關系的瓦解以及對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變成為小說中的沖突點。
小說從最開始描寫周圍環境開始,即在描寫房子的時候就可以感受到必然的毀滅,“格列布不在的那兩年,房子就像死去了一樣——有著三俄尺高的基座、百年歷史的大房子在一年的時間里變禿、開始散落、倒落”。為了傳達房子里的氣氛,作者盡可能的使用直接的描寫,在皮利尼亞克對微觀世界的注意下,物品的意義得到不同程度的擴展,在他的理解中,人物生活的周圍環境不僅僅是環境,其中的物品本身能夠傳遞人類生存的某些趨向,并且證明某種理解的方式。所以,奧爾德寧一家的物品經常表現出的是負面特征,它們獨一無二的外表說明某種東西的缺失和消失,以及固有價值的貶值。精致的古老物品、裝飾或者消失,或者損壞,失去外表的美麗,并且最終失去自己的功能、本質和價值。隨著物品的逐漸消失,比如物理空間、房間、閣樓的毀滅,生活范圍越來越狹窄,局限性也尖銳起來。褪色的照片、磨損的肖像在這里成為將要消逝的世界的最后象征,皮利尼亞克還用渾濁的鏡子來更加突顯這一主題,“痛苦地死去啊,娜塔莎,你注意到了沒有,房子里的所有鏡子都變暗了、褪色了,我很害怕在這些鏡子里看到自己的臉。所有的東西都在顫抖,所有的都是幻想不現實的”。用鏡子中反射出的模糊的臉、模糊的人體特征來預示死亡。除此之外,聲音的壓低、音樂的變形以及與此相關的某種和諧的缺失表明了奧爾德寧家族的逐漸毀滅:“巨大的黃色鋼琴發怒了,好像喇叭狗……”,以非音樂的聲音效果反映這個世界統一性的崩塌,還有軋軋作響的欄桿、門和回聲很大的走廊,這些與人的日常生活相關的聲音也強調生存方式的畸形與可怕。我們發現作者將這種對周圍環境的相似分析擴展到其他范圍,正如在果戈里小說《舊式地主》中通過房間不自然的溫暖來強調內部世界的絕緣性一樣,奧爾德寧家的氣氛通過發霉、潮濕的寒冷來表現,“這里好冷,像冬天一樣,散發出潮濕的腐爛的毛皮味道”,家里的空氣、氣氛都滲透著分解的意味。
除了對奧爾德寧一家的生活環境進行描寫外,小說還通過變化更新的“宏觀世界”與陳舊死亡的“微觀世界”之間連續的對抗,來更加清晰地描繪出這兩個世界的特征,進而揭示出存在于這兩個世界的虛構或真實的價值,并且依靠這些價值建構出人物的行為模型。比如奧爾德寧家的老夫妻,他們是舊世界的最后代表,不善于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與廣闊的宏觀世界完全隔絕,他們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回憶中,對過去生活的病態留戀成為唯一支柱。但是隨著貿易、家族財富的沒落,過去的生活逐漸消失,同物品一起消失的還有與此相關的記憶、集體回憶和家族的過去。奧爾德寧家的封閉世界被外部世界包圍和破壞,外部世界是有生氣的、動態變換的大自然,大自然無視奧爾德寧家有意識的隔絕,“房間里一片昏暗,像教堂里面一樣,為了不讓光進來,厚實的窗簾白天晚上都拉著”,侵入這個封閉的空間,并且更加強調內部世界的空虛性、無價值性,“炙熱的太陽照在圓形大窗戶上面,大廳由于光線看起來空蕩蕩的”,外部世界的生命力與公爵瀕死的家族相矛盾。在果戈里的《舊式地主》中,大自然隱藏著某種來自外部世界的不確定的威脅,而對于皮利尼亞克而言,大自然是一個掀起波瀾,死亡與重生、危險與動人共存的世界,它擁有不滅的生命,它是世界革新的力量,既建造又毀壞,就像歷史本身一樣。兩個世界的沖突最終表現在奧爾德寧家族的成員被卷入到革命事件中,他們既不是革命的締造者,也不是參與者,而只是犧牲者,他們或者在大變革中“被磨碎”,或者從新世界中被擠壓出去,他們想要將宏觀世界與微觀世界視為同一的愿望導致一系列的沖突,最終導致死亡。
3.結語
我們可以看出,兩位作家在小說中都表達了這樣的思想:當外部世界侵入人類關系的內部封閉世界時,會帶來必然的改變,由于這些變化,對事件無動于衷的、不能夠應對變化的人失去的不止是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同時他們自身的生存也會受到威脅。換言之,我們研究的是固定在某種生活上的生存模型,在這個生存模型中,生存的外在環境與它內部之間比例的破壞將導致悲劇的結果:果戈里小說《舊式地主》中伊凡諾芙娜的死亡,皮利尼亞克的小說《荒年》中整個家族的死亡。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比例的關系通過藝術空間表現出來,使得空間成為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作者所要表達的倫理概念的載體,并且這一概念覆蓋整個作品。
參考文獻
[1]Лотман Ю. М. В шк- ол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с- лова: Пушкин, Лермо- нтов, Гоголь[M]. Мос- 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果戈里. 果戈里文集[M]. 滿濤、彭克巽、白嗣宏等譯.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3]Лотман Ю. М. Стру- 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 ого текста[M].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а.
[4]Пильняк Б. А. Гол- ый год[M]. Москва: ФТМ.
[5]Киченко А. Тво- рчество Гоголя в ин- терпретации Ю. М. Ло- тмана: эволюция сем- иотического метода[J]. Гоголезнавч i сту- д i ?觙, 2009: 57-69.
(作者介紹:馬源紹,華南師范大學文學碩士,研究方向為俄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