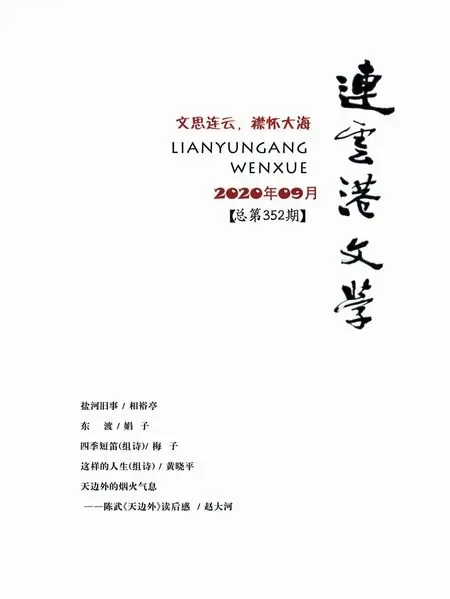暗 香(組詩)
非非
蟲繭記
下午在林中散步
一塊暗白而不可知的
蟲繭吸引著我
附著在灰暗的樹干上——
白色蟲繭通體包裹
仿佛只有層層緊密
才能讓幼小的生命
度過嚴寒的冬天
這突然映入眼球的生命
未知。這像我們在
不斷加熱的油鍋中焚雪
抑或語言。我們在書中
射出朝向自己的弓箭
密集的……箭鏃。在人生
難以抵抗的時刻
幼小之物,歷來只能
以自己的命運為靶心
大海上漂浮的獨木舟
一轉眼便不知所蹤
南瓜記
冬日,院中衰老的南瓜
懸在那兒——
被一根枯藤緊緊地束縛著
枯藤沿著根部
纏繞樹干
它的頂端,被南瓜加以
千鈞的重量
老瓜肥沃,藤身孤璨
這猶如人類纖弱的發絲
系著一座大山......
懸著,這人間的岌岌
可危之物
它隨時準備在我們的耳畔
發出明亮的
“啪嗒”一聲
岱山一日
松木蒼虬
懸崖逼仄
從岱山頂上望出
拾階而上的游人有負崖之力
他們背著帆布包仿佛
身負巨山
黝黑的線條在大山的肌腱上繃直
遠山含翠
群鳥高飛的時候
沒有任何喘息
溪飲后往零售五元的小木牌上
印幾個字
“再無難事
學會將一切看輕——”
遠處松樹下,耍弄木棍的小童
掏出定海的金箍棒
在初陽湖,讀《莊子》
老柳逶迤
新柳羸弱
在初陽我們常以一身蒼翠為鏡
早晨讀書的時候
見有先人藏在那里
兩聲清脆的鳥鳴從頭頂飛過
多么美呀,湖水說
請停一停
天上的白云,湖邊的新柳
請停一停
岸上忙碌的人們請停一停
多么美呀
柳木蒼翠
湖水為鏡,褐色的樹干
是二十余年蓬勃己身
以先人為鏡
嫩綠的柳枝,是他茁壯的手臂
以己為鏡
一身蒼翠,除了初生自我便再無他物
沙漠里的心臟
驅車在無垠廣闊的新疆戈壁
一塊寶石化的深紅樹樁
暴露在眾人眼前——
兩億年的風沙已讓周圍的
巖壁化為顆粒
但這仍未能改變它
經年的侵蝕讓樹樁
如沙漠的心臟裸露在那兒
一動不動,穩如泰山
這不動的硅化木,猶如我們
面臨人生中
最深意義的挫敗
風沙不斷地將生活的零件拆解
但我們不能完成其中的
任何一件——
這深紅色心臟像一根神秘電線
牽引著我。駕車四千多公里
從祖國的東部出發,只為目睹
這億年來至善至美的一瞬
白鷺與母親
濕地破爛的枝頭,
一只長嘴白鷺
緩緩張開雪一樣的翅膀。
下午,公園的長椅上,
我打開手機
給母親發短信:
“春夏之交,請多保重。”
我看著那只液態的
白鷺立著,
風吹著它的羽毛。
四月春光美,
白鷺的倒影
此刻正啄著水面——
二十年后,我首次愛上了
為人子的沖動。
白鷺也許是另一個母親,
它撲棱著翅膀
但很快就在枝頭凋謝。
它的細足隱藏在
一堆枯枝爛葉,
它的喙深深埋進
晚春的雪崩中。
而我的母親正在世界的
另一端道著晚安。
她滿頭白發,
而我脫下了屬于
年輕人的外套。
我們和白鷺
在漸升的氣溫中
保持了均衡。水紋漾蕩,
我被兩者的裂隙擰緊
而又一次被打開。
珍珠廣場
兩只灰色的喜鵲在頭頂
盤旋又靜止
遠處湖水一律呈現綠色
群山中有萬物的倒影
從郊區駛來的客車
摁不住嘈雜的汽笛聲
廣場的人聲鼎沸中
更凸顯觀景臺的寂靜
是王維所說傍晚的
余暉落在森林青苔上
的那種天然寂靜嗎?
當“我”在廣場上
眺望著遠處的風景
“無我”又在哪里?
我料想這世上別處
必有一個替身
自出生起,便替我
在水中聽著,不斷
從湖心躍起的魚群
四月湖風拂面
兩只啁啾的喜鵲
在天空鳴唱
放眼望去,千島湖
群山延綿——
一種不可言說的
寂靜源于我無法
在此刻獲得什么
當湖水把覽勝的游人印刻
而兩聲稍縱即逝的汽笛
在晚風中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