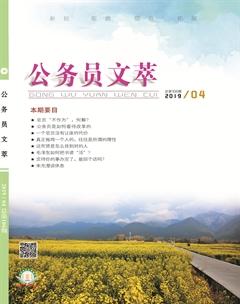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李憑
建立西晉王朝的司馬氏家族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它能夠取代曹魏,依靠的是各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西晉王朝也必須維護和調節各世家大族的利益。九品中正制正是調節世家大族之間的政治關系的平衡器,所以仍舊被沿用,但是其最初以德才品評士人的意義完全失去了。
據《通典·選舉二》記載,“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因此,西晉的選官全被中正控制,吏部僅剩下使用權;而更重要的是,籍貫與父祖的職務成了僅有的標準。這樣一來,能夠進入仕途而做高官者,自然都是所謂門第高貴的世家大族子弟。于是,西晉官場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發展到這般地步,吏治自然隨腐敗而潰壞。既然門第是決定能否入仕和官位高低乃至清濁的標準,那么世家子弟便無須培養品行與提高能力,做官以后也不必操勞政務;而庶族與寒門子弟要想入仕做官,就只能去攀附高門,賄賂權貴。正所謂“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晉書·劉毅傳》)。這樣,西晉建立之初,貪污腐敗的風氣就已彌漫官場,賣官鬻爵司空見慣。
對此,西晉開國君主晉武帝司馬炎與司隸校尉劉毅的一段對話即是很好的注釋: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日:“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晉武帝帶頭賣官鬻爵,群下當然就不以貪贓為羞了。
貪官歷代都有,并不稀奇,但西晉官場的貪官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而且是公然不諱的,這是歷來少見的現象。西晉的貪官亳不隱諱自己財富之巨,他們不僅揮霍無度,而且互相比攀斗富。在這方面,大族石崇與王愷斗富,正是有名的例證。《晉書·石崇傳》載:
晉武帝看到舅父王愷跟石崇斗富,不但不制止他們的奢侈行為,居然還幫舅父斗倒石崇,賜給舅父一株高二尺多的珊瑚樹。王愷得到了這株珊瑚樹,他把石崇請到家里來,請他觀賞這株珊瑚樹。石崇看是株珊瑚,鼻子里哼了一聲,隨手拿起一個鐵如意,一下子就把珊瑚樹打碎了。王愷見石崇打碎了他的珊瑚樹,以為這是石崇妒忌他的富有,就跳起來一把揪住石崇,大聲叫嚷說:“這是皇上賜給我的無價之寶,你賠我珊瑚樹!”石崇冷笑一聲,亳不在意地說:“你不用急,我馬上賠你!”說著,叫手下人回家搬取他收藏的珊瑚樹。其中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像王愷那樣二尺多高的更多。他叫人把珊瑚擺開,任憑王愷挑選……
由于皇帝縱容朝廷權貴貪腐斗富,功臣名將也不得不向朝中權貴低頭行賄。杜預出身于名門,功勛卓著,在西晉平滅東吳的戰爭中擔任主帥,然而他也曾賄賂朝廷貴要。西晉朝廷上下幾乎無官不貪,而西晉政權也就無可救藥了。
(摘自《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