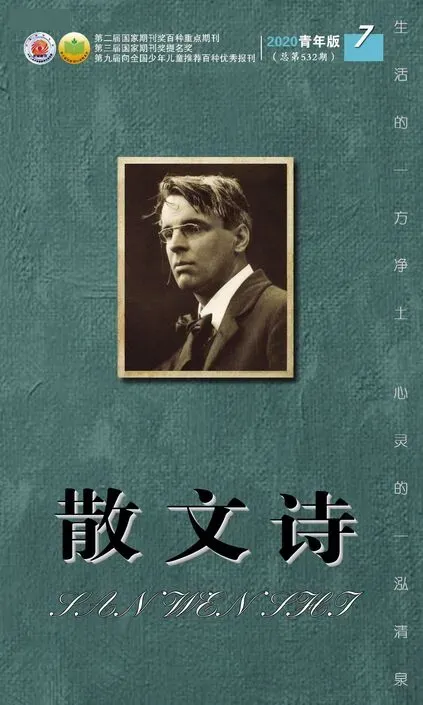“為我們剪下詞語”
——“思”之信札
莊 莊

圖/曾麗霞
一 初冬的夜, 已有了絲絲寒涼。 這是我喜歡的季候, 伴隨著大氣的下沉, 我的身體終于聽見某種落定的暗示, 而本能地放緩了自身的節奏, 開始向著一汪寧靜的湖泊張開, 并在細微的預感中獲取秘密的遼闊和遠方。 是的, 我安靜了下來, 而不是像夏天那樣, 在無休止的熱浪和蟬鳴中總是在經歷著內在的昏暗和緊張。你稱我為敏感體質, 因為這種季節變化激起的明顯帶有個人性的波瀾。 在停筆半年之后, 身體的局限得以克服, 隨之而來的, 是一種表達愿望地被喚起。 而我的每一次表達, 都希望你在場, 仿佛那是更為安全和恣意的, 是一種更深地守護和鼓舞。 如同我相信, 當我從 “思” 之暗夜中一次一次地歸來, 你必會在黎明和朝霞中迎候。 如同我相信, 循著心靈的地址, 這些不曾寄至案頭的信札, 必會經你連心的十指一一打開。
一直以來, 我都在告誡自己, 要對那些因襲的、 固有的認知心懷警惕。 時間, 更像是一個不斷重復的儀式, 日升日落之間,洶涌而至的日常總在向著每一個我們所能觸及之物流瀉、 覆蓋,那么盲目和強大, 滾雪球似的, 越裹越緊, 于是, 我們目力所及,往往只是表象。 而我相信每一個事物都會發光, 相信有一個內核的東西在黑暗的巖層里閃爍、 呼喚、 渴求。
盡管更多的時候, 我茫然于并不知道用什么來去除這無所不在的遮蔽, 但總是, 會有那些閃現的瞬間。 當我凝神于某個突然來到的事物, 它可能是某個事件、 某段記憶、 某個詞語、 某種幻象、 某個人, 或者更多的, 是并無對象的指向一種形而上的空茫,此刻, 因出離紛亂而抵達的寧靜的愉悅, 使時間顯得如此完整,并從未如此清晰地被標識為 “我的時間”。 這樣的時刻, 我視為一種隱秘的創造, 因為它越過庸常而撫觸到一顆溫暖清澈的 “思”之心。 你知道, 那些夜晚, 常常, 于清寂中, 我淚流滿面, 因為這種 “思” 之喜悅還有某種難以言傳的類似對時間和未知的鄉愁。
在我看來, 這才是值得珍視的, 在那些人所共見的表象時間之外, 當我們短暫地拋開生活的紛繁和肉身的重負, 專注于來到和發現中的事物, 我感到視覺被關閉了, 帶來污染的眼睛不存在了, 只有黑暗讓你開始重新體認和找尋, 慢慢地, 就會發現那些來自自身的光, 那些原本孩子般安睡的事物, 就會呢喃、 說夢話, 或者站在黑暗盡頭的微光里向我們招手。
你看啊, 他們是如此鮮活多汁, 如此靈性盎然, 正是借助他們, 我得以保持自己的溫度、 濕度, 以及孩子般的天真和柔軟,來對抗僵硬的生活和日益枯竭的生命。 “為我們剪下詞語”, 并非要將 “思” 局限于語詞, 而是, “思” 和語詞本來就是同時展開的。 又或者, “思”, 有時會先于語詞, 但最終, 它要依附于詞, 依附于和它有著同樣的音調和振動頻率的詞 (在最高限度上默契的詞), 才能承載 “思” 之曲折、 迂回、 盤旋。
我只是要保留這樣的時刻: 當那些被庸常緊鎖的事物偶爾掙脫約束而在心靈的地平線上噴薄而出, 一種全然自我的氣息——縈繞、 震顫, 在突然而至的光中如蝴蝶翩飛。 “為我們剪下詞語”, 即是通過語言的選擇在貌似平靜的整體中剝離出一個創造的自我、 生長的自我——為我, 為我們。
二 我從未相信消失。
在我的生命里, 任何經歷和體驗過的東西, 即使形體和輪廓被時間溶解, 即使發生的時空流逝或轉換, 它們仍然以碎片或信息的形式得以在我的體內居住。 自然, 因為強大的遺忘, 它們可能丟失或損傷了那些顯而易見的部分, 但作為一粒種子般的元素, 它們只是暫時或長久地安靜下來, 蟄伏在大腦和身體的最底層。 一旦有哪怕是最細微的觸發, 它們將恢復沉睡的知覺和彈性,并如此默契地呼應著現時的生活, 進而它們在新的時間中得到重塑, 并完成又一次的在心理上的銘刻。
如此反復, 一個貌似消失或遠去的事物總是在記憶、 想象乃至虛構中獲得更加蓬勃的活力。 這絕非簡單的重復, 而是一種豐富和贈予, 相比于遺忘, 更是秘密的幸福和慰藉。
這首先在一種童年經驗上得到印證。 隨著時間的推移, 年齡的增長, 我們所經歷的世事塵埃一般, 總在一層一層地疊加, 總在淹沒那個田埂上、 溪水邊的童年影像。 然而, 不管時間過去多久, 即便我早已來到生命的中年, 那個懵懂羞澀、 桃花般緋紅的孩子總是在穿過晨霧、 穿過暮色、 穿過鄉間窄窄的小路……是的, 總是。
我仿佛依然站在正午的陽光下, 春天的時候, 滿眼的油菜花一路鋪陳, 蜂群在帶著甜味的空氣里來回穿梭。 它們有著多么干凈的金黃和耳語, 我聽見了, 那純金色的回響。 而現在, 我依然聽見, 并感知滿腔的蜂蝶在我的內部飛舞。 我相信, 這樣的聽見和飛舞同樣在你之中持續, 因為我們擁有一個相同質地的童年:70 年代的農村, 物質的匱乏、 人情的淳樸、 自然的生態, 農耕的散漫和自由。
而日后當我深究我的內在與我所經歷之物的關聯, 我是如此感激那個 “散漫和自由”。 它一開始就為我拆除了那些橫條豎條的柵欄, 讓我像一匹小野馬, 在田野和野花的遼闊里瘋跑、 嬉戲;讓我在無人管束的竊喜里伴星月, 聽蟲鳴; 讓我無限地滑入不著邊際的遐想并依此編織自己的內心。
是的, 那個依世俗時間的邏輯早已終結的童年, 已經化入氣血, 并在記憶和懷想中一次又一次地凝固成形, 一次比一次清晰,一次比一次鮮活: 那扇動著透明的翅膀、 時刻準備飛起來的孩子。
正如現在, 當我寫到它的時候, 它在我的話語中再次到來。
三 這是一個被死亡標記的上午。
人們在談論他。 一個陌生者, 在夜晚的黑暗中, 自26 樓向下, 把自己交給了血色漾開的大地。
人們在反復談論他。 他因此在我的意識里反復地墜落、 墜落……那樣決絕和急迫, 猶如電影中不斷重現的鏡頭。 就這樣, 一個與我毫無關聯的人, 通過死亡輕而易舉地占據了我。
這是否意味著, 他以更隱秘無形的方式在延續著他的生, 甚至在一個毫無交集的人的腦海和意識里。 這看似有點荒誕, 但它真實地發生了, 在兩個全無瓜葛和親緣的人身上, 生和死, 完成了一次對接。 自死亡那鋸齒形的粗糙的邊緣, 我把自己嵌入了進去。
其實, 從一開始我就預感到, 這樣的表達會有一些艱難。 但這樣的主題值得我們一再伸展語言的觸角, 從不同的點面和維度去試探, 去接近, 直到它得到至少是我們自己認為的較為精準的表達。 或許, 我想說的是, 死亡并不代表終止和結束, 而是從未停止它的衍生和繁殖, 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 從一種形態到另一種形態, 不但從未關閉什么, 還反而如此生生不息。
在我大約六歲的時候, 死亡第一次向我展露了它蒼白、 幽藍的面孔。 多年以后, 當我回想起, 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不甚明了的冬日陽光、 被槐樹遮蔽的隱約的天空。 那一天的晚飯時分, 場院里的鄰居開始穿梭, 夾雜著急促的說話聲和腳步聲, 說是二爹爹沒了。 我擠在人堆里, 看見二爹爹躺在自家堂屋的地上, 青衣青鞋, 身上蓋著紅綢被子。 那雙鞋, 白底上綴著黑色的圓點, 冷硬而恐怖。 離我那么近的一個人, 活生生的, 怎么說沒了就沒了呢。 這自然是一個六歲的孩子無法懂得的, 而那雙充滿鬼氣的鞋, 成為無法擺脫的死亡意象, 一直懸浮在我的腦海里。
在對死亡的恐懼中, 我小心地甚至神經質地活著。 我小時候一直怕黑, 怕影子, 怕鄉下的夜里各種無名的聲響。 晚上躺在床上, 只要一閉上眼睛, 就有無數的黑云朵在飄, 夾帶著一些閃著金光的火星。 等我在驚恐中打開眼睛, 一切又無影無蹤。 如此反復。 要是雨夜, 我總會聽見一雙雨靴由遠及近、 由遠及近, 但永遠走不到我的門前。 而檐下的雨似乎永遠也不會滴完, 不緊不慢地敲打著我的神經。 這是一段夢魘般的時光, 我感到某種靈異的氣息總在我身邊圍繞。
多年以后, 我親歷了父親的死亡。 悲傷的五月, 用短暫到窒息的幾分鐘, 阻斷了一切。 那一天的父親躺在一張粉紅色的床單上, 像是沉入永久的睡眠。 父親照例被換上一身青衣, 趁著他的手還有些許溫熱, 有人在他的手中放了桃枝, 讓他握著。 另一只手握著半把桃木梳, 梳子是我平時用的, 另一半留在我身上。 我看著父親, 沒有了兒時的恐懼, 我竟覺得他那么整齊地像是去赴一個約會。 死亡, 在這一日, 竟然有著溫和平靜的面容。
在對死亡的體驗中, 一個轉換生成了: 從最初的恐懼, 到后來平靜的悲傷, 再到現在的死即重生、 生死同一。 這并非我找到了解脫之道, 只是生和死的對峙在認知里得到了暫時的緩解。 而另一層面, 當生死的邊界變得模糊, 其實質是我們每天都在生,也每天都在死。 是的, 無人可以取消這種宿命: 越接近越荒涼,越接近越虛無。 因而, 我一直試圖通過寫作來盡量保留一些氣息, 以證明生命的曾經在場。 如果你讀到了太多的疼痛、 太多的沉重, 請原諒我還沒有找到更為輕逸的方式。 但請去除那樣的憂心, 請與我一道, 照看悲傷但永不熄滅的內心。
四 語言, 在我看來, 遠非書寫的工具, 而是存在本身。
因此, 語言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存在, 無疑是對一個書寫者功力的考驗。 事實上, 在個人的書寫中, 當我試圖用自己的語調說出存在, 我感到了面臨的無數漩渦和困境: 浪濤會吞噬我, 高墻會阻擋我。 渴望中有如春天的話語——新鮮的生長的話語, 還在冰封的途中, 等待我前去認領。
這種困境首先來自語言與物的距離。 是的, 曾經, 我如此信任語言的燭照和洞見。 而有意思的, 卻是越寫越清晰地看到了那個“距離”, 不可窮盡, 越走近越遙遠, 越凝視越兩眼皆空。 就像是在暗夜里行走, 憑借星辰賜予的微光, 緊追一個縹緲游移的背影, 卻從未趕上他的步伐, 更無緣目睹宛如源頭的真容。 是自我的眼睛蒙上了太多的灰塵以致視物無以清明, 還是物的本身被太多的紛亂和神秘包裹而被捆縛? 或許, 幽暗是雙重的, 人和物都需要一個雙方心領神會的密碼, 才能完成對接和向彼此打開。 這讓我想起阿拉伯故事里的 “芝麻開門”, 多么童稚和美好的發聲,皆因無障無礙的天真呼喚而寶藏洞開。 那么這個密碼的尋得, 定然會排斥語言和思維的添加和繁復, 而是返歸一個自然的儀式:讓事物在語言中找到它們質樸但謎一樣的本名。
其次, 還有語言與自我的距離。 從表面上看, “語言” 由“自我” 來說出, “自我” 是 “語言” 的場所, 仿佛有著最近的距離, 而事實上, 我始終感到這種距離是難以縮短和消弭的。 這源于自我的多重性和多變性所帶來的復雜和神秘。 一個人內心任何微小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打斷語言的節奏, 猶如黑暗的海上航行, 注定要承受偏離帶來的波濤、 起伏, 甚至擱淺。 生成中的語言將會成為碎片的浪花飛濺, 當它再次匯入洶涌的語言之海, 已瞬間變得蹤跡全無。 這時, 將要重新尋找一種語言的方向。 如此反復。 因而, 用語言說出自我是如此艱難和難以確定。
我還想說的是語言與他者。 語言與自我相距尚且如此遙遠,更遑論他者。 更多的時候, 不同的人因內心構造的不同而在心智、 思維方式、 語言習慣、 感知力、 想象、 直覺等方面會存在極大的差異, 這差異像尖利的冰山, 難以消融。 因此, 在這個意義上, 我從不期待大眾的眼睛和耳朵。 我要找尋的是與我同質的人, 這個 “同質” 表現為在對外部事物和隱秘內心的觀察中,“思” 的起點和落點擁有一片共通的水域, 任憑他們各自波濤洶涌, 他們總能聽到對方自幽深的水底傳來的呼喚, 并作出應答。只有這樣的耳朵才會把另一個人的言說聽成充滿意義的悅耳之音,也只有這樣的人才會穿過語言的迷霧, 而真正到達另一個生命的棲息之地。 而當我在語言與物、 語言與自我的距離中無端損耗的時候, 我驚喜地發現了你, 一個同質的人, 一雙靈敏的耳朵, 在守護, 在傾聽, 包括我的笨拙之處。 為此, 我想說出感恩, 說出朝霞, 說出那迎接我們的語言的曙光。
五 當時間來到新的一年, 它仍如鏡子般平靜。 我知道, 它的下面, 深不見底。 沒有什么能激起持久的波瀾, 一次次短暫的飛濺之后, 重又歸于黑暗。 我們來不及找到痕跡、 缺口, 更無路徑。這讓我們深以為苦的水平面, 是令人絕望的玻璃之鏡。
是的, 我們總是受縛于時間, 猶如困獸之于牢籠, 既回不到過去, 也看不見未來。 這時, 我想, 我們應該容許自己從一個小心翼翼擦拭鏡面的人, 變身為一個魯莽者、 冒險者: 當我們松開手中之鏡, 至少將得到無數的碎片。
也許你同樣意識到了, 在這樣的困境里, “碎片” 是多么美好的禮物。 正是在這一打碎中, 暗喻著重拾、 拼接、 修補和重置的無數可能, 也就是說, 時間開始從一個無望的客體轉換成我們可以參與的可感之物。 這讓我對時間的絕望得到緩解, 我的心胸因此一度充滿了某種喜悅, 這也讓我確信, 時間是可分的, 可挽留的。
當我開始凝視過往, 我意識到, 如果我們把時間設定為通常比喻的流水, 那么, 只有那些淹沒過你的頭頂、 打濕過你的衣衫、濯洗過你的雙足的波濤和浪涌是屬于你的。 只有這個在我們的記憶和意識中銘刻下來的時間, 才會因為獲得個人的印記而不朽。這樣的時間, 盡可不斷地添加自我的各種信息而使其變得日益豐富而最終形成自我循環的時間之流, 或者, 自己將會變成一個時間的容器。 這遠非對時間的征服和占有 (對此我們永無可能), 而是一種有效的聯結和重置。 依此, 我們似可找到一個個為我們的生命所曾經經驗的清晰可觸的時間截面, 它的紋理, 它的路徑,或能帶給我們對未知的某種方向性的探尋。 而那正是朝霞升起的地方, 是我們的生命從陳舊走向永新的地方。
而那些無法與我們的生活和經驗互證的時間, 只是一種抽象的存在, 一種氛圍, 一種類似中國寫意的晨霧, 它來過, 卻不能被表達, 亦不能被抓住。 它漂浮, 它是 “夢的時間”。 它需要被安放在我們心靈的上界, 與我們的塵世生活遙相呼應、 互為聯結。
(注: “為我們剪下詞語” 出自策蘭 《低處的水》 中 “無人從心墻上為我們剪下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