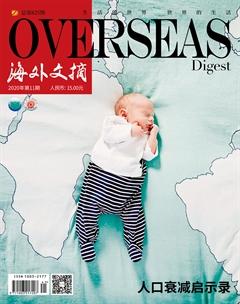從古至今,我們是如何對待老人的?
艾娃·米也特 Pat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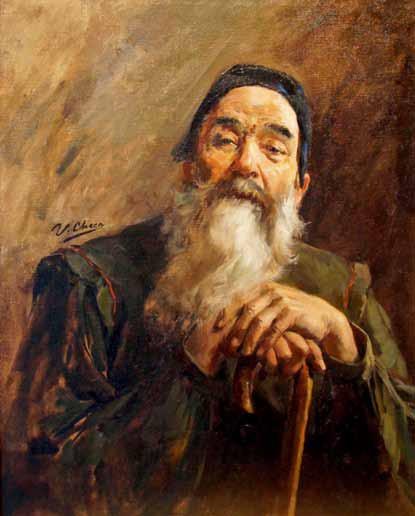
畫家烏爾皮亞諾·切卡創作于19世紀末的肖像畫《老人》
2020年3月,在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瑞典,新冠病毒已造成了最初的幾例死亡病例。基于對公民個人責任感的信任,當地政府選擇了一種較為寬松的隔離政策。因此,在疫情期間,當全球一半的人都處于隔離狀態時,瑞典人卻在露臺上玩樂,尤其是健康的年輕人。這是幾十年來的安逸和穩定所帶來的結果。
然而,當瑞典的年輕人在春日陽光下享受美酒時,斯德哥爾摩的養老院里卻正上演著戲劇性的一幕。這種對老年人尤為致命的病毒,已經開始流行了。兩個月后,在當地衛生機構的統計結果中,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病例大部分都是超過70歲的老人,且一半的死亡都發生在家里。“我們沒能保護好老年人,這是我們社會的失敗。”瑞典衛生部部長說。
顯然,失敗的不只有瑞典。在幾乎全世界,新冠病毒造成的老年人死亡率都是與其人口占比不相稱的。居民住宅是主要的死亡地點。西班牙國家衛生部數據顯示,全國死在家里的老年人已占到總數的69%。
在英國,疫情之初,政府拒絕公開老年人的死亡數量,但一些關愛老年組織,如“老年英國”,稱病毒在老年群體中已經是“暴走”狀態了。五月底,國家統計中心公布,新冠病毒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造成的死亡病例中,80%都是70歲以上的老人。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在七月初估計,新冠病毒在美國造成的死亡病例中,約1/4發生在養老院。但在其他的分析報告中,這一比例提高了近一倍。
這是怎么了?在被視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標榜為“社會民主搖籃”的瑞典、非常重視家庭的西班牙和執著于過去的英國,老人為何如此弱勢、不受保護?究竟發生了什么,導致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變得就像是哲學家維克多·戈麥斯所描述的:“老人的形象正逐漸被否定,不只在社會里,在家庭中也一樣。”
| 知識的來源 |
可以確定的是,老人的形象正在加速貶值。如今,正如社會學家皮拉爾·艾斯加里奧指出的,老人與社會之間的距離,不只是物理上的,更是道德上的。這種冷漠不僅僅是情感上的缺失,而且是對一代人的不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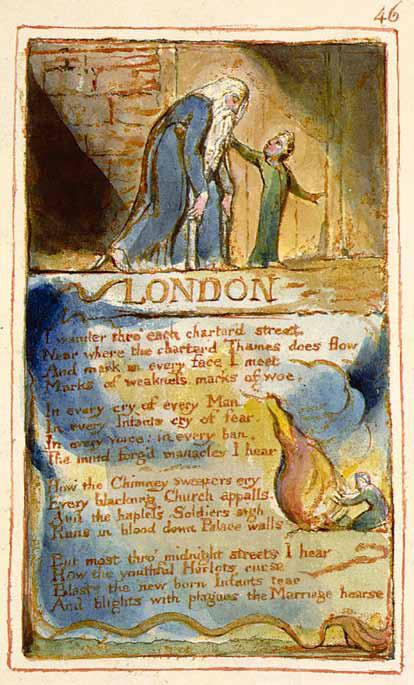
威廉·布萊克詩歌《倫敦》的插圖中,一個年輕人引導著一位老人。
歷史上,老人一直是受尊重的,尤其是在那些沒有書面語言、知識靠口頭傳述的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老人一直是傳統與智慧的守衛者,也是沖突的最佳仲裁者。在原始社會中,高齡代表著一種特權,卡洛斯·馬杜拉那醫生說:“那是一種必須在神靈的幫助下,才可能達成的功績。”
在古代,老人是權力的擁有者。希臘還誕生了“老人政治”——掌權者都是老人。直到20世紀,這種政治都還富有生命力,如在蘇聯。而在一些總統年齡較大的國家,如意大利,老人政治仍存在于最高的司法部門中。在梵蒂岡,要想成為教皇,年齡資歷是最基本的條件。
過去也是如此。在斯巴達,最重要的管理機構之一——長老會議,就是由28個60歲以上的成員組成的。在古羅馬,西塞羅在公元前44年寫出了《論老年》,其中的“Senatus”就是指擁有權力的元老院,意為“老人的會議”。而在古埃及,與所有原始文明一樣,長壽被認為是超自然的。
在希伯來文明中,老人被認為是能與上帝溝通的人。馬杜拉那指出,這一點能夠在《舊約》中找到好幾個例子,如摩西在作決定前都會詢問上帝,而后,上帝會對他說:“去吧,把以色列的老人都聚集起來,并告訴他們。”又或是吩咐他說:“去到人民面前,帶著以色列的老人們。”馬杜拉那在《歷史上的老人》一文中強調稱,在希伯來社會,“老人會議”的權力是“強大且不容置疑的”。
這種權力在中世紀時被削弱了。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稱,中世紀社會無視老人政治,但老人在作為受尊敬的象征性形象上還保有價值。他們是歷史記憶的守護人,仍會被要求成為仲裁者。中世紀是戰士和十字軍的時代,馬杜拉那說:“強者至上,老人的處境自然就不利。”但他同時也指出,14世紀中期爆發的黑死病是對老人有利的,因為當時的主要易感人群是小孩和青年。15世紀流行的天花也是如此。“在有些情況下,老人會成為一家之主……瘟疫幫助了老人,讓他們獲得了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
| 更小的影響,更多的關注 |
在文藝復興時期,對美和藝術的追崇占據主流,老人的影響力開始減弱。從這一時期的藝術作品中可以看出,只有睿智又可敬的老人形象才會被接受。而從18世紀開始,歐洲在對于老年群體的特殊照顧方面有了進步。1740年,奧地利瑪麗亞·特蕾莎女王修建了第一所養老院。1880年,德意志宰相俾斯麥創立了后來社會福利體系的基礎之一——養老金制度。1903年,俄國科學家伊利亞·梅契尼科夫提出“老年學”這一概念,即專門研究老年的科學。
隨著科學和社會的進步,從20世紀末起,人口金字塔在許多發達國家開始出現倒轉。出生率下降,而老年人的預期壽命在增長。這種變化反映出了生活質量的提高。如今的60歲與20年前的60歲已不可同日而語,更不用說70歲、80歲……人們對年齡的感知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老年學家安娜·傅雷克薩斯指出:“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比實際年齡更年輕,也比社會視角中的自己要年輕得多。”
在這個癡迷于追求青春與美的世界里,年老越來越被視為一種阻礙。是什么造成了這種戲劇化的現象?經濟發展、工業化和高速的技術革命都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人類學家嘉瑞德·戴爾蒙德認為:“社會是否會關照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一群體有多大的用處。”
82歲的戴爾蒙德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研究不同社會對待老人的方式。他發現,即使在那些最傳統的,理論上最敬老的社會中,同樣存在代際間的利益沖突。在某些社會,當老人不再有用時,就會被拋棄(玻利維亞西里奧諾人)、被迫自殺(北美因紐特人),甚至會直接被殺(巴拉圭亞契人)。戴爾蒙德認為,代際關系取決于環境,但社會價值觀也會對其產生影響。
戴爾蒙德提到,在東南亞等地的儒家傳統中,不贍養父母是為人所不齒的。地中海地區也有類似情況,那里對家庭的重視源于父權制的傳統。在這種可追溯至古羅馬人和希伯來人的文化體系中,最大的權力會被賦予最年長的男性。

西班牙布爾戈斯街頭的老人雕像
而在美國這樣的現代工業化國家中,很流行獨立于父母的單居制生活。戴爾蒙德寫道:“在那里,老人都不和自己的孩子住一起。照顧老人變得更復雜了,哪怕孩子們愿意這樣做。”
然而,幾十年來,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和生產率等概念,已經對全世界很多國家產生了影響,包括西班牙。要知道,在不久以前,與祖父母同住可是西班牙社會中很普遍的現象。這次疫情帶來的危機,以及它對老人造成的災難性影響,都在促使我們反思自身和老年人之間的關系。畢竟,那也是我們所有人都希望可以經歷的人生階段。
[編譯自西班牙《先鋒報》]
編輯: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