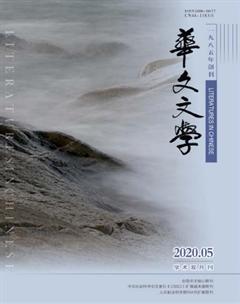張錯自譯詩歌的中國性與民族性辨析
張曼
摘 要:張錯1970年代之后創作的詩歌以中國性、民族性、獨特的用典和精確的用詞享譽中國詩壇,尤其是臺灣地區詩壇。然而,其自譯詩歌,在北美詩歌及北美中國詩抒情傳統的范疇里,詩的中國性內涵因譯介選擇被狹隘化,詩在臺灣/中國新詩語境中具有的獨特詩性被削減。但是,由于英譯詩雖然脫離了原文的詩歌與語言語境,卻并不徹底;又由于詩人一生經歷過許多曲折,其精神歸依慢慢呈現出復雜與多元化傾向,因此所生的立場與對民族主義的理解發生了變化。由此,其英譯詩在新的語境中,獲得了一種新的價值體現,那就是詩人中國式詩思及其在英譯詩中的體現參與了詩的世界性建構。
關鍵詞:張錯詩歌自譯;中國性與民族性;北美中國詩抒情傳統;世界性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0)5-0019-07
在臺灣現代詩歌史上①,張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現代主義詩人,1970年代之后,他創作的詩歌以中國性、民族性②、獨特用典和精確用詞享譽中國詩壇,尤其是臺灣地區詩壇。他不但創作詩歌,還編輯、英譯和研究臺灣現代詩。張錯無論是創作詩歌還是編輯、英譯和研究臺灣現代詩,都始終強調詩的“中國性”“民族性”。其原因,一方面,出于對臺灣現代詩如何突破“橫的移植”,從而獲得發展的考慮;另一方面,出于對臺灣現代詩如何融入“世界詩史”的詩學考慮。然而事實上,其自譯的詩歌,在北美詩歌及北美中國詩抒情傳統的范疇里,因語境變化,又因是選擇性譯介,中國性不再明顯,原在臺灣現代詩、中國大陸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詩語境中具有的獨特詩性被削減。但是,由于其英譯詩雖然脫離了原文的詩歌與語言語境,卻并不徹底;又由于詩人一生經歷過許多曲折,其精神歸依慢慢呈現出復雜與多元化傾向,因此所生的立場與對民族主義的理解發生了變化,變得更加超脫與包容。由此,其英譯詩在新的語境中,獲得了一種新的價值體現,那就是詩人中國式詩思及其在英譯詩中的體現參與了詩的世界性建構。
一、中文詩集的中國性民族性立場
與英譯詩集的西方詩學認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詩歌創作界與評論界為了及早擺脫“戰斗詩”口號式窠臼,追求詩創作的“超現實性”“純粹性”以及“晦澀聱牙”的語言,把“全盤西化”等同于詩的“世界性”,③從而導致詩創作進入了“虛無”狀態。時至1970年代,如何糾正與均衡過度的“世界性”,成了詩歌界首要的任務。“糾正與均衡”的方法之一,便是臺灣現代詩創作從全盤西化回歸傳統。受當時特殊的文化現實和政治意識形態影響,臺灣思想界對傳統與現代、左與右等文化立場存在種種分歧與角斗,并由文化層面上升到了政治層面。這一角斗與分歧體現在詩歌界,便是對相關概念的界定和劃分存在分歧和糾纏,如何理解和界定鄉土與民族的概念,又如何理解和界定中國性、民族性的內涵等,眾口紛紜,無法統一。詩人張錯理解中國性與民族性,是基于中華文化的大傳統,即是在中國古典詩學、民歌、五四新詩,還包括臺灣鄉土傳統中進行的。這一主張落實到詩歌創作中,在詩的內容上,書寫家國情懷,其中包括書寫在美華工的災難史和個人的身世;在詩的題材上,借用了大量的中國古典意象,有些直接以古典意象作為詩題,勾連起歷史與當下,增強了詩的豐富性,拓展了對詩的想象空間,除此之外,其他題材則主要涉及日常場景、時事、感懷、思鄉、贈友人等;詩歌情感的民族性表達主要是詠古以喻今。詩人借用中國傳統與現代的意象、用典感嘆個人飄零的身世,表達詩人內心深處對根的追尋,抒發對祖國的孺慕渴切之情,以及對在美華工遭遇的悲憤,進而生發出生命的悲劇感。詩人還從詩的意象(客觀物體)中得到能量,傳達出“人盡管面對著悲劇處境,然而卻在為生存的意義而掙扎著,在此過程中人獲得存在的尊嚴”,即意在召喚與啟蒙,張錯稱此是他詩歌“獨特的詩性”。④除此之外,詩人獨特的詩性還表現在不避標點符號,詩的獨白,詩的語言力求口語與古典雅言的均衡,挑戰中國十四行詩已有的成規,如在詩集《錯誤十四行》里,詩人企圖把臺灣現代詩的脈絡從里爾克、馮至,連接到何其芳、卞之琳等1940年代的中國新詩,“嘗試重建遺落的新詩抒情傳統”⑤。
正是基于這樣的立場和主張,張錯梳理臺灣自1960至1990年代30年里出版的詩選集,考察選擇標準的變化,從而發現并指出,林明德等人編選《中國新詩選》⑥,礙于臺灣當局政局的限制,不敢打破禁忌,故意漏選與中國傳統有關的詩歌,批評詩集不敢“正視臺灣地區詩歌發展與中國母親的關系暢所欲為,有時更做成誤導的場面”⑦。由此,呼吁“我們在臺灣詩壇的榮耀中,仍然應該有勇氣去憶取承認當年蓽路藍縷披荊斬棘哺育我們長育的中國母親”⑧。張錯特別稱贊了楊牧、鄭樹森于1989年合編的洪范版《現代中國詩選》,指出輯錄的詩歌涵蓋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三地⑨,并呼吁臺灣現代詩創作回歸中國性民族性。其實,早在1980年代之前,張錯就開始留意并有意在詩歌創作中踐行這一主張,并在1981年將此類詩歌編輯出版,集子名《錯誤十四行》。該詩集既踐行了臺灣現代詩回歸傳統詩學的主張,也代表了詩人在詩歌形式上對新的抒情傳統的嘗試。詩人還把這一主張踐行到英譯本臺灣詩選集的編選上,認為編選臺灣詩英譯選集,也應該像編輯出版中文臺灣詩集一樣,要考慮到與中國古典與現代傳統的統一性⑩,并對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英譯并在國內和海外發行的現代詩選集,沒有輯入臺灣和香港地區的詩歌現實提出了批評。“1949年以來,英譯的臺灣或中國大陸現代詩選,都是涇渭分明,互不相干”,而事實上,“……同在一個大中國的大前提,他們在這30年的統一性極端明顯”{11}。他認為不是從詩學傳統出發編選的詩集,無論中文還是英文,無論在臺灣還是大陸出版,都不是完整的中國文學詩集。正是張錯在1980年代甚至之前的實踐,1990年代篳路藍縷的振臂呼吁,后經由史書美、奚密等學者的發展,催生了當今王德威的Sinophone,即華語語系文學史書寫的主張與踐行。
吊詭的是,詩人這一主張卻沒有踐行在其自選、自譯并編輯的詩集中。
張錯是位多產的詩人,自1965年在臺灣出版第一本詩集《過渡》,到2016年出版的詩集《張錯詩集II——檳榔花、細雪——另一種遙望》,共23本。比較而言,雖然詩人一直生活、工作在北美,但是,時至今日僅在北美出版了兩本自選自譯的英文本詩集:1987年的《千曲之島:臺灣現代詩選》(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和2000年的《漂泊》(Drifting)。前者是一部臺灣現代詩人的英譯詩歌選集,輯入了8首詩人自選的詩歌,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詩人自選自譯的個人詩集,共37首,由格林印特節出版社、哥本哈根和洛杉磯出版。英譯本《漂泊》輯入了《千曲之島》集中詩人的7首詩歌,未輯入的一首名《貝珠淚》(The Tears of Pearl)。
英譯本《漂泊》出版之前,張錯于1991年就在大陸出版過大陸版《漂泊》,集中共輯入詩歌84首,更早些時候,即1986年詩人在臺灣也出版過詩集《漂泊者》。臺灣版《漂泊者》{12}與英譯本詩集《漂泊》在編目上不同,不過其詩歌都是先在臺灣出版,因此,即便編目不同,詩人的詩歌主張及其實踐均能在其他詩集中得到印證,因篇幅所限,對此不納入本文的考察中。如前所述,1991年大陸版《漂泊》共輯入詩歌84首,與英譯本僅37首相比,篇目上超過了1倍,詩的內容涉及三個方面的主題,其中,尤為突出是書寫家國情懷的詩如《紅豆》《故劍》《春夜洛城聞笛》等。馮至評價該詩集,認為古詩有“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的同世感。“他(張錯—引者注)從中得到啟發,善于吸取,往往略加點化,那些詩句便天衣無縫地融合在他自己的創作里,他用前者結束婉轉纏綿的‘憶往事,用后者戛然停止在雄渾悲涼的練劍。”{13}張錯本人在接受大陸學者采訪時,對詩的自我評價延續了馮至先生的話。{14}這不是迎合而是默契,早年,張錯博士論文是寫馮至評傳。張錯還特別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個性比較軟弱,以刀劍意象入詩,企圖形塑包括自己在內的知識分子恢弘人格。大陸學者由此認為,他是當代知識分子里較少幾個認識到且能坦誠表達過知識分子比較軟弱的詩人。{15}
然而,在2000年英譯本《漂泊》詩集里,“前言”的導讀文字只字未提詩的“家國情懷”“個人身世”,也只字未提詩題材和用典的中國性民族性,只強調其詩與北美當代詩歌在語言和詩學上的關系。“我發現自己完全在用另外一種語言在言說。1980年代,我曾一度迷戀“投射詩學”(Projective Verse),迷戀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的詩‘一個意念必須快速導向另外一個意念;我讀威廉姆斯(C. Williams)作品,尤其是他的《帕特森》(Paterson)……”{16}不過,在1987年版的《千曲之島》中,張錯介紹自己詩特色時,“家國情懷”和“個人身份”赫然在目。“他的個人生命與詩歌抒情以探索國家和個人身份見長,而這一探索常常迷失在中國災難性的歷史經驗中。他的詩歌反映了這一生命的悲劇感,……詩描寫日常生活,詩歌語言抒情且被高度控制,……人盡管面對著悲劇的處境,然而他卻在為生存的意義而掙扎著,在此過程中人獲得存在的尊嚴。”{17}《千曲之島》詩集里詩人自譯的8首詩中,其中7首后來都被再次輯入了英譯本《漂泊》中。縱觀《漂泊》集中輯入的詩歌,其主題雖然不能代表最具其書寫“家國情懷”的中國性民族性特色,但這些詩的題材和意象卻來自于中國文學的古典、現代新詩傳統,其中包括臺灣地區的鄉土。如古典自然意象入題的《蘭澤多芳草》(Fragrant Herbs by the Orchid Stream),古代文物入題的《雙玉環怨》(Double Jade Ring Grievance),古代詩詞入題的《惘然》(Confused),或直接以中國哲學著作作詩題的《讀道德經第20章》(Reading Tao Te Ching, Chapter 20),臺灣本地鄉土“物語”作題的《無悔物語》(Wu- Hui Monogatari)。其他的詩,其題材和意象的中國性、民族性不突出,但內容與上述詩歌一樣:追問人的存在價值,繼而追問生命的意義。
縱覽詩人自譯的38首詩(包括《千曲之島》集里一首《貝珠淚》),主要是抒發個人漂泊的心境、對生命流變和存在價值作追問,但依然能在一些詩的字里行間辨別出詩人對家國情懷的抒發,如在《滄桑》一詩結尾,詩人呼號“我們需要更完整一點的國”{18},這一類的詩還有《呼喚》(Yearning)《賞菊》,個人身世其實含蓄隱晦地隱喻家國歷史。不同的是,輯入1991年大陸版《漂泊》里的《故劍》《刀頌》《大龍》等是直接抒發詩人的家國情懷,詩人因思念家國,倍感身在異國他鄉的孤獨。張錯憑借1991年版《漂泊》詩集重在抒發詩人的“愛國情懷”“在美華人勞工苦難史”被大陸詩歌界和研究界認識與接受,由此,他被認為是臺灣現代詩中國性、民族性的代表。比較而言,英譯本無論從詩題還是從詩的內涵表達,“來是夢,去是空”的生命短暫情懷的抒發覆蓋了“過去一百多年蒙受苦難與屈辱的中國”,“戛然停止在雄渾悲涼的練劍”的抒寫。當然,英譯本也沒有完全違背詩人的主張,即編選詩人個人詩集,不但要考慮到與中國詩學傳統的關系,還要顧及到詩人個人風格的統一性,否則從詩人不同詩集里分別挑選出幾首,英譯且編成集子出版,成為該詩人的英譯合集,“只能算得上是‘選譯詩作(selected poems)”{19}。這樣的英譯詩集看似完整,并且呈現了詩人最好的作品,但詩人獨有的風格和統一的主題便消失了{20}。1987年,張錯編輯《千曲之島》時,詩的選擇偏向個人身世,但卻以“一人譯一國”{21}的心態,把“臺灣民報”時期的先驅張我軍、賴和編入集中,還把雖用日語創作但中國文化與民族意識強烈的巫永福、張冬芳和龍瑛宗輯入集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詩集沒有違背詩人編輯英譯詩集的中國性、民族性主張,也就是說,這本詩集在詩人個人風格上體現了統一性,而詩的中國性、民族性特色,則是通過包括上述所列的其他入選詩人的詩、而非他個人的詩得以體現。
可見,因詩人兼譯者譯介的傾向性選擇,張錯自譯詩集的中國性與民族性,無論在內容表達還是在詩題方面都被狹隘化。但是,“個人身世”的詩歌美學,即書寫個人漂泊的身世,進而升華到對生命的感悟與追問的“天涯美學”,正是抒發了在美“離散”族群共同的情感,也是在美華裔階層共同的心聲,更是在美華裔集體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與尋根。可見,詩人這一舉措無疑是考慮到了翻譯文本的語境化和精神歸依的多元化等因素,以及翻譯文本在21世紀北美的“歷史化”與“非歷史化”之分這一事實。
二、詩人精神歸依再選擇
與翻譯文本再歷史化
正如上文所言,詩人這一傾向性選擇與其精神歸依的多元化密切關聯。詩人祖籍廣東,生在澳門,長在香港,讀大學在臺灣,讀博和工作在美國,詩人成長過程中的不同經歷,不同的區域文化都對詩人的思想產生了作用。同時,詩人的身份隨著場域和“讀者”的變化發生著改變,有學者認為這是“離散華人身份的一個理想策略”{22}。在1980年代之前,詩人身處美國,卻對在地文化只是“承受”甚至是“抗拒”{23},內心始終只認同母國文化;可是,在1980年,詩人因欲回臺灣定居卻遭到臺灣當局當權者的抵制,從此,詩人雖仍然堅守根的文化中國性,但對“漂泊”的理解進入了精神領域,追求因“漂泊”反而內心更加寧靜與淡泊的美學。內心的寧靜與淡泊不等于無所思、無所為,而是在創作中超越母體與在地文化的“對抗”,不像多數漂泊詩人或作家,要么依然倚重母體的傳統,用文字反復贅述,要么則更加在地化。詩人以開放的姿態和心靈,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和新的人生。“一個作家的成長……必須永遠保持他心靈的開放,去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人生。”{24}其次,詩人這一主體的自我建構,雖然“其特質是搖擺不定,游移而多元,甚至是混雜性的”{25},但是仍能從中爬梳出相對清晰的脈絡:
首先,詩人在英譯詩集《漂泊》“前言”里,反其道以行之,只字未提詩的中國性、民族性,卻列舉了“黑山詩派”中的幾位北美當代詩人如威廉斯、查爾斯·奧爾森等,這并不能簡單地認為詩人在故意迎合西方。詩人現代詩創作原本就融入了他們的詩學,如被大陸和臺灣詩歌界普遍接受并認同的張錯詩歌“口語與雅言之間的平衡”“日常生活入詩”,與威廉斯提倡的“客觀主義”“要事物不要概念”“口語”“簡明清晰的描述性意象”;詩人提倡“隱喻是詩的本質”“詩的抒情意在召喚”與“投射詩學”提倡的“詩是把詩人的能量傳遞給讀者”,“隱喻不是詩的手段,而是詩的本質”{26},詩人在“形式上對中國新詩(十四行詩—引者注)的反叛”與“投射詩學”提倡的“詩是‘能的結構和‘能的放射,拒絕傳統的形式”等等均一脈相承。正是詩人對威廉斯、查爾斯·奧爾森等詩人詩學的接受,并在詩歌創作中踐行這一詩學主張,以“獨特的個性”詩學參與建構了臺灣現代詩新的詩學,但是,這一“獨特個性”英譯后回歸北美詩歌語境,自然又變成了北美詩學的“共性”。韋努蒂認為:“通過翻譯文本的選擇將外國文學非歷史化,即將它們與其意義賴以形成的文學傳統相剝離。外國文學文本常常被改寫以符合譯入語文學當下流行的文體和主題。”{27}正是由于“翻譯文本的非歷史化”不徹底,詩人翻譯時才沒有對詩歌進行改寫,而是亦步亦趨地步原詩后塵,且看《雙玉環怨》的開頭:
原文:本是一片天真無邪的頑石,/自從經過巧匠神妙的構思,/和在漫長歲月里精誠的撫割,/本來心硬如鐵的一塊翠玉,/竟被剔刻成一雙透澈玲瓏/難舍難分的雙玉環飾,/……/玉取其終始不絕,/君子如玉之真
英譯:Nothing but innocent, stubborn stone, originally, / But ingenious designing, / Devout cutting and a craftsmans handling turned / A hard jade stone / into an inseparable pair, / Tiny, delicate rings. /…/ Rings are without end; / The gentleman is as pure as jade/
自譯詩是對原文作“語義翻譯”,即表達形式與原文非常接近,同時為了達到“交際翻譯”的目的——譯作對譯文讀者產生的效果盡量等同于原文讀者產生的效果,即與譯文語境讀者“切磋與溝通”,詩人反對“音譯”,認為“音譯”等同于硬譯。“原文音譯實際等于未經翻譯的原文,為譯者的最后手段(last resort)。”劉紹銘曾委婉地批評張錯英譯詩歌不夠靈活,指出其“文字過于溫柔敦厚”{28}。這一評價也可借用過來評價張錯的自譯行為。詩人事實上對原文作“語義翻譯”,看似與他反對“硬譯”相矛盾,其實并不矛盾,正如韋努蒂所言,外國文學文本一旦與其意義賴以生成的文學傳統相剝離,便進入非歷史化語境,因此意譯或者改寫在所難免。然而,張錯英譯的詩雖然與賴以生成的傳統相剝離,卻因其原本就是中西詩學的結合與融通后的產物,因此,與當代北美詩歌傳統有“共性”之處,具體地說,詩的結構、表達技巧及其詩意的“非歷史化”都是不徹底的。
其次,即使詩的情感和語言源自中國古典,但是,這一“中國古典”特性在北美當代詩歌語境里的“非歷史化”也不徹底。鐘玲在記述1977年“美國詩人學會”在紐約召開的一次會議時,寫道:“與會的美國詩人,尤其是雷克斯羅思、莫文、史奈德,在發言時,都認為中國古典詩歌的英譯,對美國詩人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而且這些譯文已經成為美國詩歌傳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雷克斯羅思還認為他們譯的很多中國詩歌已經成為英文的經典了”{29}。
張錯長期在美國大學教書,撰寫過《當代美國詩風貌》(1973)、《當代美國女詩人詩選》(1980)、《馬丁遜詩選》(1982)。詩人還明確表示過,英譯臺灣現代詩的目的,是尋求與北美詩歌界的交流與切磋,因此可以肯定地說他既熟悉北美詩壇現狀,也熟悉北美詩歌研究和發展史,更細察中國詩學成為英文經典的流變,及其程度與因子,甚至在當代的流變及其流行趨勢。以《賞菊》詩為例,全詩都在感嘆個人身世的飄零,結尾兩句“流下的眼淚,是菊花,/還是杜甫”直接點題,即詩與中國古代杜甫《秋興八首》中“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有內在關聯。詩人選擇英譯這首詩,與北美詩歌界對杜甫的接受有關:北美當代詩歌界接受詩人杜甫,經歷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前和之后,與1980三個不同的年代。眾所周知,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前,龐德與其意象派詩人團體受中國古詩的影響,在此不贅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后,垮掉派的詩人雷克斯羅思(Kenneth Rexroth)、斯奈德(Gary Snyder)和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介紹中國詩最得力,其中包括杜甫。杜甫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非史詩非戲劇性詩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亞或荷馬優秀。至少他更自然,更親切。”“因為……他所關心的是人的堅信、愛、寬宏大量、沉著和同情,唯有這些品格才能拯救世界。”{30}“我30年以來沉浸在他的詩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個較為高尚的人,一個倫理的代理商,一個有洞察力的生物體。”{31}而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詩人們開始反對杜甫對“人的堅信、愛……”,轉而接受中國道家的無為而治的哲學、思想和詩思以及山水田園詩。比較文學認為“負影響”也是一種影響。可見,張錯自譯《賞菊》、輯入《閱讀〈道德經〉第20章》,一定程度上考慮到北美詩歌史對中國古典詩學的接受及其當代北美詩學接受中國古代詩學、思想的現狀。當然《道德經》第20章提倡淡雅寧靜的人生境界,《賞菊》詩表達出的對家鄉的思念,也是張錯所追求的,并且付諸在日常生活中。在此有必要說明,該時期美國詩人斯奈德接受中國“非經典”詩人寒山,是接受了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陳世驤的建議而為,可見,文學交流與文化走出去不能一味忽視對方。
詩人是比較文學出身,詩歌創作受到了當代美國詩的影響,在思維上已經養成了比較的方法,因此,盡管英譯詩歌選擇盡量與北美詩歌界對中國詩接受的軌道一致。但是,中國詩學,道家哲學及其思想在北美的影響畢竟有限,詩人知曉歷史及其帶來的文化倫理有所“匯通”不等于“等同”,便力求在審美感知上進一步尋求匯通,如摘引莎士比亞詩句“千曲之島”作詩集名,從而與莎士比亞等英美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詩的抒情作溝通式導讀與引領。張錯英譯詩的中國性因譯介選擇與語境的改變被削減,又正是基于這一身份系因空間和讀者的變化隨之變“新”,由此詩人精神歸依發生變化,從而詩人所生的立場自然發生變化。
三、詩思的中國性與世界性
張錯借重杜甫、《道德經》英譯經典在北美詩歌史的接受,使其英譯詩歌雖然脫離了原語語境,但卻沒有徹底的“非歷史化”。其實,在張錯英譯詩歌中,引用最多的是詩人李商隱的詩句,這也是基于詩的“非歷史化”事實,但卻與上述兩種“非歷史化”事實不可同一而語。
在英譯詩集《千曲之島》和《漂泊》里,三首《空言》《惘然》《寄托》詩分別引用了李商隱《無題》中的“來是空言去絕蹤”,《錦瑟》中的“只是當時已惘然”“望帝春心托杜鵑”作題引,可見詩人喜愛李商隱的程度之高。無獨有偶,美國漢學界尤其在中國詩抒情傳統的范疇里,闡釋李商隱及其詩《錦瑟》{32},較有影響有陳世驤、劉若愚和宇文所安。陳世驤認為,詩人從自己有限生命的循環變化,繼而窺探到自然無限時間的生與滅,最終抵達對宇宙之悲哀(cosmic sorrow)的感嘆{33}。劉若愚則認為,此詩從不同的層次上,表達著多重含義。有些人對此作象征意義的理解,有些人作寓意理解,“通過詩中提供的潛在線索,使詩的戲劇性情節可以有這樣或那樣的解釋或多種理解。”{34}孫康宜認為,李“詩歌是一種表演,詩人的表述是通過詩中的一個人物,作為自我掩飾和自我表現的一種手段”{35}。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認為,李商隱的詩尤其是無題詩“詩篇無法‘解譯,很可能是其目的所在”。同時又指出,李商隱詩可“解析”{36}。
以上詩人作為研究者媒介對李商隱詩《錦瑟》做了多元解讀,還有學者從歷史與詩的關聯角度,考證李商隱《無題·來是空言去絕蹤》與中國歷史的關聯,如旅美學人周策縱就做過考證,在此不贅。三首詩于1987年首次輯入英譯詩集《千曲之島》,結合當時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的形勢——1980年代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逐漸展開,經濟文化開始起色,形勢蓬勃;而此時的臺灣在民間展開了返鄉運動,提出“生,則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則讓我們回去獻上一炷香。”{37}這可能正是三首詩引李商隱詩句作題引的隱喻之一之所在。其次,張錯還可能除了借此抒發個人身在異鄉的漂泊身世,還包括詩人在經歷家庭變故后的孤獨與對親人思念的情緒。{38}更為重要的是,北美中國詩抒情傳統自1970年代提出,經由陳世驤、高友工、劉若愚直到王德威,在學界發展勢頭迅猛,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大陸作家與臺灣作家對臺灣文學的認知雖然波折不斷,但已經相對達成共識,如夏志清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再版時增加了對臺灣作家姜貴的分析,因此愿景已經實現。另一方面,北美的中國詩抒情傳統是華人漢學界媒介用來與西方敘事文學分庭抗禮的武器,并且對其理論的建構,從文學拓展到了藝術。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詩學建構不斷地遭到來自大陸、臺灣和國外學界的質疑,如抒情傳統把中國詩學狹隘化、絕對化。究其根源,中國詩抒情傳統的提出是基于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的結果,有民族主義的成分,因此,華裔研究者與北美的漢學家之間存在隔閡在所難免,另外,還存在美籍華裔與美籍臺灣出身學者及其詩學見解間的壁壘。而詩人雖然早已超脫,“詩是一種新的綜合,其視野更加開闊”{39}。詩人深知,民族主義“不是真正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就不該用它”。如一開始自譯時沒有把刀劍青銅器為詩題的詩輯入英譯詩集,但是,為了團結,為了正當化尋找理由時,提倡民族主義是必要的,“民族主義這個東西,為了團結,它就有用了;為了正當化尋找了理由……”{40}因此,詩人借由一個“非歷史化”的題材入詩,以詩學的中國性糾正臺灣現代詩虛無化的弊端,其真正目的是以“新的綜合”創造詩的“世界性”。事實上,張錯詩回歸傳統后,“不同于大陸新詩,又與臺灣鄉土傳統緊密聯系,因此詩是這一種新的綜合,其視野更加開闊”{41}。詩人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是,詩的抒情雖然是由歷史真實統領著,但卻建立在自然主義,而非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基礎上,《惘然》《寄托》以及《漂泊者》等描寫詩人在漂泊環境中的漂泊心理,但卻表達了漂泊環境的或悲、或憂、或壯或愁的境況,從而實現詩人個性與此環境下普遍性的融通。這一手法恰恰是在逃離西方占主導地位的二元對立與分離性思維范式,是典型的中國/東方一元性和相關性思維,不過它融合了古今、中外、傳統與現代。這正是1980年代北美詩壇持詩的“同類立場”的詩人們所追求的詩思,因此這是詩人張錯對北美當代詩學建構的貢獻,也是臺灣/中國現代詩對北美當代詩學建構的貢獻,世界文學是“一切超越其母語語境而流通、并積極地存在于他者語境中的文本和觀念”{42},因此,這一詩思可稱之為詩的世界性,它不同于1960年代詩人們追求的全盤西化的“世界性”,是中西歷史與詩學匯通的世界性,是詩人思維觀念的中國性對詩的世界性所作出的貢獻。
① 臺灣地區把1970-1983年之間的臺灣現代詩稱作新詩,以區別1970年代之前的現代主義詩歌,大陸則仍稱其為現代詩。北美學者用modern和modernism,語意上與大陸的“現代詩”接近,故本文采用了現代詩的稱謂。又,文中所有“臺灣”皆意指“臺灣地區”。
② 楊宗翰在《回歸臺灣新詩史里的抒情之聲——以張錯、席慕蓉、方娥真與溫瑞安為例》文中,將臺灣現代詩的“民族性”等同于“中國性”,而非“臺灣性”(楊宗翰:《回歸臺灣新詩史里的抒情之聲——以張錯、席慕蓉、方娥真與溫瑞安為例》。《江漢學術》2016年第6期,第45頁)。筆者認為,此處張錯的“中國性”“民族性”的概念內涵基本一致,即大中國性,其中包含臺灣在地鄉土性在內。
③ 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也提出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但與臺灣地區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倡導的“世界性”含義不同。陳思和教授對世界性因素,詳見陳思和:《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④{17}{40}{41} Cheung, Dominic. Chang Tso. 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 Edited and trans. Dominic Cheu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9, P139, P1, P1.
⑤ 楊宗翰:《回歸期臺灣新詩史里的抒情之聲——以張錯、席慕蓉、方娥真與溫瑞安為例》,《江漢學術》,2016年第6期,第47頁。
⑥ 林明德:《中國新詩選》,臺北:長安出版社出版1980年版。
⑦⑧⑨{11}{19}{20} 張錯:《詩的傳世〈批評的約會:文學與文化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8頁;第18頁;第19頁;第62頁;第62頁;第63頁。
⑩ Cheung, Dominic. The Continuit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aiwa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91(3). P399.
{12} 臺灣1986年《漂泊》只收錄詩人1983-1986年的作品,該詩集在1994-2000年重新印刷了4次,詩集的目錄沒有發生變化。因此,雖然該詩集以刀劍意象為題抒發家國情懷的詩并不多見,但這方面內容的詩可見于其他詩集。
{13} 馮至:《馮至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頁。
{14}{15}{23} 李鳳亮:《詩情·眼識·理據:現代漢詩的海外經驗—張錯教授訪談錄》,《彼岸的現代性:美國華人批評家訪談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第7頁;第11頁。
{16}{39} Cheung, Dominic. Drifting. Green Integer Press, Kobenhaven and Los Angeles. 2000. P1, P1. 又,文中引文未標注譯者的均為引者譯。
{18} 張錯:《滄桑〈漂泊者〉》,臺北:臺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13頁。
{21}{28} 劉紹銘:《一個和尚挑水吃——張錯英譯三十二家詩》,《文字豈是東西》,遼寧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頁;第119頁。
{22} Erikson, Erik H.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P. 1959. pp.17-19.
{24}{38} 引自張風博客文《推薦張錯詩集〈連枝草〉附陳義芝? 白靈文章》,2011年8月10日。http://blog.sina.com.cn/
zhangphong.
{25} 陳鵬翔:《張錯詩歌中的文化屬性/認同與主體性》,蕉風出版社2000年版(492),第103頁。
{26}{30}{31} Rexroth, Kennetn.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4. P7。參見張子清:《中國文學和哲學對美國當代詩歌的影響》,《國外文學》,1993年版第1卷,第1-13頁。
{27}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67.
{34} 劉若愚:《李商隱詩諸評之我見》,《臺灣中山大學中文學會編: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臺北:天宮書局1984年版,第135頁。
{29} 海岸:《中西詩歌翻譯百年論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93頁。
{32} 在中國,目前大陸和臺灣地區學界對李商隱僅《錦瑟》一詩的闡釋,據臺灣學人楊文雄考據,至2012年有15種之多,其中臺灣的闡釋主題分為“愛戀小姨”“失和王家”“人生悲劇”“追憶舊歡”,大陸的闡釋主題是“戀情”“詠瑟”“悼亡”“聽瑟曲”“傷唐室殘破”“游歷名區”“順宗內禪”“編集自序”“自傷身世兼悼亡”“自傷身世”“自敘平生”。
{33} 陳世驤:《陳世驤文叢》,臺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頁。
{35}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店2001年版,第255頁。
{36} 宇文所安.賈晉華,錢彥譯:《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376頁。
{37} 1987年,臺灣民眾發起返鄉運動,印發“我們已沉默了四十年”的傳單30萬份。傳單寫道:“難道我們沒有父母?而我們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們只要求:‘生則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則讓我們回去獻上一炷香。”這一運動直接促成了臺灣當局允許居民赴大陸探親。
{42}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
(責任編輯:黃潔玲)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ness and Nationality
of the Self-translated Poetry by Chang Tso
Zhang Man
Abstract: Poetry, written by Chang Tso in the 1970s, is known throughout the Chinese world of poetry, particularly in Taiwan, for its Chineseness, nationality, unique use of allusions and accurate use of words. However, his self-translated poems, in the category of North-American poetry and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North-America, is narrowed in its Chineseness as a result of the selected poems for translation and its unique nature of poetry in the context of new Taiwanese/Chinese poems is reduced. Although the translated poems in English are detached from the poems in the original and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the detachment is not thorough and because of the poets experience of many ups and downs in his life, his spiritual conversion shows a slow tendency of complexity and plurality, leading to changes in his position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ism. As a result, his translated poems in English have acquired new values in the new context in that his Chinese-style poetic thinking and its reflection in the translated poems in English have taken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etrys cosmopolitanism.
Keywords: Self-translated poetry by Chang Tso, Chineseness and nationality,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North America, cosmopolit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