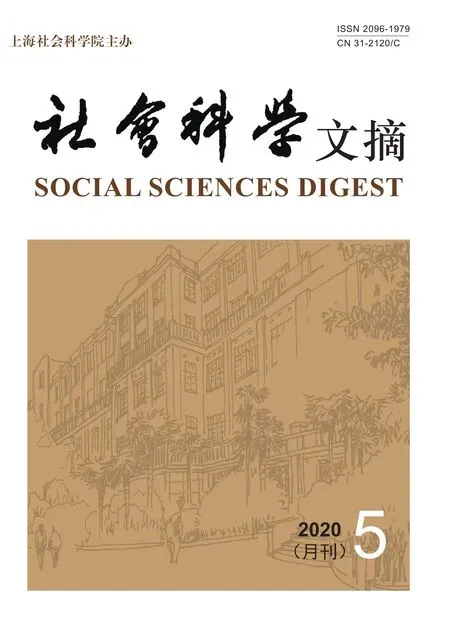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與全球衛生治理
——以世界衛生組織改革為主線
文/晉繼勇
因應日趨嚴峻的全球衛生治理挑戰,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組織,WHO)歷任總干事都力圖通過改革來促進全球衛生安全。為此,該組織先后發起了“初級衛生保健”改革(primary health care)、“一個世界衛生組織”改革(one WHO)和“世界衛生組織DNA”改革,都對WHO的全球衛生治理功能產生了重要影響。2019年底爆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幾個月內發展成為自世衛組織成立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全球衛生安全危機。這不但對全球衛生治理體系構成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也是對該組織改革成效的重要檢驗。在當前“國家主義”盛行和大國關系惡化的國際政治氛圍下,作為聯合國專門機構,世衛組織為提升全球衛生治理能力而開展的改革努力也面臨諸多局限和新的挑戰。
世界衛生組織改革的動因
(一)應對“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力
2003年爆發“非典”危機,暴露了世衛組織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和應對能力方面存在的缺陷,為此世衛組織在2005年修訂了《國際衛生條例》,2007年正式生效。《國際衛生條例》(2005)第六條要求,“締約國如果有證據表明在其領土內存在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意外和不同尋常的公共衛生事件,不論其起源或來源如何,應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所有相關的公共衛生信息。”所謂“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通過疾病的國際傳播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危害”,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的“不同尋常”事件。而具體是否宣布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由總干事根據成立的“突發事件委員會”所做出的評估意見來最終決定。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世衛組織共宣布過五次“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然而,在應對其中兩次全球衛生危機中,卻因其“過度反應”和“反應遲緩”而備受批評,這使得世衛組織不斷面臨改革壓力。
(二)內部協調機制陷入“碎片化陷阱”
作為一個國際官僚機構,世界衛生組織獨特的分權化區域治理結構,也被認為是導致其全球衛生治理功能失調的一個重要原因。世衛組織《組織法》規定,“區域委員會由該管區域會員國及副會員之代表組織之”,“區域委員會應自行制訂議事規則”,“就絕對有區域性之事項決定施政方針”。上述規定決定了世衛組織權力高度分散的治理結構,各區域辦公室在其領導層任命、預算以及優先事項上擁有高度自治權。這種官僚結構造成組織內部折沖和相互重疊,妨礙了政策實施。因此,如何通過治理結構改革,有效解決總部和各區域辦公室之間的溝通失靈問題,改變各自為政、相互脫節的狀態,就成為世衛組織的一項重要改革任務。
(三)融資體系面臨嚴重挑戰
世衛組織的融資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世衛組織評定會費零增長嚴重制約了其項目預算。在凍結成員國繳納評定會費絕對數增長的情況下,考慮到每年的通貨膨脹因素,世衛組織的財政狀況難免入不敷出,這也是世衛組織在2014年西非國家埃博拉危機期間反應遲鈍的一個原因。其次,世衛組織對自愿捐助過度依賴。其中大部分自愿捐助所流向的項目和所確定的優先事項都受捐助國偏好驅動,而非由世衛組織所確定。世衛組織在預算方面對捐助國的過度依賴,弱化了其項目預算決策權,將明顯屬于多邊機構的控制權轉移到富有的捐助國手中,不但扭曲了全球衛生的優先事項,而且嚴重制約了該組織的自主性和全球領導地位。因此,如何促進世衛組織融資的靈活性和可預測性,提升其自主性,也成為世衛組織面臨的重要改革任務。
世界衛生組織改革的進程和路徑
(一)“初級衛生保健”改革
20世紀70年代,廣大發展中國家掀起了“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政治斗爭大潮,呼吁實現全球發展正義。作為以發展為導向的重要國際組織,世衛組織也成為發展中國家追求“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要平臺。在時任世衛組織總干事馬勒的推動下,1977年世界衛生大會通過決議,“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政府未來幾十年的主要社會目標是,在2000年之前使所有世界公民達到能使他們過上社會及經濟富裕生活的健康水平”。1978年召開的國際初級衛生保健大會通過了《阿拉木圖宣言》。該宣言提出,初級衛生保健是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目標的關鍵和基本途徑。馬勒是《阿拉木圖宣言》的主要設計者和推動者,他認為,要想實現初級衛生保健,世衛組織應當通過為各國提供理性而系統的規劃,對稀缺的國家資源進行分配。也就是說,世衛組織需要將資源下沉至國家層面,通過介入其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衛生體系建設,實現初級衛生保健。馬勒推動的《阿拉木圖宣言》是20世紀全球公共衛生領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阿拉木圖宣言》的啟示下,1979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于衛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決議”,將衛生議題融入全球發展議程之中。
(二)“一個世界衛生組織”改革
20世紀9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被認為到了改革的生死關頭。1997年,全球二十位衛生專家在《柳葉刀》發表宣言,呼吁新任總干事布倫特蘭對世衛組織進行改革。正是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改革壓力之下,作為首位沒有任何世衛組織工作經歷的總干事,布倫特蘭上臺伊始就承諾要對世衛組織進行重大變革,以圖重振它在全球衛生事務中的中樞地位。
布倫特蘭的改革議程主要分為三個方面。首先,重組世衛組織總部機構。通過每周定期討論相關重大問題,形成一種更加平衡的內部橫向治理結構。這一改革舉措使組織內部決策條塊分割的狀態得到極大改善,扭轉了總部“左手從來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的尷尬局面。其次,改革世衛組織的預算。力圖實現“一個世界衛生組織、一個預算”(one budget for one WHO),來取代以往由區域辦公室負責預算的做法。最后,加強對各區域辦公室的控制權,在國家層面加大對國家辦公室的干預,提升世衛組織在國家辦公室的能見度。毋庸置疑,布倫特蘭對世衛組織的結構性改革可謂雄心勃勃,也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遺產。但其改革成功之處僅限于世衛組織總部的部門協調,就結構性改革而言,布倫特蘭的努力卻未能如愿。
(三)世界衛生組織的“DNA變革”
上任伊始,譚德塞就成立了針對世衛組織改革的“全球政策小組”,由總干事和六位區域主任組成。經過二十多個月的醞釀,譚德塞的世界衛生組織改革方案在2019年正式出臺,該方案致力于強化世衛組織的四個支柱。首先,通過強化項目支柱來推動全民健康覆蓋,促進全球衛生安全。世衛組織還推動各國領導人在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全民健康覆蓋高級別政治宣言》,極大地提升了“全民健康覆蓋”的國際政治能見度。其次,通過強化應急支柱,提升針對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該支柱旨在幫助各國強化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和預防能力。再次,對外關系和治理支柱將負責集中開展和協調世衛組織在資源調動和宣傳交流方面的工作。最后,業務活動支柱將致力于確保世衛組織更專業地履行在預算、財務、人力資源和供應鏈等領域的重要職能。這一支柱還包括在日內瓦總部設置首席科學家部門,以加強世衛組織的核心科學工作,確保組織規范標準的質量和一致性。
世衛組織全球衛生治理功能的強化
功能主義理論認為,人類事務可以分為兩個領域,一個是政治領域,另一個是專業技術領域。作為一個功能性聯合國專門機構,世衛組織的全球治理功能更多體現在其專業服務方面。世衛組織的改革進程和路徑正是為了強化上述功能。
首先,改革強化了世衛組織的價值引領功能。無論是《阿拉木圖宣言》還是《阿斯塔納宣言》,都強調了全民健康覆蓋對于實現全球衛生正義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譚德塞改革中的項目支柱聚焦推動全民健康覆蓋,充分體現了世衛組織在全球衛生治理中的價值引領功能。譚德塞將全民健康覆蓋作為其重要改革目標之一,充分體現了世衛組織對全球衛生治理的倫理價值追求。
其次,強化全球衛生治理協調功能。世衛組織一直“充任國際衛生工作之指導及調整機關”,譚德塞改革更將對外關系和治理改革作為四個重要支柱之一,力圖提升世衛組織在全球衛生治理中的協調領導能力和組織一體化。為便于總部與國家辦公室之間進行直接溝通,譚德塞啟動了“戰略政策對話”,成立了“跨部門小組”,其小組成員分別來自國家辦公室、區域辦公室和總部,促進了組織內部的一體化。
再次,改革提升了應對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功能。面臨日趨嚴重的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威脅,衛生應急能力建設成為譚德塞改革的重中之重。世衛組織主要通過以下兩個方面來強化其應急能力:一方面,強化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能力;另一方面,強化世衛組織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防范能力。如何通過強化各國、特別是公共衛生能力薄弱國家的突發事件防范能力已成為世衛組織的關注點。譚德塞啟動改革后,世衛組織成立了新的突發事件防范部門,以圖進一步促進該組織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范能力建設。
最后,改革進一步突出了世衛組織的規范和技術功能。世衛組織的專業技術規范能力有助于促進其獨立性。也就是說,技術規范是世衛組織的立威之本。譚德塞的改革強化了世衛組織的規范和技術功能。世衛組織首次在總部設置首席科學家部門,不但提升了其預測和了解最新科學進展的能力,增加了利用這些進展改善全球健康的新機會,還提升了世衛組織的核心技術職能,包括規范、標準和研究的卓越性、相關性和高效率,從而可以提供更好的全球衛生公共產品。
世衛組織改革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21世紀的全球衛生安全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也成為譚德塞改革成效的試金石。作為衛生安全領域唯一的全球性多邊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充分發揮其全球衛生治理功能,成為全球衛生安全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推動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協調者”、全球抗疫薄弱環節的應急“補位者”和全球抗疫規范和技術的“提供者”。
首先,作為全球衛生治理價值觀的引領者,世衛組織積極推動全球衛生安全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注入了道義動力。實際上,在本次疫情爆發前夕,譚德塞就強調,“在流行病領域,我們負有共同責任,擁有共同命運”。世衛組織所推動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觀念成為全球合作抗疫的價值引領。
其次,作為全球衛生安全合作的重要平臺,世衛組織發揮著重要的協調和溝通職能,是全球抗疫合作無可替代的“國際協調者”。為了引導國際社會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正確輿論,世衛組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協調行動,對抗謠言和虛假信息的傳播,甚至有人認為,“世界衛生組織正在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交媒體影響者”。世衛組織在協調國際輿論方面正視聽、明是非,為全球合作抗疫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對外,其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評估新冠肺炎疫情的潛在經濟影響,制定緩解戰略,并提出了政策選擇。對內,其在總部、區域辦公室和國家辦公室層面實現三級聯動,強化內部協調機制。總之,世衛組織的積極協調為全球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貢獻。
再次,世衛組織充當了全球抗疫薄弱環節的“補位者”。譚德塞將衛生應急能力建設作為世衛組織改革的四大支柱之一,對于世衛組織而言,如何幫助那些衛生能力脆弱的國家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全球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一環。在非洲出現確診病例后,非洲疾病控制中心成立了“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應對工作組”,并任命2名特使,專門為非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戰略咨詢。在伊朗成為疫情重災區之后,世衛組織向伊朗派遣專家組,支援伊朗疫情防治工作。世衛組織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應急努力,成為全球防疫薄弱環節的重要補充力量。
最后,世衛組織成為全球抗疫規范和技術的“提供者”。相比向各國提供的應急支持,世衛組織的規范和技術建議對于各國疫情防控更為重要,這也是其專業優勢的體現。正如世衛組織發布的報告認為,“各國寄予世界衛生組織的,不是財政或物資支持,而是提供基于國際證據和經驗的戰略性建議”。世衛組織充分發揮其規范功能和衛生技術權威,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科學的風險警示、防控手段和診療標準建議。總之,世衛組織通過充分發揮其專業優勢,為各國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效的規范指導和參考。
結語
作為二戰后建立的最重要的多邊衛生合作機制,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衛生治理領域也一直存在能力赤字問題,具體表現在全球突發公共衛生危機應對機制遲緩、協調機制碎片化、過度依賴自愿捐款財政而導致自主決策邊緣化等方面。而這種能力赤字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各成員國特別是大國將世衛組織工具化,另一方面,“衛生問題涉及主權概念下眾多復雜困難的政策平衡”,結果造成世衛組織對于國家主權的敏感。為了縮小自身的治理能力赤字問題,世衛組織進行了多輪改革,但是個別成員國對狹隘國家主義的固守和“政治化”操作,使世衛組織難以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世衛組織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其專業規范性,因此,在“反全球主義”大行其道、多邊主義舉步維艱的時代,那種希冀該組織通過改革而成為“全球衛生部”的想法是一種盲目樂觀。盡管如此,國際社會必須認識到,世衛組織是為全人類健康福祉而開展政治合作的舞臺,而不是成員國開展政治比賽的競技場。作為以公共衛生科學為立身之本的世衛組織,無疑應當成為各國凝聚抗疫共識和推動全球抗疫行動的理想平臺。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以來國際社會遇到的最嚴重的衛生安全危機,更是對21世紀全球衛生安全治理體系和能力的檢驗,顯而易見,目前的疫情防控局面可謂喜憂參半。在全球疫情爆發期間,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國家之間的守望相助,見證了世界人民的戮力同心;另一方面,我們也目睹了大國關系惡化、民族主義、戰略脫鉤等危及全球衛生治理體系根基的不利趨勢。在全球疫情危機面前,健康的全球衛生治理體系需要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包容,需要國際社會在全球抗疫資源、疫苗藥物研發等方面的積極互動和合作共享。唯有訴諸通力合作、彰顯責任擔當,共同為以世界衛生組織為主體的全球衛生治理機制運作創造有利的國際政治環境,全球衛生治理才能真正進入健康的運行軌道,世界衛生組織未來也才會有更大的改革空間來提升其全球衛生治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