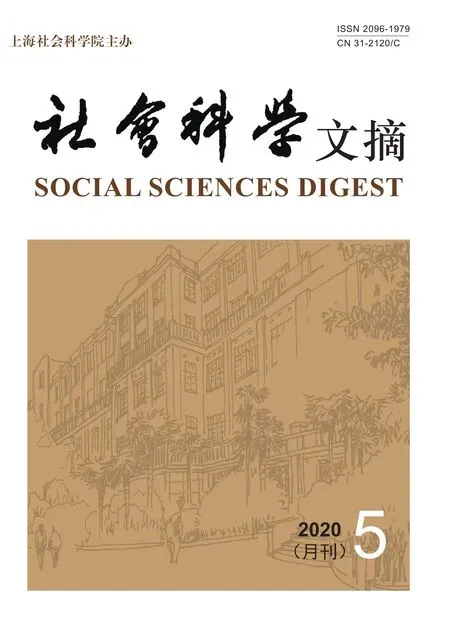強奸罪司法認定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
文/田剛
近10余年來,在我國刑法學界高舉“法教義學”大旗,全面轉向解釋論研究的背景下,強奸罪研究的“陳舊”和“封閉”更顯突兀。當前司法實踐中強奸罪的司法認定標準早已是雜亂無章,理論界對強奸罪司法困境的忽視,已成為一種逃避責任的“理論惰性”。
問題的提出:當前強奸罪司法困境的宏觀表現和微觀分析
(一)強奸罪司法適用現狀的考察:基于507份強奸罪刑事判決書的樣本分析
筆者以近10年來507份強奸罪判決書為樣本,對我國強奸罪司法適用現狀進行分析。從整體看,樣本中強奸罪多發生在陌生人之間,占比近70%,與此同時,強奸罪的既遂形態在實踐中最為常見,占比近70%,而中止形態則較為少見,占比不到3%。根據樣本數據,強奸罪在司法實踐中普遍具有犯罪人主動供述犯罪事實的情節,犯罪人未供述犯罪事實而被定罪的僅占約8%。在作為樣本的裁判文書中,普遍有對強奸罪的核心特征系“違背婦女意志”的表述。
根據上述樣本數據,可以對當前強奸罪的司法實踐得出以下初步結論:結論一,強奸罪多發生在陌生人之間,且熟人強奸與陌生人強奸之間無行為手段層面的明顯差異;結論二,強奸罪的犯罪人普遍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且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行為人采取“暴力”手段和合意奸淫幼女手段的比例更高;結論三,審判機關普遍明確表述“違背婦女意志”是強奸罪的核心特征,未明確表述的多集中在“其他”手段和合意奸淫幼女的情形。
(二)強奸罪認定司法困境的宏觀表現:法益保護功能嚴重不足
根據上述樣本結論作原因分析,可以發現我國當前強奸罪司法實踐中,對強奸罪的法益保護存在著嚴重不足。
第一,強奸罪中最為常見的熟人強奸定罪困難。結論一同域外強奸犯罪實證研究中強奸犯罪多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普遍性結論不一致。而從我國強奸罪立案情況來看,熟人強奸所占的比例也近50%,同樣本統計的比例差異明顯。因此,在當前強奸罪司法實踐中,陌生人強奸更容易被定罪,而更為常見的熟人強奸定罪則較為困難。
第二,難以有效制裁缺乏有罪供述的強奸罪犯罪人。從結論二來看,并非強奸罪犯罪人更愿意認罪伏法,而是不肯供認犯罪事實的強奸犯罪人普遍難以定罪,甚至難以啟動立案偵查程序,換言之,目前的強奸罪司法實踐中高度依賴“口供”。
第三,其他相關實證研究結論同樣表明,我國大量現實中的強奸犯罪無法通過司法審判最終定罪。聯合國人口基金曾資助我國學者對2120名受訪者展開了調查,結果顯示21%的女性遭遇過來自非伴侶的既遂或未遂的強迫性行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近年來強奸案件的立案數量與現實情況明顯不匹配,2017年為27664件、2016年為27767件、2015年為29948件,而最終法院宣判的強奸犯罪案件實際上都不足5000起。強奸罪的法益保護在應然與實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
(三)強奸罪認定司法困境的微觀分析:行為定性規則的模糊混亂
司法實踐中被告人未供認犯罪時的強奸案件,審判機關往往要進行一定的說理,否定被告人的辯解,因此也就成為了本文考察司法實踐中強奸罪認定規則的突破口。
1. 被告人未供認犯罪樣本的強奸罪成立分析
根據被告人未供認犯罪的樣本,可以發現司法實踐中強奸罪認定的以下幾個特征。第一,暴力和抵抗因素并非核心要素,且二者之間在證據上亦無必然聯系。第二,及時報案成為核心要素,特別是在24小時內報案。第三,對被告人“被害人系自愿”的辯解,否定依據較為雜亂。整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類:(1)以客觀上暴力、抵抗為否定依據;(2)以及時報案、公開犯罪事實為否定依據;(3)以認識錯誤不成立為否定依據;(4)以現場沖突為否定依據;(5)以被告人躲避公安機關為否定依據。
2. 強奸罪司法認定的核心特征模糊和具體規則混亂
從上述樣本數據分析來看,目前強奸罪在具體司法認定過程中存在著兩方面明顯問題。
一方面,“違背婦女意志”強奸罪核心特征認識的模糊。根據上述樣本,司法實踐中對強奸罪的核心特征出現了“手段非法性”“被害人主觀上否定”“犯罪人主觀認知”3種不同的解釋,而3種認知之間還存著明顯沖突,這已然說明了司法實踐對強奸罪理解的模糊。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基本一致的核心特征認知下,具體規則依然會出現嚴重沖突。例如,以樣本中最為常見的“被害人主觀上否定”特征為例,有樣本中審判機關認為,存在輕微抵抗,就足以認定被害人主觀上對性行為的否定;有樣本中審判機關主張,被害人沒有抵抗但是有言語拒絕,就可以成立強奸;有樣本中審判機關則提出,被害人沒有抵抗也沒有言語拒絕,但被告人未征詢被害人同意進行性行為,亦足以認定為成立強奸;還有樣本中,審判機關卻明確提出,被害人的輕微抵抗不足以體現被害人主觀上否定性行為,因此,僅有輕微抵抗不能成立強奸。因此,當前強奸罪司法實踐中的認定規則混亂,已然嚴重影響司法的統一和公正,稱之為司法亂象毫不為過。
問題的核心癥結:“40年不變”的強奸罪核心特征與認定規則
(一)“違背婦女意志”核心特征理論通說的僵化
1984年《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當前強奸問題的解答》),將“違背婦女意志”作為強奸罪的核心特征,該核心特征近40年來一直沒能進一步完善,已然成為“僵化的理論”。
其一,“違背婦女意志”本身內涵的模糊。“違背婦女意志”存在兩種解讀:在犯罪分子視閾下,是指犯罪分子認識到同被害人進行性行為是違背被害人意志的,即上文樣本統計中的“犯罪人主觀認知”觀點;而在被害人視閾下,則是指犯罪分子同自己進行性行為是違背自身意志的,即上文樣本統計中的“被害人主觀上否定”觀點。如果是前者,當行為人誤認為同被害人進行性行為是符合被害人意志時,即行為人出現認識錯誤時,則不應當成立強奸罪,而這顯然同我國實踐中的觀點不符。如果是后者,則更為復雜。一方面,行為人要如何去確定被害人的內心意志?另一方面,當被害人認同性行為,但行為人認為是違背被害人意志時,行為性質如何來認定?顯然,無論哪一種解讀,都會使司法機關在特定案件的審理中難以應對,因此,“違背婦女意志”的內涵長期被司法實踐模糊化處理。
其二,“違背婦女意志”同設立強奸罪法益基礎的沖突。作為強奸罪核心特征的“違背婦女意志”與作為設立強奸罪保護的法益基礎的性自主權之間,卻存在著明顯的沖突。性自主權本質是一種處分權能,是法益主體根據綜合考量對自身性行為的自由處分,而“違背婦女意志”卻僅關注法益主體的主觀心理活動,忽略了權利處分的復雜性。例如,甲男對乙女有恩,甲男對乙女提出發生性行為的要求,乙女主觀本不愿同甲男發生性行為,但礙于恩情,又與甲男發生了性行為。此時,性行為的發生違背了乙女的意志,但是并未侵害其性自主權。因此,從強奸罪的法益基礎來看,“違背婦女意志”不宜作為強奸罪的核心特征。
其三,“違背婦女意志”構成要件定位的爭議。我國大部分學者認為“違背婦女意志”屬于強奸罪的犯罪客觀方面要素,但又無法合理解釋“意志”這一典型的主觀心理活動如何成為外在的客觀行為。因此,有關“違背婦女意志”在構成要件中的地位,我國理論和實務中一直難以進行準確地界定。
(二)強奸罪核心特征外化的“抵抗規則”嚴重滯后
《當前強奸問題的解答》實質上在“違背婦女意志”核心特征指導下,對強奸罪客觀行為手段進行了界定:暴力手段是“不能抗拒”、脅迫手段是“不敢抗拒”、其他手段是“無法抗拒”。因此,《當前強奸問題的解答》實際上創制了以“被害人的差異化抗拒表現”來認定強奸罪的規則。
這種以“抗拒”為核心的規則,在犯罪人進行無罪辯解時,犯罪的成立高度依賴暴力因素,甚至是嚴重暴力因素的存在,這一弊端又進一步導致了現實中大量強奸行為難以通過司法程序定罪。因此,根據上文的樣本顯示,“被害人的差異化抗拒表現”規則已然嚴重滯后,而刑法學界又疏于提供理論指導,于是司法機關不得已開始自行進行“補救”。一方面,開始自行增設“佐證規則”。諸如陌生人關系、被告人的前科、被告人及時報案、向親友公開等開始作為強奸罪成立的重要輔助證據,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被告人及時報案和向親友公開。從上文樣本統計來看,不乏大量司法機關將其認定為“違背婦女意志”的核心證據,隱然已具有“司法慣例”的色彩。另一方面,開始自行對“被害人的差異化抗拒表現”規則進行“改造”。例如,將“抗拒”擴大解釋為任何輕微的肢體抵抗或單純的言語拒絕,甚至開始放棄“抗拒”,直接從缺乏被害人的明確授權來認定強奸罪。然而,上述規則“改造”都是在基層司法機關“各行其是”的環境下進行的,新舊各類規則摻雜,必然造成強奸罪司法實踐的混亂。
困境突破的基礎思路:確立“缺乏被害人同意”為強奸罪核心特征
(一)“缺乏被害人同意”取代“違背婦女意志”的優勢性分析
其一,存在形態的優勢。“缺乏被害人同意”是一種客觀狀態,有明確的客觀外化表現——未經被害人同意的性行為。而“違背婦女意志”是一種主觀心理,必須通過進一步的主觀考察才能確定。因此,一個在客觀上未經被害人同意的性行為,無法直接認定屬于違背被害人意志,甚至被害人的言語拒絕和輕微抵抗亦不足以證明違背被害人意志。
其二,法益結合性的優勢。“缺乏被害人同意”同強奸罪保護的法益的結合更為緊密,同意是一種授權行為,本身就是性自主權的權利處置,而“違背婦女意志”無法同法益直接聯系。因為意志是一種思想狀態,思想狀態必須先外化為客觀行為,才能處置權利。
其三,構成要件地位優勢。強奸罪中法益主體的同意,屬于構成要件阻卻事由,因為法益主體的同意實質上是同行為人達成了“合意”,使行為不再具有法益侵害性,因此不成立犯罪。因此,“缺乏被害人同意”也就成為了一種明確的成立強奸罪的客觀構成要素,而“違背婦女意志”則無法在構成要件中找到自身的合理定位。
(二)強奸罪中認識錯誤司法難題的解決
在懲治強奸罪的司法實踐中,常常要面臨這樣的難題:如果強奸案的被告和被害人對性行為有完全相反的認識應如何處理?若在“缺乏被害人同意”的核心特征下重新審視,會發現上述認識錯誤司法難題將得到合理的解決。“被害人同意”是一種法定的授權行為,具有鮮明的規范化屬性。正如同行為人不能拿走熟睡被害人的財物,然后宣稱自己未經同意拿走被害人財物是事實認識錯誤一樣,行為人于對性自主權產生了錯誤認識,應當屬于法律認識錯誤,不影響行為性質的判斷;而對于上文中被告人同被害人達成性交易合意的情形,考慮到被害人對前往賓館同被告人發生性行為已然同意,是符合法定要求的性自主權處分行為,盡管被害人處于醉酒狀態但并非完全喪失意識,可以收回同意的表示但是全程未收回,應當認為被告人并非進行了“缺乏被害人同意”的性行為,強奸罪不應成立。
問題解決的細化方案:以“肯定性同意”為認定強奸罪的具體規則
(一)強奸罪認定基本規則的域外流變
早期英美法系國家認定強奸罪的合理抵抗規則,同我國的傳統認定規則類似,以被害人在不同意心理狀態下通常會采取的抵抗程度為標準。隨著英美法系國家強奸犯罪改革的深入,新的“否定性同意”規則被提出。“否定性同意”是指,被害人只需要在言語上表現出對性行為的不同意,不需要作任何抵抗,就可以認定性行為系“缺乏被害人同意”,應當成立強奸犯罪。隨著性自主權法益的全面保護日益受到重視,“肯定性同意”規則逐漸被英美法系國家立法機關和理論界所認可,即:在沒有被害人自由的、肯定性的對性行為的同意表示時,同被害人進行的性行為都應當認定為“缺乏被害人同意”,成立強奸罪。
大陸法系國家強奸罪的成立,普遍要求行為人使用暴力,或使用對身體或生命有現實危險的脅迫,或利用被害人無保護的狀態,本質上依然是合理抵抗規則,但近年也開始向“否定性同意”規則轉向。例如,2016年德國通過了強奸罪的重大修正,成立強奸罪不再需要暴力、脅迫或處于危險狀態,只要被害人明確提出否定表示,就可以成立強奸罪;法國新的《反性暴力及性歧視法》也對成立強奸罪的暴力、脅迫條件進行了修正,對性行為的否定替代了對行為手段的考查,成為強奸罪認定的核心。
(二)本土化的“肯定性同意”規則之提倡
具體到我國強奸罪立法的完善,在樹立了“缺乏被害人同意”為強奸罪核心特征后,未來我國的強奸罪認定規則應當如何選擇?
筆者認為,“肯定性同意”是我國的最優選擇。首先,“肯定性同意”規則同“缺乏被害人同意”核心特征最為契合。“肯定性同意”的本質,是合法性行為的發生必須有肯定性語言或行為的存在,而這也是“同意”最為直觀、明確地表現。其次,“肯定性同意”規則是充分尊重和保障性自主權的表現。以搶奪罪中對財產權的保護為例,倘若司法認定規則要求被害人財物被行為人搶奪時,被害人必須當場對搶奪行為提出否定,否則不能成立搶奪罪,這無疑是荒謬的。那么同樣的規則為何可以適用于性自主權的刑法保護之中?因此,“肯定性同意”規則并不是對性自主權的過度保護,而是僅僅實現了同等保護。進一步來看,對特定法益的保護程度,核心依據是法益的重要程度,隨著社會性自主權意識的覺醒,性自主權的人格尊嚴屬性凸顯,實質上提升了設立強奸罪法益的重要程度,采用更有利于性自主權保護的認定規則,不能視為一種是過度刑法保護。
綜上所述,將“肯定性同意”規則作為我國認定強奸罪的新規則并不會產生“水土不服”的問題。實際上,盡管“肯定性同意”規則未被我國刑法學界普遍認可,更沒有司法解釋予以明確,但是我國基層司法機關已經開始自行探索適用。然而,這種“司法能動性”雖值得肯定,但亦會破壞我國的司法統一性。因此,吸收司法機關有益嘗試的經驗,規定以“缺乏被害人同意”核心特征為基礎的“肯定性同意”規則,是解決當前我國強奸罪司法認定面臨的問題的最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