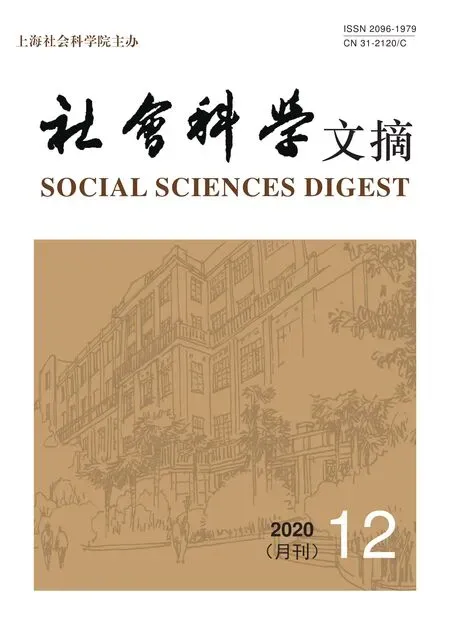國籍觀念在晚清中國的生發與實踐
文/邱志紅
國籍觀念與制度系源自西方社會,其相關概念于19世紀隨著西力東漸而出現于晚清的社會生活中,并通過1909年清政府制定頒行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近代意義的國籍法——《大清國籍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奠定了父系血統國籍觀念的法理基礎;其影響所及,自民國初年以來的兩部國籍法及至當代的國籍政策都有程度不同的繼承和表現。已有研究對國籍觀念在晚清中國的產生、發展過程還缺乏具體、深入的闡釋,特別是“國籍”相關概念在中國傳統法律中的思想因子與呈現方式,國人對這一概念早期理解的時代特點,及其對晚清中國政治社會的影響,均還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本文嘗試從概念史的角度考察國籍觀念在晚清的形成與實踐,以期豐富對中國近代國家轉型過程中國籍問題引發的復雜歷史細節的認識與思考。
外與內:國籍觀念的思想因子
國籍是伴隨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從國際政治體系中演變而來的新的法律概念。現代英語世界中Nationality和Citizenship均有“國籍”的意涵,用以指涉一個人在法律上的國家成員身份,二者經常交替使用。一般情況下,Citizenship經常是在國內法層面上強調“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更多地被譯作“公民權”或“公民身份”,而Nationality則是在國際法的層面被使用,強調國家與其管轄下包括本國人、外國人和無國籍人在內的“國民”之間的法律聯系。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國籍,既是具有領土、主權、政府的現代民族國家國民身份的主要標志,也是國民與國家之間權利與義務的主要依據,是連接國民與國家身份關系的重要的法律紐帶。換言之,國籍的本質是區別不同國家國民的身份問題,即是“哪國人”的問題。
國籍觀念脫胎于現代民族主權國家的形成中。而中國在數千年以帝制為核心的王朝國家統治之下,無法衍生出指涉個人與王朝政府關系的“國籍”及其相關概念,完善的“戶籍”制度則是連結二者關系的重要紐帶,是歷代統治者保障兵源、征收賦稅、穩定社會秩序的工具。
但在中國法律傳統中,從唐律開始,便存在著“化外人”“化內人”的概念,前者且為后世所沿用,并且生發出“外夷”“外國人”等詞匯。就法史學研究而言,究竟律例中的“化外人”“外國人”概念是否與近代國際法意義上的“國籍”概念相一致,值得考察。
根據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國籍”觀念的發展脈絡,一個國家在制定“國籍法”以區分本國人和外國人的法律身份時,是以承認有其他平等主權“國家”的存在為前提的。這個前提條件在傳統中國顯然并不存在。19世紀尤其是19世紀40年代前,作為“天朝上國”的中國封建王朝與周邊鄰國(包括邊疆民族)關系的展開是在朝貢體系之下進行的。朝貢體系的核心理論來自傳統中國的“天下”觀念與華夷之辨。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我們來看中國法律傳統的外化人概念,無論是唐律中屬于“蕃夷之國”的化外人,還是大明、大清律中來降、朝貢的外化人、外國人,他們所從屬的國即所謂的“蕃夷之國”、夷國和朝貢國,都不是基于純粹的政治地理空間,而是文明、文化觀念上建構的國之概念。作為中原王朝的中國,面對這些所謂的“他國”,不是按照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原理,如平等、主權等與之交往,而是通過“書同文”的文化推進,不斷將其納入“四夷懷服”的朝貢體系。
傳統中國的天下觀念中難以完全生發出明確的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國界”或“邊界”意識,但中國法律傳統中,針對不同的法律適用對象,仍有不同的法律規范,如唐時的化外人依自國所謂“俗法”或“本俗法”的法律管轄;化外人與化內之“民”間的交流,如旅行、貿易、婚姻等,則皆為法律所不允許,且嚴格限制民人外出的范圍。明朝政府將那些違反海禁國法而前往化外之地的海外移民視為“逃民”與“罪民”。清朝開國之初,為了防止沿海民人與鄭氏集團或“三藩”等反清勢力相結合,清政府大力推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將出洋者一律視為“政治犯”“謀反者”和“逆賊”。臺灣鄭氏政權被消滅后,清政府雖然解除了海外貿易的禁令,并準許1717年前出洋者回籍為民,但人民出洋仍在禁止之列,那些“甘心異域”“存留不歸者”即被歸為“不安本分”之列,被政府視為海外潛在的威脅。一直到嘉道時期,面對內憂外患的紛至沓來,清政府對待海外華人仍大抵視其為“天朝棄民”,抑或是“自棄王化者”,采取“概不聞問”的消極態度。由此觀察,海外華人身份問題長期為清政府所忽視。
晚清地方官民與西方國籍制度的初次接觸
世界上第一次國籍立法實踐發生在法國大革命時期,1791年的法國憲法確定了憲法規定國籍的方式,并以法律形式確認了對海外國民的保護權利,此種精神后來為大多數國家所仿效和繼承。直至1842年普魯士頒布世界上第一部單行的國籍法,單行法取代附屬法的國籍立法模式逐漸發展為世界趨勢。血統主義(以父母的國籍為準賦予子女原始國籍)與出生地主義(以子女的出生地為準賦予原始國籍),被確認為國籍取得的兩大基本標準。按照西方國籍法理論,除了以出生賦予原始國籍外,西方國家還接受繼受國籍以及婚姻、收養等方式取得國籍。海外華人移民在僑居生活中逐漸接觸到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典章制度,包括國籍等法律制度,一些華人通過出生、婚姻、歸化等方式,建立起其與這些西方國家法律上的聯系。而隨著西方列強殖民勢力在全球范圍的擴張,僑居殖民地國家的華人便有取得相應宗主國臣民身份的可能。1841年英國占領香港島時,英國政府即宣布該地的香港居民7450人為英國臣民,這也成為近代以來第一次中國人民因不平等條約而發生國籍身份變更的事例。
就清政府的實際統治與管轄區域而言,近代國籍問題最先集中出現于五口通商開放時期的英籍華人群體,其中以廈門最為突出。這些來自英屬海峽殖民地、享有條約特權的英籍華人,大部分是明清之際或是新加坡開埠以后移民東南亞的華僑后裔,無論外貌、衣冠服飾,還是語言、生活習慣,都與原鄉民人沒有太大差異。當他們在通商口岸開放初期回到中國時,其中一些人善于利用“雙重”身份的優勢,游走于清政府和殖民地政府管轄的中間地帶。每每與當地官民發生摩擦、糾紛時,他們便以外國人身份為護身符,利用領事裁判權加以干涉,此種情況,積弊日久,嚴重破壞清政府的司法制度和地方秩序的安定。而英國領事與當地政府官員圍繞有關英籍華人的身份問題的爭議,也極易引起外交糾紛與沖突。1851年發生在廈門的陳慶真案,便是清朝地方官員初次處理國籍問題的重要案例。而因陳慶真之死引發的這場中英外交風波,雙方辯論的焦點則集中在中英兩國官員對待國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上。陳慶真案中,在蘇理文、文翰等英人關于國籍法律的普通法認知里,按照英國以出生地主義為主、血統主義為輔的標準,凡是在英國本土及其屬地出生者,自然即為英國屬民;但是在張熙宇、徐廣縉等清政府地方官員的知識系統中,國籍還是完全陌生的概念與法律制度,自然難以理解英領事解釋的屬人管轄權等相關國籍原則與觀念。雙方在國籍概念認識上的分歧,造成了陳慶真案處理及交涉過程中不同法律制度間的矛盾與沖突。關于此類英籍華人的國籍歸屬問題,中英雙方雖最終未能達成共識,清政府地方官員卻在與英領事的辯論中,激發了對國人身份歸屬即國籍問題的認知與思考。他們對衣冠服制作為分辨標準和立場的堅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統主義國籍觀念的初步萌芽。而此一時期清政府官員在面對此類華洋交涉引發的國籍問題的處理方式和態度,也為日后國籍問題交涉中的“出生地主義”與“血統主義”之爭埋下伏筆。
國籍知識的早期引介與實踐
鴉片戰爭后,伴隨西方各國堅船利炮而來的不僅僅是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以及條約體系下圍繞中英雙方對外籍華人身份的各種爭端,國際法知識也開始傳入中國,其中美國在華傳教的丁韙良翻譯出版的一系列國際法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有關國籍的概念和制度知識。丁韙良譯作《萬國公法》是19世紀晚清中國首次系統接觸國際法的重要譯著。在該書中,丁韙良對國際法的三個基本原則,即尊重各國主權、國與國之間平等往來以及遵守國際公約和雙邊條約的相關理論進行了介紹。繼《萬國公法》后,丁韙良和他的同文館學生相繼又翻譯了多部國際法著作。就國籍相關概念與制度而言,《星軺指掌》詳細介紹了外國人加入美國籍后所具有的外交保護等權利以及相關義務。《公法便覽》向國人輸入了人民有自由遷徙,寓居他國之人有入籍、復籍的權利與規范等國籍方面的知識與觀念。
通過《萬國公法》等國際法著作在晚清中國的譯介和流傳,國籍相關的國家主權、平等、權利、僑民保護、自由遷徙等法律知識和觀念逐漸為國人所了解和接受,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國籍觀念在晚清中國的萌生、發展和傳播。1879年閩浙總督何璟在處理廈門當地的英籍華人國籍身份爭議時,已經能夠援用《萬國公法》中有關國籍法律知識,與英國領事進行針鋒相對的談判。在19世紀80年代中荷關于華僑國籍歸屬問題的交涉中,駐德荷公使許景澄利用國際法知識與荷蘭外交部據理力爭,不僅取得了外交上的初步勝利,還基本確定了清政府對華僑國籍的基本原則,即原始國籍的血統主義原則、繼有國籍的妻從夫籍原則和有限出籍原則。這三大原則奠定了20世紀初《大清國籍條例》的主要內容。
此外,在條約體系的建立過程中,國際法知識的傳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清政府遵從國際慣例,廢除海禁政策,進而確認了華人移民的合法性。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華工出洋始得以允許,但為“保全”華工,限以“華民情甘出口”為條件,且在外華人仍不準回國。隨后其他條約也有類似規定,特別是1868年《蒲安臣條約》以法律形式確立了近代國際法意義上國籍申請、保護僑民的基本原則,顯示出清政府初步的國籍法意識。
除了華工出洋合法化之外,在郭嵩燾、張之洞、薛福成等大臣的吁請下,清政府對海外華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對其經濟力量的重視程度不斷加深。自1876年起,清政府在海外陸續設立公使館和領事館,為保護華商和華工提供了制度保障。1893年,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根據對南洋華僑的實地調查,上書駐英公使薛福成,主張解除禁令。在黃遵憲上書的基礎上,薛福成正式奏請清政府廢除出洋華人不準回國之禁例,請求朝廷嚴議保護出洋華民良法。至此,清政府正式廢除海禁,確立了允許海外移民的法律制度。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用以指稱移民海外的中國僑民或華人僑寓者的“華僑”一詞,逐漸在官方和民間流行,并在20世紀初的政治風云中得到廣泛使用,進一步凸顯和固化了其所附麗的政治意涵。
清政府的國籍立法實踐
清政府自1893年正式立法護僑之后,有兩個方面的發展愈來愈引起統治者的關注。一方面,隨著海外移民人數的增加,加入所在國國籍的趨勢也逐漸凸顯。當這些外籍華人以領事裁判權回到祖籍地與當地民人發生各種糾紛時,處理華洋交涉時的國籍問題令各地方官員和各國領事牽扯了大量精力。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那些并未遠赴海外寓居、始終居住在清政府統治管轄范圍內的民人,發現具有外國籍便可以獲得逃債、逃捕等種種切實好處后,亦紛紛尋找各種途徑取得外國國籍,此即所謂“改籍”問題。甲午戰爭以后國內華人改籍現象開始明顯,至20世紀初已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并且與邊疆危機連在一起。此外,遍布東南亞、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契約華工等海外移民,他們因長期遭受僑居國的不公平對待,迫切希望得到祖籍國政府的承認和保護。凡此種種,都使得清政府需要重視國際法、各國移民條例、國籍法律等相關知識,并反省自身法律規范方面的缺失。
1899年日本新頒布《國籍法》不久,即有旅日華人向日本方面提出入籍申請。1906年,又有長崎華商提出歸化申請,長崎縣知事向清政府駐長崎領事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詢問。為徹底解決此類海外華人入籍問題,駐日公使楊樞向外務部提出制定華人改入外國籍辦法的建議。而在此一個多星期前,清政府外務部已經就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有關國籍規定等問題的詢問,致函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進行相關咨詢。柔克義向清政府外務部提出6個非常具體的有關國籍法的問題,除了涉及國籍的取得、喪失和恢復方面的內容外,還特別提出對華僑權利的保護、來華外國人入籍等需要清政府解決的新問題。
此時剛剛履新大理院正卿的修律大臣沈家本對制定國籍條例基本持肯定態度,且采取他一貫的修律風格,即從組織人員調查外國法律開始,徐徐圖之,不能操之過急。然而這時清政府對待國籍立法的態度卻有了實質性的變化。1907年中荷設領談判,荷方強硬地將設領和華僑國籍問題捆綁在一起,這一突發事件成為推動清政府國籍立法的催化劑。
1908年駐法公使劉式訓上奏光緒皇帝,再次重申國籍立法的重要性。這份奏折是代表晚清國籍觀念成熟、推動國籍立法進程的關鍵性文件。劉式訓在奏折中闡述了國籍與籍貫的區別,國籍重要性的四個方面,即關乎主權、關乎現行條約、關乎海外華僑的政治地位、關乎國民的權利與義務,并提出本國人入外國籍的程序及規范。尤其重要的是,他特別提醒清政府注意荷蘭擬根據屬地主義原則改變殖民地華僑身份,并以此為清政府在荷屬東印度設領設置障礙,這也為不久后荷蘭新訂殖民地入籍新律引起當地華僑強烈反彈埋下了伏筆。
在荷屬各界華僑、各地封疆大吏、海內外社會輿論的共同請愿和期待中,修訂法律館終于在1909年3月5日完成《國籍條例草案》的草擬工作。外務部在該草案基礎上于3月9日正式形成《國籍條例草案》5章25條,明確提出國籍立法采折中主義的偏血統主義原則,即以血統主義為主、出生地為輔,并參照各省歷年交涉情形,擬定《施行細則》11條。《國籍條例草案》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即進入“憲政中樞”憲政編查館的審定復核程序。最后經憲政編查館核議的《大清國籍條例》共分固有籍、入籍、出籍、復籍和附條5章24條,并附《施行細則》10條,于3月28日頒行。與《國籍條例草案》相比,《大清國籍條例》文字上更加精煉、嚴謹,內容上對外國入籍者、本國復籍者擔任政府官職的條件、職務、范圍以及入籍者、出籍者的資格條件作了更為完整、明確、嚴格的限制,進一步強化了清政府的國籍立法意圖和原則。
縱觀《大清國籍條例》從醞釀、動議、制定到出臺的歷史過程,由于國籍問題本身的復雜性,駐外使節、封疆大吏、清政府各中央機構、荷屬各埠華僑組織及國內商會多種力量參與其中,形成合力,最終促成清政府統治者在國籍立法思路上逐漸從明確海外華人自愿改籍、嚴格限制國內民人擅自改籍以及確定海外華僑的合法身份三個層面達成共識,推動了政府層面國籍觀念的成熟。此外,來自社會輿論的力量也值得重視,除有人從國家主權、民族平等、維護國家司法主權完整等層面強調國籍法的重要意義外,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一批知識分子,積極著文立說,普及國際法和國籍法律知識,從學理上探討國籍問題的解決方案,在譯介日本國際法學者方面尤其不遺余力,均可視為晚清中國社會精英國籍意識高漲的一個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