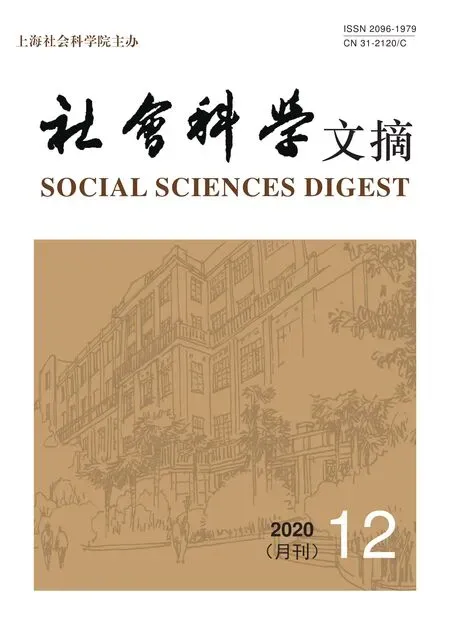免疫、自啟免疫與自啟免疫共同體:文學(xué)理論與跨學(xué)科的隱喻
文/程朝翔
引言:當(dāng)代文學(xué)理論的跨學(xué)科性
在21世紀(jì),主導(dǎo)西方文學(xué)的仍是理論。理論已成為創(chuàng)造性寫作的一個新的體裁,可以和舊的體裁平起平坐,而且表現(xiàn)出更大的活力和韌性。同時,理論是跨學(xué)科的,涵蓋了人文社科的各個領(lǐng)域,而且越來越走向自然科學(xué)。
文學(xué)理論和文學(xué)研究走向自然科學(xué)的一個例子來自斯提芬·格林布拉特。他將《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jì)》的亞當(dāng)和夏娃敘事作為文學(xué)來進行研究,并將其置于自然科學(xué)的框架之內(nèi):古人類學(xué)和古生物學(xué)的正模標(biāo)本是確認和命名一個物種的根據(jù),也是整個物種的實體例證和代表。古人類或者古生物的標(biāo)本一旦被某一科學(xué)家確認為正模標(biāo)本并被科學(xué)社區(qū)所認可,這一科學(xué)家就成為一個物種的“作者”。
上帝像科學(xué)家一樣,是很多正模標(biāo)本的作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類的正模標(biāo)本——亞當(dāng)和夏娃。亞當(dāng)和夏娃也是最早的人類,即人類這一物種的化石。這在科學(xué)上也能找到類似物,即被命名為露西的化石,她是大約生活在32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種的一位女性,也是人類最老的祖先之一。因此,研究亞當(dāng)和夏娃不僅是研究人類這一物種的代表,也是研究最早的人類。
當(dāng)代進化生物學(xué)有一觀點認為,動物的進化并非直線式的,而是枝杈繁雜。猿不僅進化成人,而且由另一枝演變?yōu)楹谛尚伞:谛尚墒侨祟惖慕H,同時也最接近于人類的原始狀態(tài),即在天堂的狀態(tài)。以黑猩猩為參照,可以更好地理解人類的發(fā)展。
黑猩猩社區(qū)和人類社會一樣,有所謂“文化”。黑猩猩的生活環(huán)境,即原始森林,與《圣經(jīng)》的“天堂”相似,因此它們依然像亞當(dāng)和夏娃一樣,不知善惡,不知羞恥;人類則被趕出了天堂即原始森林,面臨著嚴(yán)酷、荒蕪的環(huán)境,因此沿著另一條道路進化至今。人類不可能再選擇回到天堂、森林、黑猩猩的狀態(tài),因為人類已有知識。亞當(dāng)和夏娃在天堂是有選擇權(quán)的,他們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的未來,也決定了人類的進化方向。選擇決定一切,選擇不僅決定了物種個體的未來,也決定了整個物種的未來。我們當(dāng)下的選擇,將會決定我們和我們子孫的未來。
免疫和自啟免疫:生命政治學(xué)的重要概念
此類研究受到福柯“生命政治學(xué)”的影響。在福柯之后,“似乎很少能有一個領(lǐng)域不受生命政治的影響”。在該領(lǐng)域的理論中,免疫是一個重要話題。
理論中的免疫和自啟免疫是比喻,或者更具體地說,是隱喻;文學(xué)理論借助隱喻與其他諸多學(xué)科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這也是文學(xué)在當(dāng)下獲得社會性的重要途徑。理論敘事中的免疫和自啟免疫是所謂“比喻的比喻”:“免疫”一詞最初來自法律、社會、宗教、政治等領(lǐng)域,后被自然科學(xué)所借用,然后又被借用回人文社科領(lǐng)域,因此它是“比喻的比喻”。這個詞最早的意思是享受特權(quán),不受法律和規(guī)則的制約,成為法律和規(guī)則的例外。
在現(xiàn)代的人體免疫的意義出現(xiàn)之前,這個詞在醫(yī)學(xué)中的意思就是“免疫”,而非防疫和抗疫。該詞當(dāng)時的“醫(yī)學(xué)意義”與法律和政治意義完全一致,指的是不受疾病侵襲的特殊赦免,也就是天賜的或者天賦的免疫。這一意義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代生物“免疫系統(tǒng)”的發(fā)現(xiàn)。
當(dāng)現(xiàn)代科學(xué)發(fā)展出現(xiàn)代免疫學(xué)時,這一概念經(jīng)歷了范式的轉(zhuǎn)移,獲得了今天的意義。免疫成為“防疫”或者“抗疫”——人體的免疫系統(tǒng)并不能“免”于細菌和病毒的攻擊,而是隨時戒備,不斷防御,抵抗外敵。因此,人體的“免疫系統(tǒng)”其實是“防疫”或者“抗疫”系統(tǒng)。但英文中的免疫一詞仍被保留,中文也沿用至今。
通過實驗,俄國科學(xué)家梅契尼柯夫使這一概念發(fā)生了從哲學(xué)到科學(xué)、從隱喻到理論的轉(zhuǎn)變。他把透明的海星幼蟲放進試管,然后將含有幾粒深紅色粉末的水滴注入試管。在顯微鏡下,透明的幼蟲體內(nèi)的活動細胞吞噬深紅粉末,隨之自己也變成深紅色。這不是簡單的進食,而是細胞在吞噬和消滅入侵者。這是生物免疫的重要過程,即吞噬細胞工作的過程。
此前,雖有“抗擊疾病的戰(zhàn)爭”的說法,但這完全是“隱喻”,因為人類尚未在醫(yī)學(xué)上證明人體會對疾病發(fā)動戰(zhàn)爭。而梅契尼柯夫?qū)⑵渥C實,使隱喻變?yōu)榭茖W(xué)。
現(xiàn)代的人體:現(xiàn)代免疫學(xué)理論的建構(gòu)產(chǎn)物
隱喻既然是用一個領(lǐng)域中的概念來替代或者“再現(xiàn)”另一個領(lǐng)域中的概念,那就會在兩個領(lǐng)域之間建立聯(lián)系。“免疫”與“抗疫”將醫(yī)學(xué)、生物學(xué)與政治、法律、宗教聯(lián)系起來。借助隱喻,免疫學(xué)使人體成為“現(xiàn)代人體”,并將其納入現(xiàn)代性的系統(tǒng)。
所謂現(xiàn)代和現(xiàn)代性,始于歐洲文藝復(fù)興,或稱早期現(xiàn)代。從那時起,人逐漸在思想上得到解放,擁有自我和自我意識。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意識的“現(xiàn)代化”早于科學(xué)對于“現(xiàn)代人體”的發(fā)現(xiàn)。沒有思想的解放和意識的現(xiàn)代化,就不可能有科學(xué)上的進步和發(fā)展。同時,科學(xué)使用現(xiàn)代“隱喻”不斷構(gòu)建現(xiàn)代科學(xué)理論的過程與思想和意識的現(xiàn)代化同步,先于相關(guān)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而相關(guān)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反過來又推動人文社科的發(fā)展,雖然這種推動有時是在科學(xué)研究的成果相當(dāng)成熟之后。
在早期現(xiàn)代,人的自我塑造已具有現(xiàn)代性。自我擁有主權(quán),與外界界限分明,為保衛(wèi)自己的疆界而與外界爭斗。
現(xiàn)代的人體如同現(xiàn)代的自我,“我”與“他”之間界限分明,靠免疫系統(tǒng)來抵御外界的侵犯。一旦有外界抗原(例如病毒)侵入,免疫系統(tǒng)就會被觸發(fā),阻止病毒的復(fù)制,因而殺死病毒。但過分反應(yīng)也能與病毒感染一起引起或加重某些癥狀。這些癥狀如果嚴(yán)重就會造成感染性休克,甚至導(dǎo)致器官的衰竭,造成死亡。免疫系統(tǒng)因此面臨兩難之境:行動過緩就會導(dǎo)致病毒猖獗,而行動過猛則會誤傷人體——兩者都能使人體受到重創(chuàng),甚至喪失生命。
現(xiàn)代的自我也是如此,對于自己領(lǐng)地的守護和對于外界的抗擊過分激烈,也會毀滅自己。因此,最有自我的人物往往是邪惡的人物。他們過于自信,極力維護膨脹的自我,同時也侵犯外界,破壞生態(tài),傷及自己,自取滅亡。他們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不相信命運和運氣——他們也不會相信“赦免”。對于邊界過于分明的自我而言,愛、欲望、邪惡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西方的“自我”有邊界又有行動能力和動機,與其他的自我相對立。它與其他文化的自我并不相同,與現(xiàn)代之前的自我也并不相同。現(xiàn)代的人體與現(xiàn)代的自我非常相似。
在現(xiàn)代之前,這種自我和人體并不存在。在古希臘悲劇中,俄狄浦斯在阿波羅神諭宣示了他的命運之后,他的自我就已經(jīng)命中注定,任何塑造自我的企圖都是徒勞的。他弒父娶母的詛咒就像惡性病毒一樣,不能免疫,無可豁免。所謂“命運”也許就是自然秩序。人皆有命,每個人在大自然的秩序里都有自己的位置:有的無疾而終,“豁免于”疾患;有的罹患疾病,不治而終;有的雖有病痛,但可以恢復(fù)自然秩序,逐漸療愈。療愈就是人體自然而然地擺脫疾病,恢復(fù)健康,雖然其間也不排除醫(yī)學(xué)和非醫(yī)學(xué)的協(xié)助。
療愈是現(xiàn)代之前的醫(yī)學(xué)觀念。根據(jù)這一觀念,大自然對所有有機體都有療愈的力量。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會被打破,生出疾病。而療愈,則是要恢復(fù)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這種觀念在現(xiàn)代免疫學(xué)誕生之后就在西方壽終正寢。
自啟免疫共同體:免疫系統(tǒng)理論建構(gòu)下的人類社區(qū)理論
在西方的現(xiàn)代免疫體系里,人體識別自我,確立自我的邊界,抗御外部的入侵。外部的入侵者即抗原,包括病毒、細菌等。抗原的入侵觸發(fā)了免疫系統(tǒng),啟動了免疫細胞,即淋巴細胞(白血球),亦即抗體。
人體的免疫系統(tǒng)與人類的社區(qū)/共同體極為相似,可互為參照。人類社區(qū)也需要確定自身邊界,劃清本社區(qū)與其他社區(qū)的關(guān)系。不同社區(qū)之間會有矛盾沖突,甚至?xí)袘?zhàn)爭。社區(qū)需要防御和自衛(wèi),因此首先需要劃清敵我,這也是免疫的關(guān)鍵。
免疫力和防衛(wèi)能力可以后天獲得。為抵抗病毒,可將可控的、不致命的病毒注入人體,使人體受到感染,發(fā)展出后天的免疫力,這就是疫苗接種。在人類社會,抵御外部威脅的一個辦法就是主動將外部的部分威脅納入自己的社區(qū),將其中和。如果將威脅納入社區(qū)也無法將其中和,那至少也會有助于在自我、非我、他者等之間進行辨析,“敵人必須被辨認出來才能被打敗”。疫苗接種的原理也是如此:將弱化的病毒注入人體,人體的免疫系統(tǒng)就會將其辨認出來并且記住。一旦人體再次遭受病毒的攻擊,免疫系統(tǒng)就會第一時間辨認出已經(jīng)儲存在記憶中的病毒,并毫無延遲地啟動免疫細胞,對其進攻,將其殺死。
對于初次感染的病毒,人體的免疫系統(tǒng)需要花費較長時間來進行辨認,然后防御。如果遇到新冠病毒一類毒性較強而又十分狡猾的病毒,人體免疫系統(tǒng)就顯得反應(yīng)遲鈍。同時,為了迅速消滅病毒,人體免疫系統(tǒng)也會過度反應(yīng),引起大量炎癥和其他病理反應(yīng),最終甚至?xí)斐伤劳觥R虼耍磻?yīng)遲鈍、調(diào)動不足和過激反應(yīng)、調(diào)動過度都會造成嚴(yán)重后果。當(dāng)社區(qū)面臨外部入侵和內(nèi)部威脅時,反應(yīng)不足和反應(yīng)過度也會造成同樣后果。
有的哺乳動物發(fā)展出了高效的免疫系統(tǒng)——不過分反應(yīng),也是高效的標(biāo)志之一。新冠病毒的宿主蝙蝠是唯一會飛的哺乳動物,它可以長期受到病毒感染而不發(fā)病。它的免疫系統(tǒng)顯然也足以控制毒性巨大的病毒,即復(fù)制速度極快的病毒,從而使自身免于被病毒摧毀。社區(qū)可能也需要像蝙蝠一樣,既能控制威脅,又不至于因控制過度而毀滅自己。在這個意義上,蝙蝠是一個重要的隱喻。
在人體免疫系統(tǒng)的過度反應(yīng)中,自啟免疫十分獨特,因為它是在沒有外界抗原即外界入侵的情況下,免疫系統(tǒng)的自動觸發(fā)。所謂“自啟免疫”,以往的中譯名為“自身免疫”。然而,所有的免疫其實都是“自身免疫”,只是大部分免疫是由外界抗原所觸發(fā)的,而自啟免疫是在并無外界抗原的情況下自動觸發(fā)的。因此,本文將其譯為“自啟免疫”。大約在20世紀(jì)50年代,科學(xué)家發(fā)現(xiàn)了自啟免疫,但科學(xué)界一度難以接受自啟免疫理論,因為其核心就是人體可以自己攻擊自己,這說明人體有自殺性。目前已知有多種自啟免疫疾病。
自啟免疫類似于人類社會的內(nèi)戰(zhàn)、內(nèi)亂、內(nèi)斗等。免疫系統(tǒng)將自我識別成敵人或入侵者,并攻擊自身的某一器官或整個系統(tǒng),引發(fā)疾病,其中包括致命疾病。在自啟免疫中,自我、自衛(wèi)、自我防御的觀念受到顛覆。在免疫中,核心是自我;而在自啟免疫中,自我將自我識別為敵人或者他者,自我已經(jīng)變成敵人或者他者,自我與敵人或者他者的界限被打破。
在“911事件”之后,德里達特別強調(diào)自啟免疫的自殺性質(zhì)。“恐怖襲擊就是自啟免疫疾病的癥狀,而自啟免疫疾病威脅著西方參與式民主的生命,威脅著支撐這一民主制度的法律體系。”他還強調(diào),“911事件”并非自啟免疫疾病的第一個癥狀,而只是最新癥狀。美國的恐怖分子都是“自己人”,來自美國內(nèi)部,或者是美國在冷戰(zhàn)期間在世界各地培植的代理人。他們最終成為攻擊美國自己的暴力恐怖分子。恐怖分子與病毒高度類似:他們沒有武器,但劫持了美國的武器和飛機,就像病毒劫持了人體細胞一樣,利用人體細胞的能量和蛋白質(zhì)來大量復(fù)制自己,從而殺死細胞并最終殺死自己。
自啟免疫與免疫的區(qū)別在于自我邊界的打破。在恐怖襲擊中,沒有國界的概念,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對于另一個民族國家的攻擊,而是國際恐怖分子超越國界和國籍的攻擊。這也類似于病毒,沒有國界、國籍和地域界限。恐怖襲擊和病毒蔓延一樣,都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攻擊。
自啟免疫顛覆了自我的邊界。在自我概念中,邊界這一關(guān)鍵詞劃出了自我與他者的區(qū)別:自我需要防御,以防他者的侵犯。而現(xiàn)在,“自我的邊界上有潛在的很危險的沖突,而自我就是由這些沖突所構(gòu)成、所界定”。邊界沖突,即對于邊界的突破,成為自我與他者沖突的場所,但也成為自我之所以成為自我的原因:沒有他者,沒有與他者的沖突,就沒有自我。如果他者不復(fù)存在,自我也就隨之消亡。這也就構(gòu)成了另一種可能性:自啟免疫雖然是自殺性的,但又不能沒有,因為這種沖突使自我得以存在。
根據(jù)自啟免疫的邏輯,這甚至不是也不需要邊界沖突,而是主動破除邊界:“為了保護自我的生命,為了構(gòu)建獨一無二的活生生的自我,為了構(gòu)建自我與自我的關(guān)系,自我必然被引導(dǎo)著歡迎他者進入自我內(nèi)部……免疫防御本來是為非我、敵人、對立面、對手準(zhǔn)備的;自我將它拿來,使它在保衛(wèi)自我的同時又抵御自我。”
自啟免疫既是自殺性的,但同時也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它意味著開放,向他者開放,開辟了各種可能性——“通向未來,也通向自我轉(zhuǎn)變”:“在于自我,也在于他者,在于自我之中的他者。”通過自啟免疫,自我認識了他者,接納和容納了他者,使他者成為自我的一部分,使自我成為他者的住所。自我將自我識別為他者,說明他者寓于自我,自我也可以轉(zhuǎn)化為他者。
那么什么是他者?不僅是抗原、病毒、異體,而且是一切“不是自我、大于自我的東西:他者、未來、死亡、自由、他者的到來和對于他者的愛”。他者無所不在,是一切非我和未知之物。空間意義上的邊界已經(jīng)消除,人和人體在時間上與他者連續(xù)不斷地進行交往和交流。
生命層面上的自啟免疫體就是社會層面上的“自啟免疫共同體”。德里達將幾個相關(guān)的詞拆分,將拆出的成分又組成一個新詞,即自啟免疫共同體(auto-coimmunity):一方面,是“作為自啟免疫共同體的社區(qū)(社區(qū)的共同點是共同擁有免疫的責(zé)任或擔(dān)當(dāng))”,另一方面,是“人類的自啟免疫共同體,特別是自啟免疫的人道主義”。前者強調(diào)單個社區(qū)的免疫責(zé)任,即自我防御的責(zé)任;后者強調(diào)人類命運共同體感知和容納“他者”的博大的人道主義。
結(jié)語: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xué)的話語互參
自然科學(xué)和人文社科使用不同的話語和解釋范式。自然科學(xué)有時借用人文社科的話語來描述和命名自己的發(fā)現(xiàn),而人文社科也會借用自然科學(xué)術(shù)語來描述社會現(xiàn)象。當(dāng)然,跨學(xué)科的描述可能不夠準(zhǔn)確,甚至有錯誤。然而,這種“誤讀”有時反而是不同學(xué)科溝通的基礎(chǔ),甚至?xí)l(fā)跨學(xué)科的范式轉(zhuǎn)移。
通過對免疫和自啟免疫理論的“誤讀”,人文社科學(xué)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了“生命政治學(xué)”思考。而對于“現(xiàn)代人體”的反思也許會促使醫(yī)學(xué)研究更關(guān)注現(xiàn)代科學(xué)基礎(chǔ)上的“療愈”,即不僅是“戰(zhàn)勝”病毒和疾病,也關(guān)注如何讓人體更適應(yīng)外部世界,與病毒和疾病和平相處。
人類需要尊重“他者”,包括自然,甚至包括無生命的病毒,使這些他者與自我和平共處,甚至變?yōu)樽晕业囊徊糠郑蝗祟愐矐?yīng)該善待作為他者的自我,不讓自我因為懼怕他者而成為自我都無法辨認的他者。人類命運共同體應(yīng)該是自我之中有他者,他者之中有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