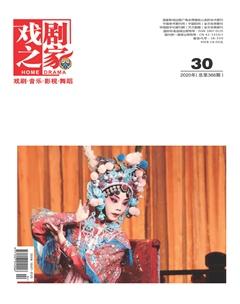德彪西舞蹈交響詩《游戲》及相關(guān)研究
唐大林
【摘 要】本文對舞蹈交響詩《游戲》的創(chuàng)作背景、創(chuàng)作歷程以及表現(xiàn)內(nèi)容進(jìn)行梳理,分析《游戲》相關(guān)研究成果并闡述諸多作曲家對該作的高度評價,以此說明其歷史地位與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芭蕾舞劇;德彪西;游戲;創(chuàng)作歷程
中圖分類號:J705?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20)30-0086-02
德彪西一生創(chuàng)作了不少杰作,也對西方音樂史的發(fā)展方向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眾所周知,其創(chuàng)作主要集中于鋼琴曲與管弦樂曲兩方面,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歌劇與芭蕾舞劇音樂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同時,對古典與浪漫主義時期管弦樂中具有很高地位的交響曲卻從未涉足,這是由于德彪西個人認(rèn)為貝多芬已將交響曲這一形式發(fā)展到教科書式的完美典范。
德彪西共創(chuàng)作有六部芭蕾舞劇音樂,均為生命的最后幾年所創(chuàng)作,說明芭蕾舞劇這一形式在其創(chuàng)作晚期中占據(jù)比較重要的地位。這六部芭蕾舞劇分別為由莫德·艾倫委托創(chuàng)作《卡瑪》(1911-1912)、受賈吉列夫委托為俄國芭蕾舞團(tuán)而作的舞蹈交響詩——《游戲》(1912-1913)、采用安德烈·海勒的腳本創(chuàng)作的兒童芭蕾舞劇——《玩具箱》(1913),此外還有一部“歌劇——芭蕾舞劇”(1912-1915)以及兩部未完成的芭蕾舞劇音樂。同時,其多部管弦樂作品(如《牧神午后前奏曲》《夜曲》等)被改編成舞蹈音樂由俄國芭蕾舞團(tuán)上演。
一、《游戲》及其相關(guān)內(nèi)容梳理
“芭蕾”一詞由法語“ballet”音譯而來,意為“跳”或“跳舞”,它是發(fā)源于文藝復(fù)興時期意大利的一種古典舞蹈,十七、十八世紀(jì)由法國宮廷中發(fā)展流行起來并逐步職業(yè)化,到十九世紀(jì)末二十世紀(jì)初,由俄羅斯舞蹈團(tuán)發(fā)展至極盛。而芭蕾舞劇則是指以芭蕾為主要表現(xiàn)手段,結(jié)合音樂、舞臺美術(shù)、服裝、文學(xué)等于一體,用以表現(xiàn)某個故事情節(jié)的一種戲劇性綜合藝術(shù)。
在當(dāng)時的法國,芭蕾舞劇不僅是路易王朝時代的宮廷舞蹈,同時也比歌劇更受歡迎。舞劇在法國上流社會一直扮演著一種比歌劇更為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被視為國家傳統(tǒng)的象征。在法國一部歌劇要想獲得成功、贏得觀眾的認(rèn)可,必須要有大段的舞蹈來支撐,而芭蕾舞蹈演員則在其中扮演了相當(dāng)重要的角色。自1909年起,俄國芭蕾舞團(tuán)嘗試將俄國的舞蹈音樂藝術(shù)介紹到整個歐洲,并在法國上演了改編自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管弦樂組曲《天方夜譚》、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鳥》《彼得魯什卡》以及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等作品,而法國社會在聽?wèi)T了枯燥無味的舊式芭蕾舞劇之后,開始狂熱地追捧這一編劇、舞美、服裝、動作以及音樂均為全新形式的舞劇。因此,這一時代的芭蕾舞劇廣受作曲家、舞臺藝術(shù)家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強(qiáng)烈關(guān)注,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芭蕾舞劇音樂。
德彪西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舞臺藝術(shù)的形式與內(nèi)容的表達(dá)以及音樂與劇本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諸多有益的探索,并表現(xiàn)為作曲技術(shù)、樂曲結(jié)構(gòu)等多方面的突破。其在談及“我為什么寫《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時寫道:“我想寫舞臺音樂已有很久了,可是我想譜寫的舞臺音樂的形式是如此不同尋常,經(jīng)過多次嘗試之后,我?guī)缀醴艞壛恕N乙郧皩円魳返难芯浚瑢?dǎo)致我憎恨習(xí)以為常的主題展開方式,因?yàn)槟欠N美完全是技術(shù)性的,只有我們階層的文化人才感興趣。我希望音樂擁有也許比其他任何藝術(shù)更多的自由,不是局限于或多或少準(zhǔn)確地再現(xiàn)大自然,而是要讓大自然與想象力相互溝通。”[1]關(guān)于《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創(chuàng)作中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他認(rèn)為自己開辟了一條可以讓其他人遵循的新道路,而這一路徑使長期墨守成規(guī)的戲劇音樂解脫開來。
在舞蹈交響詩《游戲》創(chuàng)作之時,德彪西已經(jīng)完成歌劇《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管弦樂《牧神午后前奏曲》《大海》《意象集》以及舞劇音樂《卡瑪》等風(fēng)格獨(dú)特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并且這首作品創(chuàng)作于德彪西最后幾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因此可以說《游戲》這部作品是德彪西成熟時期的一部杰作。
德彪西的舞蹈交響詩《游戲》于1912年受賈吉列夫之邀,為1909年前后組建的俄國舞劇團(tuán)而作,由該團(tuán)首席男舞蹈家尼金斯基編劇與編舞。德彪西于1912年6月與賈吉列夫聯(lián)系并著手寫作,三個月后即完成舞蹈交響詩《游戲》的鋼琴版,并由法國樂評家、管風(fēng)琴家、作曲家、樂譜出版商瑪麗·奧古斯特·杜蘭德創(chuàng)立的杜蘭德樂譜出版公司(巴黎)于同年首次出版。德彪西接受賈吉列夫的建議,重新改寫結(jié)尾并數(shù)次修改總譜。從1912年9月開始動筆直至1913年4月底管弦樂版本才最終定稿。1913年5月15日,舞劇《游戲》由俄國舞劇團(tuán)(尼金斯基、卡爾沙維娜、柳德米拉·肖拉爾舞蹈,彼埃爾·蒙圖指揮)首演于巴黎香榭麗舍劇院。德彪西的舞劇音樂《游戲》題獻(xiàn)給杜蘭德夫人,《游戲》的總譜(管弦樂譜)于1913年11月由杜蘭德出版公司首次出版,而后由該公司于1914、1947、1988、1998年等多次再版。此外,由作曲家萊奧·洛克斯改編的四手聯(lián)彈版本也由杜蘭德出版公司于1914年首次出版。
芭蕾舞劇《游戲》的編劇與編舞尼金斯基從高更的繪畫中汲取靈感,以抽象造型藝術(shù)的形式設(shè)計出機(jī)械化的舞蹈動作,加上現(xiàn)代化的背景與服裝,使這部作品不同于往日的任何一部芭蕾舞劇。尼金斯基設(shè)計的《游戲》劇本是一個僅3人出場的獨(dú)幕芭蕾舞劇,以啞劇的形態(tài)進(jìn)行表演。故事情節(jié)描寫在黃昏的公園里,不知從哪個角落滾來一個網(wǎng)球,一男兩女三位舞者在找球之時互相追逐、互相迷失、互相爭吵,陷入戀愛的游戲。先采用全音音階構(gòu)成的和弦表現(xiàn)黃昏的靜寂之美,接著網(wǎng)球出現(xiàn),然后手執(zhí)球拍的男舞者上場,表演精彩的舞蹈,退場后兩名女舞者接著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上場。她們在跳舞之時,而男舞者正從樹叢后窺視這兩位姑娘,他碰到樹葉時沙沙作響。之后他說服其中一位姑娘與他跳舞,另一位姑娘則跳起了嘲諷般的舞蹈。男舞者走向心生嫉妒的第二位姑娘,要教她跳圓舞曲。此時,第一位姑娘準(zhǔn)備離去,卻被第二位姑娘阻止。于是三個人經(jīng)歷賭氣、爭吵而后擁抱在一起跳起舞來,共同陶醉在愛情的甜蜜之中。突然,又不知從哪兒飛來一個網(wǎng)球,正好落在他們腳邊,打斷了這種甜蜜的氛圍。三個人都受到了驚嚇,然后各自匆匆離開,紛紛消失在昏暗的公園深處。
《游戲》的標(biāo)題內(nèi)涵既指網(wǎng)球的游戲,又指年輕人與兩個女孩之間糾纏不清的愛情游戲。在《游戲》這部作品中,德彪西以非傳統(tǒng)的、游離的、不確定的調(diào)性,非均衡性、非對稱性的節(jié)奏、節(jié)拍,非規(guī)整型的樂句(或樂段)長度,平行的和弦、開放的結(jié)構(gòu)、精致而獨(dú)特的音色構(gòu)成等音樂手法賦予其時間的運(yùn)動與音樂的流動性。
二、德彪西《游戲》相關(guān)研究述評
目前國內(nèi)外對德彪西舞蹈交響詩《游戲》的研究多限于從史學(xué)、音樂學(xué)等角度進(jìn)行描述性介紹,并且大多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根據(jù)筆者所掌握的中英文參考文獻(xiàn),主要有以下幾部(篇)著作對《游戲》的研究較為深入并具有較高的學(xué)術(shù)性。
《<游戲>作曲進(jìn)程中音色的確立》(Myriam Chimènes,“The definition of timbre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of JEUX”)主要通過三方面來對《游戲》進(jìn)行闡述,其一為從史學(xué)的角度對作品的創(chuàng)作及其首演之后的評價與影響做一概述,其二為手稿版本比較研究,其三論述德彪西在《游戲》中管弦樂隊的布局與創(chuàng)作手法。該文在論述《游戲》的音色手法時借用了皮爾·布列茲對有關(guān)作曲現(xiàn)象總結(jié)的術(shù)語——“用一系列姿態(tài)(gestures)來表達(dá)”。
《德彪西<游戲>:時間與形式的游戲》Jann Pasler, Debussy,“Jeux”: Playing with Time and Form,該文從作曲技術(shù)理論的角度通過對“主題動機(jī)、節(jié)奏節(jié)拍、音色織體與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等方面進(jìn)行分別論述與例證說明,較為深入地闡述了《游戲》一曲的結(jié)構(gòu)形式在時間進(jìn)程中的體現(xiàn)及其相關(guān)結(jié)構(gòu)手法的運(yùn)用。
《德彪西<游戲>的形成》(Robert Orledge, The Genesis of Debussys ‘Jeux)一文從史學(xué)的角度對德彪西及其《游戲》相關(guān)的人物、事件進(jìn)行史料的整理與說明,較為直觀地展示出該曲從最初的劇本構(gòu)思到最后的舞劇演出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與創(chuàng)作觀念,對本文研究《游戲》的創(chuàng)作背景以及創(chuàng)作觀念的淵源關(guān)系產(chǎn)生了重要的作用。
《比例中的德彪西:音樂分析》(Roy Howat,“Debussy In Proportion:A musical analysis”)一書從“結(jié)構(gòu)比例的發(fā)端、早期發(fā)展、《大海》及其他印證”四個部分來闡述德彪西作品中的比例關(guān)系,并通過例證著重論述有關(guān)德彪西作品中“黃金分割比例”。
筆者發(fā)表的《德彪西<游戲>的音高結(jié)構(gòu)邏輯初探》《德彪西舞蹈交響詩<游戲>的節(jié)奏手法探究》《思維·地域·觀念——從<游戲>的創(chuàng)作觀念與技法探究德彪西藝術(shù)風(fēng)格之演變》《德彪西舞蹈交響詩<游戲>中意識流現(xiàn)象初探》等系列研究成果直接以《游戲》為研究對象,對其從創(chuàng)作觀念到創(chuàng)作手法一一進(jìn)行詳盡的分析與歸納,并且對《游戲》中相關(guān)創(chuàng)作特征的淵源關(guān)系進(jìn)行了較為細(xì)致的梳理。
此外,楊立青先生《管弦樂配器風(fēng)格的歷史演變概述》一文中有關(guān)部分對《游戲》的音色結(jié)構(gòu)與力度對位等方面進(jìn)行了相關(guān)闡述,以及《德彪西的管弦樂曲》等著作中部分章節(jié)對《游戲》一曲從史學(xué)視角與對舞蹈劇本以及音樂本體的分析這兩方面進(jìn)行了相關(guān)介紹與研究。
三、結(jié)語
對于德彪西的舞蹈交響詩《游戲》這部作品,歷史上諸多著名作曲家、音樂理論家對其評價相當(dāng)高。譬如在斯特拉文斯基的自傳中曾回憶德彪西在鋼琴上彈奏《游戲》縮譜時大加贊賞,他說道:“太棒了!”。而美國當(dāng)代著名音樂學(xué)家約瑟夫·克爾曼在其專著《沉思音樂——挑戰(zhàn)音樂學(xué)》中認(rèn)為:“在音樂中,現(xiàn)代主義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恰好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主要的作品如德彪西的《游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以及勛伯格的《月迷皮埃羅》。而第二階段直接出現(xiàn)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以布列茲、施托克豪森以及凱奇的創(chuàng)作為代表。”[2]此外,法國著名音樂評論家讓·巴拉凱所著的《德彪西畫傳》中談道:“總有一天,人們會認(rèn)識到德彪西最后一個創(chuàng)作時期的重要性,并且更全面地了解德彪西的音樂。事實(shí)會證明,從美感的角度看,近60年來最大的音樂成就就在以《大海》《游戲》為代表的一張紙樂譜中。”[3]
參考文獻(xiàn):
[1][法]德彪西.熱愛音樂:德彪西論音樂藝術(shù)[M].張裕禾,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42.
[2][美]約瑟夫·克爾曼.沉思音樂——挑戰(zhàn)音樂學(xué)[M].朱丹丹,湯亞汀,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4.
[3][法]讓·巴拉凱(Jean Barraqué).德彪西畫傳[M].儲圍圍,白沄,宋杭,譯.冷杉,審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