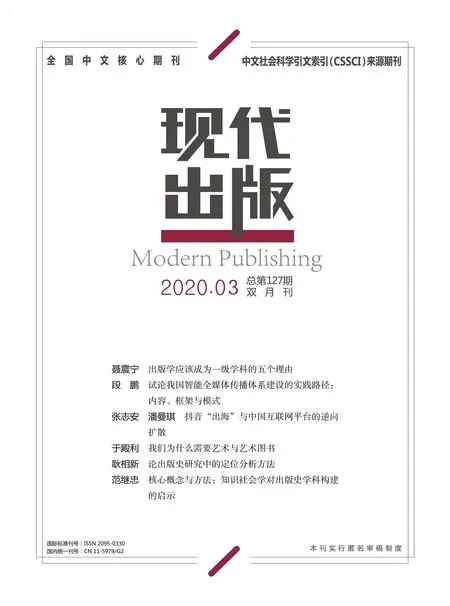從讀書到出版:張元濟早期閱讀史及其效應
◎ 王龍珺
文化史學家達恩頓十分強調閱讀在人們“想些什么”“怎么思考”“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并且注入感情”①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種通過閱讀活動探究個體思想形成過程的閱讀史研究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得到了具體應用。有學者關注到了傅蘭雅的《治心免病法》一書對譚嗣同思想的影響。②近幾年,上述閱讀史研究方法日益為出版史研究者所熟悉,相關成果體現在對王云五的研究上。③有學者通過勾連王云五個人閱讀史和他的出版活動,探究二者之間的關系,闡發其個人閱讀史的影響機制。這些研究成果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徑。
張元濟的一生始終和讀書、談書、校書、訪書、出書緊密聯系在一起。根據上述思路,考察張元濟的閱讀史對理解其出版思想和出版活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但筆者目力所及,未見有以張元濟閱讀史為研究對象的專文或專著。因此,本文不揣冒昧,以張元濟書信和日記等為基本史料,爬梳和厘清張元濟早期閱讀史④,力圖較準確地回答張元濟早期閱讀史中“在哪里讀”“讀什么”“怎么讀”等基本問題,在此基礎上探討張元濟早期閱讀史對其日后出版實踐所產生的具體效應。
一、知古而不泥古:張元濟的舊學閱讀
1892年,年僅25歲的張元濟取得進士功名。對于科舉時代的士子來說,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意味著要有極其深厚的舊學功底。張元濟出身于浙江海鹽名門望族。書香世家的文化氛圍和讀書傳統對張元濟影響極大。張元濟自小就踐行著“吾宗張氏,世業耕讀。匪學何立,匪書何習”的張家家訓。他的童年是在廣東度過的。那時候,張元濟一直跟著舅舅謝榴生讀書。回到海鹽后,又師從于秀才查濟忠和朱福詵,后者在光緒朝歷任國子監司業、翰林院傳講、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有著作傳世,可謂學問大家。濃厚的讀書氛圍、優越的家學條件使得張元濟擁有良好的舊學閱讀環境,再加上其自身的努力,張元濟對中國傳統經典讀物十分熟悉。
青年時代的張元濟除了深入接觸衡文取士所必需的舊學書目外,對其家族典籍和鄉邦文獻格外青睞。這是張元濟舊學閱讀活動的一大特點。海鹽張氏歷代世祖有不少遺著傳家,如《入告篇》《寒坪詩抄》等。同時,張家又是藏書世家,致力于藏書、刻書事業,所藏之書歷百年而未散佚。父張森玉向張元濟介紹先祖遺著和家族藏書情況,并叮囑張元濟年長之后一定要閱讀其九世祖的《入告篇》。此書是張元濟的九世祖張惟赤(號螺浮)在順治、康熙兩朝做京官時的奏牘匯編,其內容主要是對君王的諫言和對時政的批評。張元濟從廣東甫一回到海鹽,就將螺浮公的《入告篇》借來閱讀。張元濟記錄下了他的讀后感言:“開卷誦讀,乃知吾螺浮公立朝大節,有非常人所能及者。”⑤張元濟的舊學閱讀活動在進京入仕后持續進行。1896年在給汪康年的一封信中,張元濟表示“弟近讀公羊”⑥。由此可見,京官時期的張元濟繼續保持著對傳統典籍的關注。張元濟時常在與汪康年的書信中表達希望他代購書籍的請求,這些書籍大多是西書(這一情況下詳),但也有一些舊學書籍。如1897年張元濟曾讓汪代購《墨子閑詁》,此書是清代集《墨子》校勘大成之作。毫無疑問,張元濟的舊學閱讀活動始于少年時代。對中國古典文獻的關注和熱愛,成為其一生閱讀實踐的一大主題。
張元濟的舊學閱讀活動更多在修身治心的層面上展開。從閱讀目的上看,其并未超脫士大夫文人的古典審美旨趣。他曾自我表白:“余喜蓄書,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遠,亦愛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曠神怡。”⑦值得指出的是,張元濟讀古、知古,但絕不泥古。張元濟曾從梁啟超處得到一部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對此他是非常感激的。梁啟超把這部書稱為“思想界的一大颶風”。彼時許多士族儒流對此書的批評甚至咒罵極其激烈。“惑世誣民”“非圣無法”“心術可疑”“學術不端”等語紛至沓來。但是,張元濟對此書并沒有持和經學衛道士一樣的保守立場。結合他在維新變法運動中的活動和表現,可以推知他對這部在當時語境下的一反傳統經學主張的創新之論至少是接受的,甚至持歡迎態度。如是舊學閱讀觀,決定了張元濟并不是一個保守的儒家士大夫文人。即便是伴隨終身的閱讀習慣和愛好,張元濟也做到了“己所欲”,也不“強施予人”。戊戌政變后,罷官去職的張元濟南下上海主持南洋公學。此間,他改變了學生讀“《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御批通鑒輯覽》等舊書”的做法,轉而“勉勵學生讀新書”⑧。顯然,張元濟是用實用主義的眼光審視中國傳統典籍的。在民瘼深重、列強環伺的時局下,他認識到傳統典籍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節奏。為求新知,西書和新書才是主要獲取渠道。從事實上看,京官時期的張元濟閱讀史,以求新知為目的的閱讀實踐更為奪目。
二、汲汲于西學:張元濟的新知閱讀
上文已經談到,雖然張元濟接受的是科舉制度下的古典教育,但他并非一個保守的國粹主義者。相反,張元濟在危機日深的國勢下,選擇以一種廣博的文化觀擁抱西學。他說,“今之自強之道,自以興學為先。科舉不改,轉移難望”⑨。張元濟顯然認為,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理論已經挽救不了頹唐的國勢。他轉而對西方新輸入的先進知識文化報以極大的興趣和期望。因此,張元濟十分渴望接觸各種新知讀物。揆諸張元濟這一時期與汪康年的往來信函,經常被提及的事項就是催促汪康年郵寄《時務報》等維新報刊和委托汪康年代為采購各種報刊。“貴報久不來,能否設法郵傳,以饜閱者之望。將來需用圖籍,俱擬求尊處訪購。”⑩“前懇代購《東京日日新聞》暨《時事新報》,得君書,謂已函訂,如已寄來,并乞附《時務報》寄下為荷。洋文圖籍未知購得幾種?日來想已在途,尤為企盼。”?“讀三十二冊《時務報》,知尊處代售《湘學報》。久欲購閱,苦于未由。……請代寄一分至京,從第一冊起,該價乞代付,將來總繳。”?張元濟對新知的汲汲之態,躍然紙上。根據張元濟這一時期的書信,張元濟接觸過的新式報刊讀物至少包括《時務報》《東京日日新聞》《時事新報》《東報》《知新報》《農學報》《萬國公報》《湘學報》《鄂學報》《經世報》《蒙學報》《國聞報》《薈報》《芻言報》。在書籍方面,張元濟的接觸面亦十分廣泛。他曾從梁啟超處取得一本《西學書目表》。此書著錄譯書約300種,是當時了解西學的重量級讀物。張元濟購買西書的渠道還是通過汪康年進行的。維新運動期間,張元濟創辦通藝學堂,并主持學堂工作。他多次通過汪康年為學堂購置圖籍。“托購格致等圖(除天文圖、百鳥圖已購外,余均請代購。并圖說各一冊、天文圖說二冊、百鳥圖說一冊)并各種書籍,如兄事太忙。或仍托少塘一購。”?“單墾購各種圖書,格致室無之,請于廣學會及洋書坊一詢。天文百鳥百獸暨光電水熱各種一切圖說,均系益處智書會本,諒必有之。請代購全分(惟天文圖說需兩分)。至各種圖,如滬上無之,可否即日示悉,當托友人在外洋購之。”?張元濟對西學接觸面之廣、程度之深、訪求之急,可見一斑。同時,為了能更好地閱讀西學讀物,張元濟開始學習英語。在當時鄙夷洋務的社會語境中,身為朝廷官員的張元濟的這一舉動絕對是一種另類先鋒行為。于是,張元濟被譏諷為“二毛子”式的人物。
京官時期,張元濟的新知閱讀實踐還有一重要特征,就是他深度介入新知閱讀共同體建設,成為當時京城新知閱讀共同體的重要個體節點。維新運動期間,大量有關西方政治制度、科學知識、社會文化的書籍涌入。閱讀新知讀物,成為當時開明帝制官僚和先進知識分子的時尚之舉。圍繞著這些新知讀物,這群追逐新知的人天然地形成一個有著共同閱讀旨趣的共同體。他們傳遞、分享、交流先進讀物,成為變法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在這個閱讀共同體形成的過程中,張元濟扮演著重要的個體節點角色。這一角色主要表現在,張元濟積極參與《時務報》的代銷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經驗累積,張元濟成為各家報紙駐京的“代銷點”。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張元濟說:“上海各報現在歸弟經手者,有《農學》《知新》《蒙學》《譯書公會》《實學》等報,此外《萃報》《求是》當亦可以歸并。”?對于張元濟來說,承擔如此多的報紙代銷工作顯然是一沉重的擔子。他自感責任重大,兩次向汪康年談及此事,希望汪能夠給予妥善處理。張元濟曾組織和參與過一個以“約為有用之學,蓋以自強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茍且畏縮之風”?為宗旨的團體,名曰“健社”。其成員大多為講求西學、思想開明的京官。這一團體后來發展成規模較大的西學堂。很有可能健社乃至西學堂成員的新學讀物就是從張元濟處取得的。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張元濟曾提到,“貴報嘗譯《東京日日新聞》暨《時事新報》二者,友人頗欲購閱,可否即托貴館古城先生代辦兩分”?。這里的友人,即指急盼從張元濟那里取得新知讀物的閱讀共同體成員。在以張元濟為重要個體節點的閱讀共同體中,還有一位重量級的成員,即光緒。光緒自身有強烈的新知閱讀欲望,經常開列書單交由總理衙門進呈。這一任務則落在了張元濟身上。“當時京師書鋪新書極少,張先生往往以篋中所有,并向知友乞假,湊集進呈”?。光緒帝所閱的《日本國志》即為張元濟所呈。
三、張元濟早期閱讀史對出版實踐的效應
上文對張元濟早期閱讀史的概貌做了鳥瞰式的描畫。這僅是本文的基礎任務。如果閱讀史研究停留在對個體閱讀活動的挖掘和梳理層面,就擺脫不了蘭克史學的桎梏。布洛克指出,統帥和啟迪歷史研究的是“理解”。?用這一論斷觀照閱讀史研究,除了閱讀行為本身應得到挖掘外,閱讀的意義和價值同樣需要得到足夠的重視。誠如閱讀史專家戴聯斌所言:“閱讀行為本質上就是尋求文本意義的一個活動”?。如何尋找和確證閱讀行為內蘊的文本意義以及文本意義對閱讀者的作用過程,應是閱讀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兩位學者觀點的啟迪是,閱讀史研究要想有新的進路,必須考察閱讀行為的輻射效應。閱讀史研究的任務除了考證歷史上真實讀者的閱讀活動外,還要透過真實讀者的思想形成和行為實踐來窺探閱讀所產生的意義。具體到張元濟身上,他的一生與書相伴相隨,其早期閱讀實踐勢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來的出版實踐。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接下來的工作是縷析二者之間的關系。
1.實用主義閱讀觀助力“啟蒙出版”
上文業已提及追求“有用之學”是張元濟發起和參與健社的主要目的之一。他認為“泰西種種學術”可以用來“掃腐儒之陳說而振新吾國民之精神”?。張元濟雖未對何為“有用之學”做出精確的解釋和界定,但他所接觸的新知讀物顯然是“有用之學”的主要內容。可以看出,張元濟的閱讀活動具有鮮明的“致用”色彩。但這種“致用”絕非儒家修齊治平理論的外顯,而是杜威所說的實用主義。在杜威那里,知識被理解成“純粹的社會應用”?。而張元濟認為,西學讀物包含富國強種的奧秘,所以他才會盡全力接觸和傳播西學。在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張元濟認為無用的東西,是科舉制度下的知識理論。用他自己的話說,即“帖括無用”。如果不引進全新的知識風潮,造成的后果將是“廷臣唯諾,不達時務”?,朝廷遍布愚昧腐朽的“非洲太古之人”?。在這個意義上,張元濟眼中的新知閱讀的宗旨和杜威實用主義幾乎同調。因此,把張元濟的閱讀觀飾以實用主義的標簽,是合適的。
京官時期的張元濟雖未萌發自覺的出版意識,但這種實用主義的閱讀觀已經開始塑造他后來的出版思想。這一點,清晰地顯示在他對當時出版物的評價之中。張元濟曾多次對汪康年表達對《時務報》的贊許之情。“《時務報》讀過八冊。崇論宏議,以激士氣,以挽頹波,他年四百兆人當共沐盛德,此舉誠不朽矣。”?與此同時,他對孫家鼐的官書局大為不滿,批評它“所刊局報,多系蕪詞。閣抄格言,最為可笑。洋報偶有微詞,譯署原文咨送,均被刪削”,而改變這一陳腐態勢的方法則是“新出緊要圖籍,尤宜從速譯印”。?上述一揚一抑的“媒介批評”和提出的解決之道或可被理解為張元濟出版思想萌芽的表現。從中可以解讀出張元濟清醒地認識到高質量的書籍傳播對改變國家面貌的重要作用。在張元濟看來,有效用的信息出版活動,可以收到“歆動群倫”?的效果。
入館之后,這種以實用主義為指向的出版思想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在張元濟眼中,出版的目的是“可以提攜多數國民”?。換言之,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要“以扶助教育為己任”?。這也成為張元濟為商務印書館定下的出版宗旨。從反面來看,張元濟明確反對有害讀物的出版。在給蔡元培的信中,他極力批評涉及“誨淫故技”?的讀物,希望當局加以取締。此外,他還兩次拒絕由商務印書館代售刊有康有為鼓吹帝制的文章的《不忍》雜志。這種對出版物質量的把控和張元濟對孫家鼐的官書局的批評,是一脈相承的。很顯然,作為職業出版家的張元濟對應該出什么書、不應該出什么書,有著清晰明確的標準。這一標準取決于出版物對社會大眾的實際利益。張元濟的實用主義出版觀表露無遺。至此,張元濟強調“有用”的閱讀觀轉換成強調“有用”的出版觀。在這種出版觀的指引下,張元濟主持下的商務印書館的知識生產活動無不以對社會、國家、文化的積極效用的追求為己任。這和張元濟實用主義閱讀觀的思想內核是一以貫之的。
商務印書館第一個重大貢獻莫過于編纂新式教科書。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后,新式學校層出不窮,傳統儒家開蒙讀物已不能適應新的教育形勢。開發和出版新式教科書成為彼時中國出版業最大的市場所在。在這一背景下,為“力求適應潮流需要,以符提倡協助教育之初衷”?,張元濟立即組織蔡元培、蔣維喬、吳丹、高夢旦等一批新式知識分子從事教科書的編纂。及至1925年,在張元濟的領導下,商務印書館共推出了“最新教科書”“共和國教科書”“新制教科書”三大套現代新型教科書。
再來看商務印書館的翻譯出版活動,同樣凝結著張元濟“以用為先”的理念。以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復譯著為例,該館出版再版嚴譯名著包括《天演論》《原富》《群學肆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名學淺說》。?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些西方名著對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這些譯著的閱讀和傳播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商務印書館類似的翻譯貢獻還有許多,如林紓所譯《迦茵小傳》《撒克遜劫后英雄略》《拊掌錄》、蔡元培所譯《妖怪學講義》《倫理學體系》等。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事業成為國人近距離觀察和理解西方社會思潮和思想文化觀點的重要窗口。通過商務印書館的翻譯出版活動,中國社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與外周世界共振。此外,科技類譯作同樣璀璨奪目。謝洪賚所譯《幾何學》、黃英所譯《動物學》、杜亞泉所譯《植物學》、包光鏞所譯《地質學》等,?極大促進了國人自然科學素養的提高。在這個意義上,商務印書館的翻譯出版活動在中國近代文化的啟蒙和實現中國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而這些巨大社會效益的產生,顯然和早年“沉湎西學”的張元濟追求“有用之學”的閱讀觀所產生的思想效應是密不可分的。
2.古籍閱讀實踐與古籍傳承出版的融合
前文已經談及張元濟對中國傳統典籍和家鄉文獻的熱愛。讀古書,已經成為張元濟生命歷程中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才會自我表白“我是書叢老蠹魚”?。即使在繁忙的館務之余,張元濟依然保持著閱讀古籍的習慣。主持館務后,張元濟對古籍的態度超越了傳統士大夫文人的審美情趣。他開始從保存民族文化的高度審視古籍出版。用張元濟自己的話說,他要“為古書續命”。“保存國粹”“以餉學者”成為張元濟決心大規模介入古籍搜求、輯印與出版工作的目的。值得強調的是,在商務印書館輯印出版古籍的過程中,張元濟的身份是雙重的。具體地說,他既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出版經理人、策劃人,又是以文獻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和版本學家的身份參與到古籍的搜求、編輯、整理的過程中。前者是職業身份,后者是學者身份。而后者身份的形成基于作為傳統讀書人的張元濟在古典文獻方面數十年如一日的閱讀研究。
面對大量珍貴古籍在戰亂中毀損散佚的局面,張元濟慨嘆道:“自咸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對此張元濟深感責任重大。所以,對于古籍保存他才會說“抱殘守缺,責在吾輩”?。這是出于一位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這樣,找書、讀書、編書幾乎是張元濟的本能行為。為得善本,在與時人交往的過程中張元濟時常囑咐他人為商務印書館代購古書。如他在一封給丁文江的信中說:“先生行蹤所至,如遇有志書為敝館所無者,務祈代購。不能購,則托人代抄,雖費多金不惜也。”?再以張元濟1916年的日記為例,檢閱之,托人購書的記錄俯拾皆是。“孫星如介紹元本《圣朝混一方輿勝覽》六冊,索價一百廿元。還一百元。沅叔代購明抄《文苑英華》,二百四十元。又吳印臣刻《宋元刊本詞》,卅元。”(二月十四日)?“托伯恒買《學海類編》四百元《墨海金壺》五百元《學津討原》三百元。如三部同購,可加二三百元。”(三月二十一日)?“為舊書部買入《資治通鑒》《佩文》《書畫譜》《段說文》《許說文》《隸辨》又一種,共八十二元。”(三月廿二日)?張元濟曾多次不顧路途遙遠艱難而外出訪書。1928年,張元濟遠渡重洋,赴日訪書。“訪日期間,在一個多月時間里,除星期日外,每天都聚精會神、如饑似渴地選閱國內罕傳的宋元舊槧,晚上整理筆記,往往直至午夜,毫無倦容。”?“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覯,輒影存之。”?這句精準描述正是張元濟上述辛勤訪書、問書、求書、選書的生動寫照。同時,張元濟身體力行,事無巨細地參與古籍的整理和編輯過程中。以張元濟1925年的與館中編輯丁英桂的通信為例,關于古籍的編校記錄,同樣俯拾皆是。“《元秘史》清樣亦閱過。”?“《樂府新聲》校記閱過,稍有改動,并原稿送還。”?“《宋史》一卷閱過送還。”?“《洛陽伽藍記》毛樣已閱。”?由此可見,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古籍過程中,張元濟的上述兩種身份是高度融合的。對古籍孜孜不倦的追尋,既是出于讀書人張元濟對傳統文獻的閱讀熱忱,又是出版家張元濟領導下的商務印書館對傳承民族文化高度負責的體現。也就是說,作為讀書人的張元濟在古籍方面長期的閱讀實踐和作為出版人的張元濟的出版實踐是高度統一的。正是這種統一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張元濟對商務印書館另一大歷史貢獻—輯印《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
上文業已提及,關注鄉邦文獻是張元濟舊學閱讀的一大特色,這一點也影響了商務印書館古籍出版的文化氣質。舊年對桑梓文獻的獨特興趣,使得張元濟入館后,不僅關注經典古籍的傳承,還十分注意地方特色文獻的搜集與出版,特別是其家鄉海寧先人的遺著。他說:“寒家先世手澤經兵燹后存者亦復寥寥,弟年來銳意搜求,什不獲一,追維祖德,感喟無窮。”?“此真千秋恨事矣。”?在這種情感的感召下,張元濟非常注意對海鹽以及其他地方文獻的找尋。在得知丁文江游歷貴州后,張元濟囑其“搜集貴州縣志”?。他對同是嘉興籍的同年王甲榮說“友人見告秀水高等小學藏書樓有海鹽人王文祿所輯《海鹽文獻》一部,計二十卷,乞代查。如能借出一閱最妙,否則托人代抄一分,乞估抄資,又托。”[51]民國之初,他收集到的全國方志,有2600多種。通過張元濟對其鄉邦文獻數十年如一日的訪求,商務印書館相繼輯印了《涉園題詠》《涉園叢刻》《槜李文系姓氏總目》《橫浦文集》等海鹽地方文獻。其中,《橫浦文集》經常被張元濟作為禮物饋贈友人,足見他對其重視、珍愛程度。
3.源自閱讀的“民族人格”注入出版實踐
張元濟思想中的“民族人格”理論廣受學者尊崇。有學者探究其“民族人格”理論的形成時,認為儒學傳統精義與其家學淵源這兩種因素的影響為大。[52]進一步考察,張元濟是從中國傳統典籍,特別是儒家經典中汲取了對民族的熱愛和對國家的忠誠的。“考文獻而愛舊邦”,張元濟的這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提示這種愛國思想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他對中國傳統典籍的閱讀。當張元濟熟讀了諸多儒家經典時,他認為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53]由此可見儒家典籍在張元濟愛國思想形成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張元濟從家鄉海寧文獻閱讀中也獲得了對民族的體認和關懷。上文提到,青年時期的張元濟閱讀了其先祖的《入告篇》。這一閱讀行為使他“益曉然于致君澤民之道”[54]。雖然這一讀后感有些許封建色彩,但仍可視為張元濟“民族人格”思想的早期萌芽。
張元濟身體力行著這種“民族人格”。上海被日軍攻占后,深陷貧困的張元濟寧可賣字鬻文,也不肯為日軍當局站臺;1948年,在中研院第一次院士開幕式上,他痛斥國民黨弊政,呼吁和平;新中國成立后,他又為新中國各項事業獻計獻策。在張元濟漫長的出版生涯中,同樣無處不體現著他的“民族人格”。張元濟出版生涯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開創新式教科書出版之風氣。后人尊其為“中國現代教科書之父”[55]。在解釋其投身這一事業的原因時,張元濟說“可盡我國民義務”[56]。在輯印出版古籍、保存民族文化領域,張元濟“做出了萬古不磨的弘功偉績”,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文化寄托人”。[57]為開啟明智、溝通中西文化,張元濟積極傳播新學。有學者認為這始終是“以熱愛祖國和革新社會作為自己的出發點”[58]。一句話,作為出版巨擘,張元濟把源自自身閱讀的“民族人格”全方位地注入他一生的出版實踐中去。
在出版領域,生發于閱讀活動的“民族人格”最典型的體現莫過于張元濟在1937年5月出版的《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有感于當時少數附逆落水的漢奸,張元濟從其熟讀的《左傳》《史記》《戰國策》中選取了若干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故事,編著成書,以此激勵民眾奮起抗日,保全國土。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上海各報,時借是書發言警眾”[59]。在該書中,張元濟強調,書本上有不少的豪杰可以做模范。他所選取的人物,皆來自“人人必讀的書本里”[60]。在這里,不難看出張元濟是現身說法,以自身閱讀體悟,來說明傳統典籍對民眾愛國主義思想形成的巨大作用。此書出版時,商務印書館曾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這一則廣告語清晰無誤地呈現了張元濟的閱讀活動與成書之間的關系。“作者校閱《百衲本二十四史》,最近校《史記》時,深感于古代英雄人格之高尚,足以激揚民族之精神,因就列傳及《左傳》《國策》中選取十數人,均舍生取義,復仇雪恥之輩,堪為今日國民模范,并將原文譯成白話,分排上下層,對照讀之,明白淺顯,尤為感動,今欲復興民族,必先提高人格,此為非常時期不可不讀之書。”[61]
四、結語
張元濟是西學東漸大背景下典型知識分子的代表。個人的選擇和時代的影響共同造就了他早年橫跨中西的閱讀實踐。閱讀形塑思想,思想創造實踐。臺灣有學者將張元濟的文化觀描述為一種“調適取向”的文化觀,“既非‘國粹派’或‘歐化派’,亦非‘中體西用派’,其對于中西文化確能宏觀而涵容,對不同立場之見解亦具多元之尊重”[62]。這種生發于閱讀實踐的混融文化氣質投射到了張元濟的出版實踐中。張元濟“在積極傳播新學的同時,重視流通古籍,一生努力溝通中西文化”[63]。從張元濟閱讀史到出版實踐,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影響鏈條。概而言之,張元濟融匯中西的閱讀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商務印書館開創新知、引進西學和保全國粹、傳播古籍兩種看似對立的文化功績。商務印書館引領風氣、中西合璧的文化氣質,和張元濟的閱讀實踐是相互呼應的。
達恩頓主張閱讀史研究的核心是“流變不已的讀者群如何建構不斷變化的文本的意義”[64]。閱讀是一種信息輸入行為,經過復雜的人內傳播過程,總會以各種方式輸出傳播。閱讀的意義和效果終將外顯為個體的行為活動。因此,除了根據歷史上真實讀者記錄下的閱讀感受、體悟、思考外,考察真實讀者各種行為實踐亦是窺探閱讀所產生的意義的一扇窗口。“腹有詩書氣自華”即暗含這個道理。也就是說,可以將真實讀者的實踐史和其閱讀活動聯系起來,建立一條從閱讀到實踐的解釋通路,以此來豐富閱讀史研究的可能性。作為個案研究,本文對張元濟閱讀史和出版實踐所建立的聯系也許是粗疏的,但深度挖掘和呈現出版人的閱讀史,闡明從閱讀到出版實踐的作用機制,應該是拓寬未來出版史研究內涵的一個可行路徑。
注釋:
① 達恩頓.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M].呂健忠,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
②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50.
③ 相關成果包括《試論王云五“百科全書式”的讀書觀及其實踐》《出版家王云五的讀書生涯》《王云五的讀書觀》《王云五怎樣讀書》等文。
④ 本文將張元濟早期閱讀史界定為張元濟1901年加入商務印書館之前的閱讀活動,主要考察張元濟入仕之前、擔任京官和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三個階段的閱讀活動。
⑤? 張榮華.張元濟評傳[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5:2,106.
⑥⑨⑩??????????[56]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二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96,169,171,172,181,173,174,190,170,225,170,225,175,196.
⑦ 陳江.張元濟論出版工作—張先生書海拾貝[C]//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242.
⑧ 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53.
? 孫慧敏.翰林從商—張元濟的資源與實踐(1892-1926)[J].思與言,2005(9):15-52.
?? 張元濟.張元濟詩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169,110-113.
?? 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4,92.
? 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M].黃艷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31.
? 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35.
?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188.
? 張人鳳.戊戌變法與張元濟[C]//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554.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三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461,467.
??史春風.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97.
? 董麗敏.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1902-1932)[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335.
? 鄒振環.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55.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九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3,14.
?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八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2.
???????[51]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6,68,71,73,74,223,5,225.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六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55,175,176.
? 趙守儼.《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校史隨筆》的學術貢獻[C]//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59.
[52] 柳和城.張元濟的思想及其淵源初探[C]//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413.
[53][60]張元濟.中華民族的人格[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1,2.
[54] 張榮華.張元濟評傳[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5:2.
[55] 吳小鷗,褚興敏.張元濟與現代教科書發展[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5(5).
[57] 周汝昌.中華文化托斯人[C]//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443.
[58][63]劉光裕.論張元濟的編輯活動—兼談在文化史上的影響[C]//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106,105.
[59] 柳和城.兩代學人一對摯友—記張元濟與胡適交往始末[C]//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219
[61] 牟小東.讀蔡元培與張元濟往來書札[C]//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242.
[62] 劉怡伶.近代變局下的另類選擇—張元濟的文化思考與實踐[J].中極學刊,2001(12).
[64]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