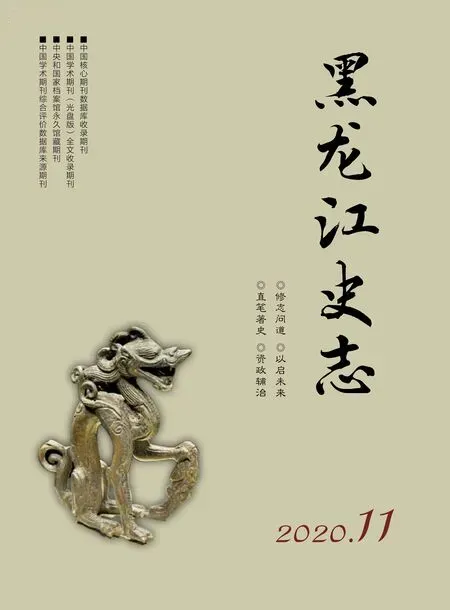中國古代人口思想與西方歷史上人口理論的比較
國福麗
(黑龍江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一、中國古代人口思想
(一)春秋戰國時期商鞅和韓非子的人口思想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春秋時期大多鼓勵人口增長。與之不同的是,商鞅理性地看到了人口與土地之間存在著矛盾,強調人與地的對比關系。而且商鞅注重人口調查,是歷史上組織全國范圍人口調查的第一人。韓非子則在商鞅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把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視為“民爭”的根源,他指出“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韓非子主張通過法制來制止“民爭”。
(二)東漢末年徐干的人口思想
作為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徐干著有《中論》一書,其中《民數》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關于人口問題的專論。他說:“故民數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罷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意即,國家的一切政治經濟措施皆要以人口數量為依據,將掌握人口數量的重要性提高到治國平天下的高度。
(三)唐代韓愈的人口思想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人口思想與其相生相養論有密切聯系。韓愈認為,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間相生相養,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勞動,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則他對社會就是無益的。韓愈進一步地將人口按其職業分為“六民”,認為農、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養的,為社會所需要。士是治人者,由別人供養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對社會有益的人。而僧、道二民,則不從事農工商等經濟活動,卻需要農工商供養,實質上是一種過剩的人口理論。
(四)元代馬端臨的人口思想
儒學教授馬端臨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明確提出人口質量問題,并論述了其重要經濟意義的人。他指出,考察人口與國家富強的關系,不能只看數量,還要看質量如何。他說:“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捍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馬端臨對人口質量的重視,是中國人口思想的一個重要進步。
(五)清朝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乾嘉時期中國人口快速膨脹,60 年間從1.2 億增長到3 億,引起了人們對人口問題的特別關注。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計篇》中,提出了中國傳統社會最為典型的絕對人口過剩理論。他認為在長久的和平條件下,人口會出現過快增長的現象,其原因既有人口本身的自然繁殖,也有土地兼并、貧富分化等社會原因的催化。他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人口過剩帶來的不利后果,并進一步提出了抑制人口過快增長的兩大對策:“天地調劑之法”和“君相調劑之法”。前者指通過自然災害和生存競爭減少過剩人口,后者指統治者通過人為的政策干預去緩和人口與生活資料的矛盾,包括發展生產、調劑人口區域分布、減輕稅負、抑制土地兼并、賑濟災民等。總體而言,洪亮吉對人口問題的看法比較悲觀,對于抑制人口過剩沒有足夠的信心。
二、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的人口理論
(一)重商主義的人口思想
重商主義興起于15 世紀西歐地理大發現之后,世界市場形成之時,其主要信條是推崇通過政府干預手段,保持對外貿易順差來實現財富積累。在人口問題上,重商主義認為,大規模勤奮工作的人口,不僅能夠為國家提供充足的勞動力進行殖民擴張和海外貿易,而且有利于保持低工資從而降低出口商品的價格,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此,重商主義鼓勵增加人口,并通過各種法令嚴厲懲罰游手好閑者和不務正業者,促進人口向現實勞動力資源轉化。
(二)古典經濟學的人口思想
古典經濟學形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立的初期,由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資源來支撐工業的擴張。因此,古典經濟學家對人口增長均持有積極態度。威廉﹒配第認為人口眾多可以增加政府收入,減少政府統治更多人口的單位成本。存在失業時,政府應該雇傭失業者來進行各項公共工程建設,而籌集公共工程的資金則來源于比例稅和人頭稅。可以說,威廉﹒配第是提倡采用公共服務創造崗位來減少失業的凱恩斯理論的先驅。
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在其傳世之作《國富論》中,專門設立了一章來探討勞動工資問題。斯密寫道: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與工資基金成比例,而工資基金來自于雇主們的剩余收入和剩余資本,即來自于國民財富的增長。斯密認為,對人們造成是否生育的激勵,從而決定了國家人口數量。因此,高工資既是財富增長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斯密主張高工資,認為高工資會鼓勵勞動者勤勉,這與重商主義的觀點不同。
古典經濟學的英國代表大衛·李嘉圖,則以地租為核心展開了他的經濟理論。他認為,人口增長與固定的土地數量以及農業中的收益遞減規律相互作用,導致一方面糧價提高,地租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增加,另一方面利潤減少,資本積累受到限制,從而對勞動力的需求將達到極限。
(三)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
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于馬爾薩斯應歸屬于古典經濟學還是庸俗經濟學存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扭轉了西方歷史上長期以來對于人口增長的樂觀態度,敲響了全世界對人口過度膨脹負面影響的警鐘。馬爾薩斯認為,社會上的罪惡和貧窮現象,不應歸咎于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而應歸咎于人類的生育能力。他認為,如果不受控制,人口將以幾何級數增長,每過25 年翻一番;而以糧食為代表的生活資料最多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無論如何,生活資料的增長必然遠遠不能滿足人口自然增長的需求。因此,應對人口增長進行兩種控制:“預防性控制”和“積極控制”,前者是指通過道德約束控制人口出生率,后者是指運用自然法則如饑荒、瘟疫、戰爭等來提高人口死亡率。馬爾薩斯說:“我們應該促進大自然在制造死亡率方面的作用,而不應該愚蠢徒勞地致力于阻礙其作用。”
(四)坎南和維克塞爾的適度人口理論
19 世紀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帶動了鋼鐵、石油、汽車等產業的發展,也帶動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社會供養能力得到改善,而西方的人口增長卻放緩了。馬爾薩斯理論破產后,英法國家開始擔憂人口不足的問題。倫敦學派的奠基者埃德溫·坎南在其著作《初等政治經濟學》和《財富論》中,提出了適度人口理論。他從人口與土地、人口與生產率、人口與收益等方面探討人口的適度規模。所謂適度人口,是指在一定的時期內在一定的土地上生存的、達到產業最大生產率的人口數量。這里的產業不僅指農業,而是全部產業。坎南特別強調,適度人口不是一個靜態數字,而是動態變化的,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在推動著產業的最大收益點發生變化,推動著最大收益點向有利于人口增加的方向變動。“這一代人口是上一代人口存在的結果,又是下一代人口出現的原因,因此適度人口是從長遠來看的最適度人口。”坎南認識到,調節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使人口達到適度規模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人口政策應有所區別。
與坎南同時期的瑞典經濟學家維克塞爾,1910年在日內瓦國際馬爾薩斯者聯盟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論適度人口》的演講,第一次提出了“適度人口”的概念。維克塞爾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有兩種相反的趨勢:一是由于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二是人口增加有利于分工和協作的深化,新的產業組織能夠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對于達到適度人口規模的途徑,維克塞爾認為提高死亡率不可取,降低出生率則是可以采用的。
(五)卡爾·桑德斯的適度人口密度理論
卡爾· 桑德斯是西方歷史上第一個研究人口質量問題的學者,他于1922 年出版了《人口》一書。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他認為經濟標準是判斷人口適度數量的唯一標準。桑德斯進一步提出了人口適度密度的范疇,并把獲得人口平均最好的生活水平作為適度人口密度的評判標準。適度人口密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理想的人口密度取決于技術和知識的應用程度、環境的性質、民族的風俗習慣等。他指出,適度人口數量和適度人口密度是一個大概數,要準確計算它們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提出這個概念有助于判斷人口數量是過多還是過少。桑德斯的適度人口密度理論,是對坎南和維克塞爾適度人口理論的重大發展。
三、中西方人口思想的比較
(一)相同點
縱觀以上中西方歷史上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思想,可以發現不論是中國古代,還是20 世紀30 年代之前的西方歷史,都存在著對人口問題大致相同的一些思想發展脈絡:
第一,都是從早期積極鼓勵人口增長逐漸轉變為反思人口增長過快,出現過剩人口的危害,再轉變為主張人口數量應與經濟發展相協調。
第二,對于人口問題,都是先關注人口數量到后關注人口質量,總的來說,經濟學家們對于人口數量的探討更多,這也是人口政策控制的重點。
第三,對于過剩人口,大部分學者關注的是過剩人口的總量,對過剩人口的結構和地區行業差異分析得少。
第四,對于過剩人口引起的社會矛盾,大部分學者都主張應由政府去進行主動干預。
第五,都指出了人口增長速度快于生活資料增長速度的嚴重后果,治理措施也大同小異。
(二)不同點
第一,在研究對象上,歷史階段的不同決定了中外人口問題的研究對象關注點不同。中國古代長期處于封建社會中,人口問題更多地體現為人的矛盾,關注點在于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糧食等生活資料與人口數量的不協調。而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期,人口問題更多地是在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過程中凸顯出來的,關注點在于資本要素和勞動力數量的不協調,強調的是勞動相對于資本而言過剩與否。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中國更早注重全國性人口調查,建立人口調查登記制度。中國古代學者的研究更多地將人口問題與社會制度相聯系,探討了生產關系層面,分析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收入分配與人口問題的相互影響。西方學者的研究更多地將人口問題與市場經濟相聯系,探討了生產力層面,分析經濟增長、產出效率與人口問題的相互影響。
第三,在文化背景上,中國古代學者受儒家文化影響深遠,對人口問題的觀點始終擺脫不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例如儒家文化以“仁、禮”為精髓,在中國政府救濟貧民是理所當然的職責。西方經濟思想早期受基督教影響嚴重,到古典經濟學則是在資本主義文藝復興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強調維護人權,而他們所要維護的人權是上層社會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人權,因此李嘉圖和馬爾薩斯都反對劫富濟貧。
第四,對人口問題的重視程度有差異,中國古代的重視程度更甚于西方。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論述人口問題的專篇,是公元200 年左右徐干的著作。徐干將掌握人口數量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要務,將人口問題的重要性上升到治國平天下的高度。馬端臨則在公元1300 年左右,就將人口質量問題明確提出來并論述了其政治經濟意義,這要早于西方人口質量研究第一人卡爾· 桑德斯六百年左右。
第五,對過剩人口的治理手段方面,中國古代更傾向于發揮政府人為的作用,運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利。例如韓非子的法制,馬端臨的“君相調劑之法”。西方經濟學歷史上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兩種主張交替占上風,作為古典經濟學家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就不主張對工資進行管制,傾向于由市場機制自發決定工資水平。
四、對我國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人口不足或人口過剩,都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一個國家應該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適度的人口規模,這種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是與本國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稟賦、本國的知識技術應用水平、本國工農業的生產能力、本國的撫養能力相適應的,是動態變化的,也是需要政府去主動運用人口政策和產業發展政策,進行調節和干預的。不論是人口數量的調節,還是人口質量的提升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制定人口政策應當著眼于國情,著眼于長期,一國之內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人口政策應允許存在差別。
對于過剩人口,如果能夠有效吸收和利用,使之轉化為現實的勞動力資源,則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助力。政府要在過剩人口的就業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以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務的方式來創造就業崗位,配套以適當的稅收政策,以免造成政府財政負擔。減少非生產性勞動者所占的比重。通過發展經濟、擴大資本積累規模來刺激勞動力需求,是解決過剩人口的根本措施。
過去,我國享受了人口快速增長、年齡結構合理帶來的人口紅利。當前,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勞動力資源的相對短缺和結構性過剩可能同時并存,人口紅利窗口發生變化。一方面我們要著眼于提高人口出生率,鼓勵生育,調整人口年齡結構;另一方面要對結構性過剩人口進行知識技能培訓,提高人口質量,增強勞動力流動,完善社會保障。
人口問題不是一個單一的獨立的社會問題,而是與資源、環境、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等相融合的復雜問題。我國在政府的有效治理下,在科學技術和人類理性日益發展的未來,一定會有能力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