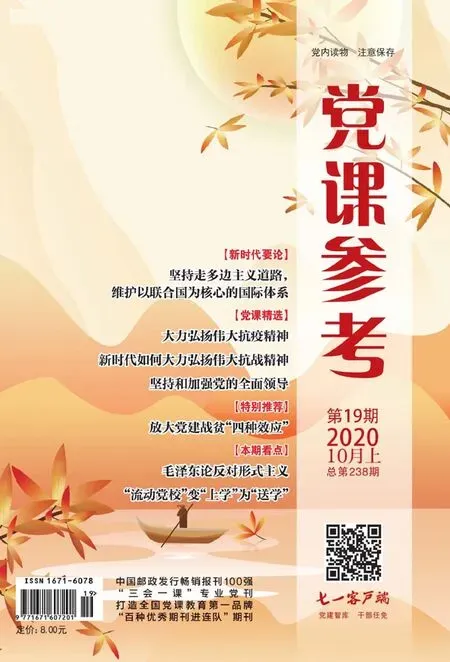開國大將許光達的學習人生
〉〉〉〉〉 全建業
許光達,1908年11月19日出生在湖南省長沙縣東鄉蘿卜沖的一個貧苦農家,就是現在的黃興鎮光達社區。許光達是新中國最年輕的開國大將,曾經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首位裝甲兵司令員,被譽為“中國裝甲兵之父”。回顧許光達的一生,無論是讀師范、入黃埔、搞革命、留學蘇聯、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他都將學習作為奮斗的基石,作為一種自覺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不僅體現在對知識的渴求與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探究上,更體現在把學習成果應用于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
樂于鉆研求甚解
1932年,許光達在應城戰斗中身負重傷,因當時蘇區醫療條件差,被送往蘇聯治傷,后來進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在這期間,他下定決心突破俄文。他說:“讀別人翻譯過來的書,不如自己去讀原文書。”沒過多久,在一次學習交流會上,許光達竟然能夠用俄語跟蘇聯同志結結巴巴地談話了,這讓所有同學感到非常驚訝。每次授課結束后,他都有一大堆問題要問,不把問題搞清楚絕不罷休。許光達埋頭寫文章做學術研究的韌勁,在同期留蘇同學中是出了名的。
新中國成立之后,許光達把對學習的鉆研勁頭帶到了學校、帶到了部隊。1954年8月24日,他在第一坦克學校與學員談心的時候講道:“虛心鉆研,認真學習,在知識面前,是沒有任何可以驕傲自滿的,必須攻讀。也不用害怕,‘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科學面前不允許半點虛假。”后來,他還指示裝甲兵各級領導機關建立“軍官日”學習制度,給干部自學創造必要的條件。
除了督促各級軍官的學習,他自己更是學習不輟。在機關,只要軍委沒有重要會議,他都堅持與機關干部一同參加“軍官日”學習。每到院校,他都要抽空去教室聽課。有一次,許光達到第二坦克學校系統學習坦克技術。課后,他拿著筆記本走到教員面前問:“馬力的定義是什么?剛才我沒聽清楚。”教員回答說:“馬力,是指發動機的功率單位,一馬力相當于一匹馬那么大的力氣。”“不,我想知道這一概念的確切定義。”教員告訴許光達:“準確的定義是:一秒鐘把75公斤的物體提到一米的高度所做的功。”教員站在許光達面前,心里很是感慨,一位年過半百的將軍,學技術竟是如此認真。他曾經教過好多學員,還沒有一個學員對“馬力相當于馬的力氣”提出過質疑,唯有許光達較真。
還有一次,在上實車駕駛課時,許光達開著坦克在起伏的跑道上前進。只見他動作有條不紊,手拉操縱桿,腳踏油門,駕著坦克加速向前沖去。突然,前面出現了一個斜坡,許光達還未來得及把坦克調整過來,坦克便順著斜坡駛下去了。還好,坦克沒翻過去,停在一個很陡的斜坡上。這個意外情況把教員嚇壞了,他對許光達說:“您下車,我把坦克開過去。”許光達說:“不,我開上來的,我還要把它開下去。在這里我不是首長,是你的學員。”說完,他屏住氣,硬是把坦克從斜坡上開了過去。在許光達率先垂范學習精神的感召下,包括許多高級干部在內的廣大官兵習軍練武蔚然成風。
勤動筆墨苦用功
據粗略統計,許光達生前的讀書量超過一萬冊,而且很多書上都做了批注,留下的手稿達四五十萬字。不少人看到許光達在黃埔軍校和蘇聯學習的筆記,驚嘆其記錄之詳盡細致、標圖之準確美觀。特別是專家學者在審看《許光達軍事文選》文稿時,震驚于作者關于協同作戰、未來戰爭模式、機械化、現代化軍隊建設等一系列思想,超前了半個多世紀,其覺醒之早、角度之新實在難以想象。許光達特別喜歡把學習的思考記錄下來,不僅熱衷于讀書批注,而且勤于動手撰寫筆記。1926年至1927年,許光達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有一篇筆記叫作《野戰工程》。筆記內容非常詳實,繪圖精準,字跡工整,不僅有理論知識的記錄,還有基于現實情況的思考。1932年,他在莫斯科學習期間有一篇筆記叫《騎兵進攻戰的基礎》。這篇筆記不是一般知識點的簡單抄寫,而是對騎兵戰斗規律的深度挖掘,堪稱一篇極具理論深度和現實意義的學術論文。最有影響力的筆記非《坦克論》莫屬,這是他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期間的一篇學習記錄。許光達組建裝甲兵的很多思路,都得益于當時對坦克的研究與思考。可以說,如此嚴謹的治學作風伴隨著大將的一生。
我們還可以從他的一些學術論文中管窺其軍事才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以閃擊戰術橫掃西歐14國,并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一舉攻占了蘇聯的大片領土,世界為之震驚。德軍的閃擊戰術打得蘇軍節節敗退,莫斯科已面臨嚴峻威脅,很多人都認為蘇聯難以抵擋德國的進攻。而許光達卻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閃擊戰的歷史命運》一文。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對蘇德雙方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情況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在他看來,德軍閃擊戰之所以一時奏效,源于對手戰略戰術思想的落后和對于閃擊戰的毫無準備,當它遇到另一種最新型的、代表人類正義進行戰爭的、有同等裝備和技術的軍隊時,閃擊戰就會遭受悲慘的破產。而蘇聯紅軍就是這樣一種新型軍隊,它的軍事理論是建立在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基礎上的。因此,他認為希特勒的閃擊戰在蘇德戰爭中必然覆滅。戰爭的進程完全印證了許光達的預見,5個月后,蘇聯紅軍就對德軍發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德軍元氣大傷,節節敗退,最終覆滅。
學思結合融哲理
許光達十分講究學習方法,注重學思結合。他對一些問題總是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清醒的分析,并且善于把這些思考用文字表達出來。1930年1月5日,毛澤東撰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10多年之后,當許光達讀到此文時,寫了一篇讀書心得叫《歷史的回顧》,堪稱學思結合的典范。他根據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觀點,結合當年革命形勢,對洪湖蘇區革命斗爭進行了詳細的總結分析。他在文章中坦言:“當時我在洪湖,可惜沒能及時看到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洪湖若能按此執行之,那將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好局面呢?”
實踐證明,當年許光達琢磨的許多理論問題,在新中國武裝力量建設方面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關于坦克、裝甲車作戰特性的研究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1933年,國內蘇區紅軍武器裝備還留有諸多冷兵器時代的痕跡。許光達從列寧學院的軍事課堂上獲得了關于坦克作戰的知識,對坦克產生了濃厚興趣,從此開始熱切關注坦克及裝甲兵部隊在大兵團步兵突擊中作戰能力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之后,許光達成為共和國首任裝甲兵司令員。毫無疑問,他提出的“沒有技術就沒有裝甲兵部隊”這一經典軍事學術名言,以及他在解放軍裝甲兵建設方面的一系列精辟見解,都不是一時的靈感迸發。許光達成為一名軍事家不是偶然的,是他樂于學習、勤于思考,并升華為哲學思考的結果。他對理論和技術的高度重視,表現出了很強的“兵哲相容”的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