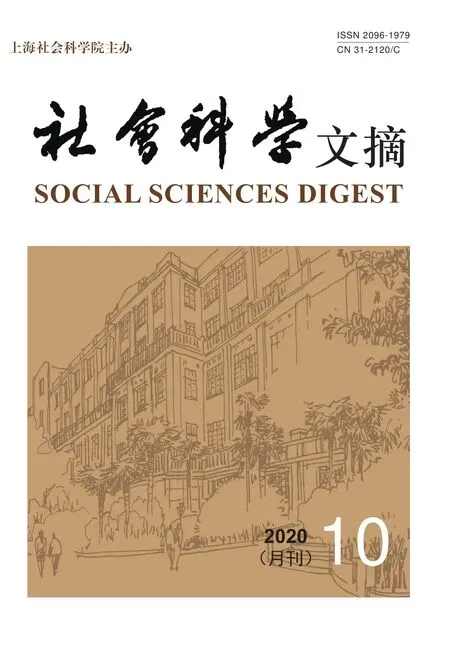社交媒體在疫情危機風險傳播中的核心作用與傳播機制
文/張克旭
社交媒體時代的危機風險傳播
(一)理論綜述:風險溝通與危機傳播的整合
風險溝通與危機傳播是兩個聯系緊密的研究領域,自20世紀80年代誕生以來,二者在理論發展和研究實踐上存在交叉,又有所區別。
1982年美國強生公司的“泰諾”膠囊投毒事件,引發了危機傳播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揭開了美國危機傳播研究的序幕。早期危機傳播理論代表性的有Fink提出的階段分析理論,提出包括潛伏期、爆發期、擴散期和消散期的“四階段”模式。到20世紀90年代,危機傳播研究迅速發展起來,代表理論包括Benoit的“形象修復理論”(IRT)、Birkland的“焦點事件理論”。2000年后,在對危機傳播既有理論進行整合的基礎上,Coombs提出了“情境危機傳播理論”(SCCT)。Frandsen和Johansen在整合“形象修復理論”和“危機情景分析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修辭話語場理論”(RAT)。2010年后,隨著社交媒體在危機傳播中的重要作用,相關的研究也更加豐富,比較有影響的是“社交媒體中介危機溝通理論”(SMCC),把社交媒體作為溝通中介,對組織機構的危機應對策略進行分析。
風險溝通的研究同樣受到突發事件的影響。1984年,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爾發生毒氣泄漏事件,促使美國政府于1986年通過了《超級基金修訂和補充法案》(SARA);同年,美國首屆“風險溝通全國研討會”在華盛頓舉行,標志著風險溝通領域開始走向成熟。以1986年為界,“風險溝通”開始成為研究中的焦點。此后,雙向風險溝通模式逐漸居于主導地位,而“社會-文化”取向的“風險認知理論”占據優勢。
目前學界對風險溝通與危機傳播之間的關系存在分歧,但都認識到二者的共同點、互補性和交叉性。Reynolds和Seeger在總結和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把風險溝通和危機傳播整合起來,并稱為“危機風險傳播”(CERC),提出了五階段模型,包括前危機、初始、保持、解決、評估。
在國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促進了風險溝通和危機傳播的研究。2003年的SARS疫情是我國相關理論研究的重要節點,同年國務院頒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促進了國外理論的引入和本土化思考。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H7N9疫情、2018年開始的疫苗事件,更促進了風險溝通和危機傳播的理論應用和傳播實踐,兩個概念的應用也出現合流的趨勢。學界對風險溝通和危機傳播關系進行辨析,提出政府對風險溝通與危機傳播的意識與策略,分析兩個概念的異同及整合模式等。國內相關的實證研究多從媒體報道、突發事件、輿情監測的角度切入,再運用危機風險傳播的理論進行分析。
(二)傳播實踐:社交媒體成為危機風險傳播的主渠道
自2010年開始,以Facebook、Twitter為代表的社交媒體蓬勃發展,公眾在緊急情況下會求助于社交媒體。在國內,媒體的傳播生態和民眾獲取信息的渠道發生很大變化。從媒體傳播生態來看,全民化、移動化、社交化已經成為社交媒體傳播的主要特征。這帶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傳播渠道的演變。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信息傳播中,以“雙微一端”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成為主渠道。
1.社交媒體是公眾獲取疫情信息的首要來源
從受眾媒介使用方式上,以“雙微一端”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成為獲得疫情信息的首要信息來源。根據“零點有數”發布的調查數據,微信群/朋友圈是公眾了解疫情信息的“第一渠道”,占比為63.9%;門戶網站/新聞客戶端占比為48.2%,微信公眾號(38.2%)和微博(37.2%)獲取信息的公眾接近四成;視頻/短視頻占比為15.1%。在傳統媒體中,電視的占比最高,為55.9%。此外,單位/學校/社區通知(15.8%)和朋友/熟人交流(15.3%)也占據一定比重。
2.社交媒體是疫情信息的主要擴散渠道
在疫情信息傳播中,受眾獲取疫情信息后的傳播擴散行為非常關鍵。根據北京師范大學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的網絡調查,網友對疫情信息的十大傳播行為中,微信朋友圈(45.1%)和微信群(36.9%)的熟人傳播最多。其次是網絡搜索相關信息(33.0%),微博發言或轉發占26.9%;也有19.0%的網民不做任何發言或轉發。再次,在新聞APP中發布或跟帖占16.0%,在短視頻平臺發布/評論占13.2%。最后,在百度貼吧(11.7%)、豆瓣、知乎(10.7%)等發帖跟帖比例差不多,還有2.5%會在境外媒體平臺發布內容。
相較于以報刊、電視和廣播為代表的傳統主流媒體,以“兩微一端”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已經成為疫情信息傳播的主戰場,尤其是微信群/朋友圈具有群組眾多、傳播速度快、波及范圍廣的特點,成為疫情信息傳播和接收的“第一渠道”。
疫情危機風險傳播的關鍵節點與傳播機制
(一)疫情危機風險傳播的發展階段
突發危機事件的生命周期理論中,Fink提出經典的四階段劃分方法,即潛伏期、爆發期、蔓延期和消散期。在此理論基礎上,本文分析了“知微數據”提供的從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15日與新冠疫情相關的新聞、微博和微信文章共1,851,142條,與全國確診病例進行對照,通過識別疫情信息數量變化的節點,同時對照關鍵事件,將此次疫情信息傳播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四個階段。
1.潛伏期(2019.12.30—2020.1.19)
2019年12月30日下午,微信群中開始流傳武漢衛健委關于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的內部通知;晚上出現“SARS冠狀病毒”的微信群截圖。12月31日下午,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第一份《情況通報》,成為疫情信息傳播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疫情危機風險傳播的潛伏期比較長,一方面與不明原因病毒的被認知過程有關,另一方面是對疫情信息傳播的人為干預,例如,2020年1月1日武漢市公安局公布對8名“造謠者”進行了處理。
2.爆發期(2020.1.20—2020.2.9)
此次疫情危機的引爆點來自于衛生醫學領域的專家和中央領導人的重視。2020年1月20日晚,國家衛建委高級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證實了“人傳人”,迅速引爆輿論。1月23日武漢市宣布“封城”,公眾的緊張情緒爆發。1月28日,最高法院發表文章為8名“傳謠者”進行正名,輿論“平反”達到最高峰。2月7日,“吹哨人”李文亮的去世成為一個情緒宣泄口,掀起又一輪輿論高峰,這也是疫情信息發展曲線的重要拐點。
3.蔓延期(2020.2.10—2020.2.29)
因為新冠疫情的嚴重性,危機風險傳播的蔓延期長且熱點頻出。2020年2月13日,湖北省主要領導進行調整,武漢單日確診病例過萬,引起公眾關注。2月26日,一名武漢確診女子刑滿釋放回到北京,引起網絡熱議,掀起一個次峰點。
4.消散期(2020.3.1—)
2020年3月1日之后,多省市連續多天新增零病例,陸續將疫情防控應急響應等級從原來的一級調整為二級。與此同時,國外包括意大利、伊朗、韓國、日本等進入疫情緊急狀態。3月10日,以中央領導人到武漢考察和方艙醫院休艙為標志,國內各地生產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復,主要關注防范境外對中國的疫情輸入風險。
(二)社交媒體在關鍵節點的核心作用與傳播機制
1.起點:疫情的“感知器”,形成原始信息“倒灌”主流媒體
全民化、移動化、社交化的社交媒體平臺具有龐大而細微的“感知觸角”,在第一時間捕捉到此次疫情的最早信息,其中微信群/朋友圈是原始信息源。
2019年12月30日晚上,“SARS冠狀病毒”的提醒信息在微信群傳播,其中三個主要群組是“武漢大學臨床04”“協和紅會神內”“腫瘤中心”微信群。當晚,微信群、豆瓣和微博開始討論。2019年12月31日上午10點,“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沖上微博熱搜,高居榜單一二名。之后,《第一財經》《新京報》《人民日報》、央視新聞等主流媒體進行關注和跟蹤報道。下午,武漢市衛健委發布關于疫情的情況通報。這樣,以微信群進行了人際群組傳播開始,經過社區討論和微博話題傳播,引發主流媒體大眾傳播,最終形成官方通報,社交媒體起到了疫情感知和監測預警的作用。
2.引爆點:風險信息的“放大站”,形成“轟動效應”影響大眾
2020年1月20日晚,鐘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視采訪時確認“人傳人”,這種風險信息是通過電視等主流媒體發出的,但社交媒體起到了重要的“信號放大”作用,并且因前面信息披露不透明等原因,潛伏醞釀期長,引爆點強,產生了“轟動效應”。
影響引爆點產生轟動效應的因素包括:(1)關鍵人物——鐘南山,作為受人尊敬的“意見領袖”發表有指導性言論,引領公眾和媒體看清事實真相,引導輿論走向;(2)重要內容——新冠病毒能人傳人,內容本身具有重要性,有激起大眾的情緒刺激,特別是恐懼;(3)社會環境——在類SARS傳染病爆發的背景下,鐘南山的講話“放大”或提高了對新冠病毒特定危害的風險認知。之前的研究表明,人們在接觸引發負面情緒的信息時,更傾向于進行人際交流。在社交媒體環境下,民眾通過評論、點贊、分享等行為來進行人際交流和群組傳播,引發轟動效應。
3.爆發點與峰點:與主流媒體互動共振,形成“信息瀑布”,引發高潮
社交媒體環境中存在不同觀點的群組和網絡社區,社交媒體全民化的高使用率,在一定程度促進了信息共享和觀點互動,有利于“信息瀑布”的形成。信息瀑布(informational cascades)最初在經濟學領域被提出,是指個人不依賴自己的私人信息,而是觀察并跟隨前人的行為進行行動。在武漢封城后的官方應對和對“造謠者”的反思中,公眾通過社交媒體平臺結成群組和交流信息,啟動了“信息瀑布”的形成過程。
“信息瀑布”通過兩種運作機制產生有現實沖擊力的“瀑流”。一是與原有媒體傳播體系互動,實現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和傳播擴散。傳統新聞的傳播擴散是層級化的“自上而下”,從政府機構開始,流經精英網絡到達媒體機構,形成新聞文本,最終抵達社會大眾。二是社交媒體的群組成員根據活躍程度可區分為活躍者、跟隨者和沉默者,之間關系的網絡化激活使動員人數急劇增多,使個人參與運動的成本降低,容易讓沉默者跨越“參與門檻”,通過話語或行動表達訴求。武漢宣布封城后幾十萬人緊急“出逃”,“雙黃連”風波引發民眾排隊搶購,都是“信息瀑布”網上激活、線下行動的例子。
4.拐點:社交媒體成為情緒宣泄口,帶來社會情緒“轉向”和多種聲音
2月7日凌晨,微博上多家官媒發布了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引發大量網民討論。截至2月7日凌晨6時,話題“李文亮醫生去世”有6.7億次閱讀,73.7萬次討論;截至2020年2月24日,該話題已有19.9億次閱讀,138.4萬次討論。
根據清博大數據的統計,自2020年2月6日至2020年2月12日,該話題共有相關信息510,596條,從社交媒體表現出的社會情緒來看,負面信息最多,占比44.03%,正面信息占比29.09%,情緒化傾向非常嚴重。
究其原因,是因為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上,群組化、交互性的傳播模式以及信息海嘯沖擊下的把關難度,為情緒化宣泄提供了便利。微信群、朋友圈的“圈群化”為情緒化傳遞提供了群組基礎,形成同質化的“回音室”,“閉環式”的群內傳播和“強關系”的人際傳播結合,帶來極端情緒的放大和增強。微博平臺上基于“弱關系”的粉絲群和基于內容聯系的話題社區,使網絡社群的聚集門檻大大降低,很容易發生規模龐大的網絡化“群體事件”,帶來嚴重的群體情緒化傾向。
社交媒體對突發公共衛生危機傳播的影響與啟示
(一)重視社交媒體的“吹哨”模式,監測預警突發公共衛生危機
此次新冠疫情的信息傳播充分顯示了突發公共衛生危機傳播的特性:在內容和強度上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危機傳播或突發事件,而是結合了突發事件、自然災難、緊急救援、高傳染性威脅、不確定的醫學科研發現等多重要素,塑造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未知風險和不穩定的傳播環境。在這種傳播環境下,以前階層化的“全知全能型”的傳統傳播體系很難發揮作用。
社交媒體的“吹哨”模式是公共衛生流行病監測和預警的重要來源。在國際公共衛生領域,傳統上國家治理的主流方式是“精算模式”:基于事件發生的準確信息進行精準化管理。最近幾年,在接連遭遇埃博拉、西尼羅河病毒、禽流感等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的情況下,強調警惕性和不可預測的“哨兵模式”被奉為準則:更多地停留在提醒重大事件的發生,并不負責提供專業性的操作指南。在此趨勢下,我們需要重視社交媒體具有的“哨兵”功能:需要在無法預測的疾病爆發初期迅速吹響“哨聲”,以寬容化的方式對待突發公共危機預警,李文亮等8位“吹哨者”已經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二)社交媒體傳播主體“業余化”,需構建新型網絡把關機制
社交媒體賦予普通民眾信息傳播和組織動員的能力,打破之前建立的傳統層級結構,形成“大規模業余化”,這一方面帶來傳播結構的解構:借助社交媒體,“草根化”的社會成員可以繞過傳統的“把關機制”,獲得獨立的信息發布和傳播渠道;另一方面,因為社交媒體傳播主體的業余,對信息的真實性把關不嚴,也容易帶來大量謠言的傳播。
傳統的新聞把關是通過專業的新聞采編及其相關管理機構進行,現在的網絡把關則包括三個層面的機制。一是通過大眾過濾、協作“眾包”的群組化把關,主要是基于關系的群體認同,發揮“群體效應”。從正面意義上,通過協作生成的“公民新聞”,成為專業媒體新聞的重要補充,使邊緣化的聲音可被聽見,并提供不同于主流媒體的另類敘事。但在小型群組內,容易形成觀點極化或情緒激化;傳播主體的“業余化”和直接的目標訴求,也容易帶來虛假新聞的泛濫;因為缺乏媒介素養,傳播動員也有可能變為惡意煽動。二是基于社交媒體平臺進行內容分享和粉絲關系建立,平臺數據和算法推薦形成“數字泵閥”,結合話題標簽、轉發/評論等技術工具形成“平臺效應”。社交媒體平臺實際掌握著數據內容和體系規則,在網絡把關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三是組織機構的媒體化傳播和把關,通過權威、專業和深度的內容形成“媒體效應”,設置議題框架。這三種把關機制的互動、博弈和融合,是未來構建新型網絡把關機制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