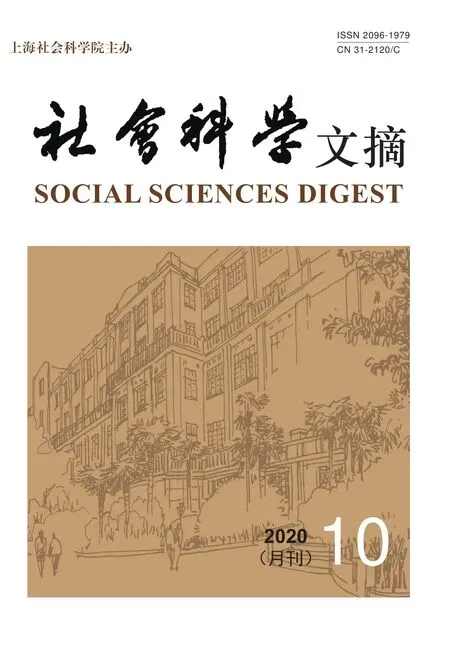超越公共行政案例研究中的“定量范式”
——與于文軒教授商榷
文/宋程成
近年來,隨著大量優秀案例研究作品被發表,國內公共行政學界對于其基本特點和應用狀況進行了一系列回顧,大多是從方法論要素以及中國獨特環境對案例研究應用前景的影響等角度來分析并形成辯論。然而,大部分上述文章都是從靜態標準角度來論述何為“好”的案例研究,未能清晰地呈現研究者應該如何在案例分析動態實踐中遵循相應的標準與原則。特別地,針對于文軒教授最新發表在《中國行政管理》上的《中國公共行政學案例研究:問題與挑戰》一文(下稱“于文”)中提及的一系列看法和建議,本文試圖在理解和把握其觀點背后相關學理依據的基礎上,開展一定程度的對話。
本文原則上同意于文對案例研究作用以及其與量化研究間關系的討論,并且無意就案例研究背后的哲學基礎或數理邏輯基礎進行論爭,亦無意反駁于文強調的案例研究信效度方面的各類經典看法,而是試圖重申和討論案例研究的“非量化”特點以及這一特點對研究起點、實證操作和相關發現的可能影響。
圍繞著上述目標,下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首先,從大部分案例研究重視實質性問題、側重依因變量選擇樣本的事實出發,討論在公共行政案例分析中引入量化研究的抽樣原則和因果識別機制的可能困境,以及這類做法對于案例研究在公共行政領域獨特比較優勢的潛在損害;其次,結合案例研究在操作上存在的“易學難精”問題,強調研究者必須特別重視數據的“三角測量”和數據呈現的“結構化”,并且在此基礎上有效地開展敘事性分析和盡量排除競爭性假設;再次,回顧案例研究探索和發現新概念的功能和價值,并提出了公共行政案例研究的概念創新應以機制發現為主要目標,據此強調案例研究的結論也具備一般化的潛力;最后,嘗試在引證兄弟學科案例研究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就開展本土化公共行政案例研究提出可能的“理想方案”。
公共行政案例研究的起點:實質的而非隨機的
首先,于文使用大量篇幅討論了從因果機制識別出發來進行案例研究不僅具有必要性,亦具有可能性,并且重點提出了案例研究要盡可能地避免選擇性偏差,以及在研究中遵循量化分析控制內生性問題的程序。于文偏重強調因果機制或因果效應識別的論點,雖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卻忽視了公共行政案例研究的重要基礎和起點——實質性問題及其非隨機分布性。
不少研究者由于受到社會科學方法論重要參考書目《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定性研究中的科學推理》的影響,趨于認為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本質上都是為了識別因果機制,其差別只是在材料意義上;而且,這兩種研究(方法)都是系統的乃至科學的。遵循上述看法,于文提出了不應該過分強調案例研究是質性研究,以及案例研究也可以混合或定量的相應判斷,這一思路就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的趨勢看,基本是合理的。必須指出的是,識別因果關系并且揭示其背后的機制,是社會科學家的基本共識之一。但是,如果太過強調特定強勢學科所規定的“因果機制”識別方案,會導致一部分既有現實意義又具備理論價值的案例研究被忽視或放棄。這是由于:
第一,從研究起點角度看,案例研究很難遵從嚴格的統計邏輯。從統計學邏輯看,為了合理識別特定的因果關系,抽樣必須是覆蓋“自變量”而非“因變量”。而按照我們一般意義的理解,案例研究往往源于有趣、特殊或者反常的社會現象,也即所謂的實質性問題(如中西“大分流”等)。因此,盡管于文強調的量化乃至混合研究的取向,與近年來其他學科中興起的研究范式有著相互呼應,但是在常識意義上,案例研究仍然被學術界認為是圍繞著小樣本(即Small N)的一種研究方法(論),這意味著基于事件時間線的基本敘事是案例分析的關鍵,而量化工具則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更加精確的控制—比較手段。故而,本文以為,不應該過分強調案例研究的“非質性”或“親量化”屬性。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說量化研究不需要有趣和重要的問題,而是說在研究設計過程中的樣本選擇階段,“因變量”和“自變量”在兩種方法(論)中存在著顯著的“優先序列”差異。
第二,進一步地,盡管有著比較案例以及過程追蹤(Process-tracing)等分析方法和手段,但由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本身的不可控因素過多和在因果機制上存在著的“多對一”難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案例研究的因果機制是需要研究者圍繞著時間軸來進行勾勒的。當然,有學者可以辯稱,盡量尋找可能的案例并且進行控制實驗,是合格的學術研究所必須重視的,而且隨著相應技術的進步和數據的完備,越來越多的比較案例是可以識別出單一、特定的重要因果機制的。但是,刻意去尋找自變量隨機分布的條件,往往會忽視案例研究自身獨有的優秀傳統。如果僅看到強勢學科的量化工具在方法論上的優勢,會導致案例研究出現一系列潛在的技術“模仿”風險而喪失其對現實的敏感性。
第三,在很多時候,案例研究并不具備開展一系列嚴格符合“政策效應評估”檢驗的條件,即案例研究本來就很難提供“純”的數據。多數時候,單案例研究只能在時間性這一單一維度上構建出差異,因此深入情境的敘事和盡可能多地思考不同類型的因果機制在案例現象中起到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就已經發生的事件而言,試圖借助自然實驗等思路來實現對潛在影響因素的控制會變得相當困難和不現實。但是,在現實公共生活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大量的改變整個行政體系或者行政行為的單一案例,這些情況卻又總是值得討論的,這是因為公共行政這個專業自身的學術取向迫使我們去深入探討這些案例。因此,必須重視案例研究的“因變量”自身或者“依因變量選擇”(Selecting on Dependent Variables)的基本屬性和特點。我們固然要在分析案例的過程中努力避免對于材料的選擇性使用(Cherry-picking),但是在研究最開始的起點選擇上,卻必須遵循案例研究那些經典作品所秉持的“因變量抽樣”原則。
案例研究的分析與操作:結構化而非形式化
其次,于文重點指出了基于歐洲傳統的批判式和建構主義案例分析缺乏進一步重復和實證的可能性,也提出了一些典型的信效度指標來規避“洞見大于檢驗”的風險;但是于文所列舉的案例分析并不是傳統意義的單案例研究,而是以量化分析為主體的一些經典文獻。一味在形式和程序上遵循定量研究在數據分析時的信效度原則,并且有選擇地忽視案例研究在數據分析和收集時的差異性,則可能會真正導致案例分析“嚴謹性”的喪失和研究結論的平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案例研究的可行性。
因此,盡管我們在原則上認同于文提及的大部分數據操作建議,但是當學者們特別是初學者遵照于文建議去著手相應的案例研究時,必然會感到困惑且無從下手。這是由于:一方面,初出茅廬的研究者難以形成有效的問題意識,即提出的問題存在現實意義不足等缺陷;另一方面,初學者不會很好地整合案例材料和理論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不同于量化分析有著非常嚴格的數理邏輯和軟件操作手冊,案例和質性研究雖然也有很優秀的指導作品或軟件,但初學者在模仿和利用教材過程中的“獲得感”和“熟練度”往往是差異巨大的。
可見,于文在樂觀地提及案例研究與定量研究的一致性時,忽略了案例研究或質性研究的關鍵特點——“易學難精”。從這個角度看,研究者必須在研究設計階段就充分意識到困難,而不是覺得案例研究的數據收集工作相對比較簡單。例如,如果要對中國政府部門或其工作人員進行研究,學者們不僅需要跨越“研究技巧”上的鴻溝,更需要跨越材料收集上的系統性難題。誠如于文所言,案例研究的材料應該足夠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必須是具有“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的特點,這不僅有助于學者建構案例故事的完整性和整體性,更有助于我們從不同角度判斷學者所提出的分析框架的內在一致性和其對因果機制的論述是否完備。
特別地,數據的三角驗證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研究者讓受訪者自身“溯因”(Abduction)的風險。當被問及為何需要從事某類實踐時,受訪者回答的“原因”(其實是“理由”)往往由于自我歸因或刻意隱瞞而不可信。由于各類因素限制,公共行政研究者面對的受訪者,可能多是有著豐富臨場經驗和應變能力的老練人物,其對于學者訪談目標的識別以及對問題政治敏感度的把控都相對較強,而這就會加大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因此,每一個嚴謹的公共行政案例研究者都不能把建構因果機制或者“分析敘事”(Analytical Narrative)的權力讓渡給研究對象,這既是一種方法上的“不達標”,更是智識上的“偷懶”。
在這個意義上,案例研究得以成功的關鍵是要有一定的“家法”或標準。例如,工商管理學界近年來興起了兩個優秀的案例研究學術傳統:一是以艾森哈特為代表的比較案例方案,二是以喬亞(D.Gioia)為代表的分析性敘述方案。這兩個學者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特別強調數據的“結構化”。但筆者以為,要重“結構化”但不能唯“結構化”,真正優秀的案例研究“重意不重形”,只要能夠將數據合理呈現并開展有效的比較分析,是否有相應的“一級概念”“二級概念”甚至“三級概念”并不重要。不同類型的案例研究者應該有自己的分析策略偏好,不要太拘泥于形式上的“相似度”。
確立與拓展案例研究的發現:一般性而非特殊性
再次,于文提及了案例研究中“分析性一般化”的作用和價值,并且重點論述了如何通過單案例分析來確立和拓展相應的結論。不過,于文在強調案例分析可推廣價值時,未能系統闡述案例研究“一般化”的產物,即學術概念以及其如何與現有理論進行合理對話等問題。換言之,由于傾向從定量研究統計法則角度來思考研究結論的“普適性”,于文未能就案例分析結論的一般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進行有效論述。
第一,理想的案例研究,其結論往往會得出一個讓人感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概念”。但是,案例研究的新創概念往往最為人詬病,這尤其以“概念拉升”(Conceptual Stretching)現象最為普遍。例如,學界當前最為流行的某些“定語+核心名詞”概念,在不少案例研究中已經完全失去了其本來的分析功能,甚至淪為了純粹的“標簽”。當然,這一問題幾乎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通病,不過,由于案例研究特別適合做探索性研究,這就更容易使學者有“新創概念”的沖動。簡單來說,不少概念創新都是偏重于思考案例的獨特性而忽視了其形成原因的普遍性。有分析認為,這是由于隨著國內學界逐步強調與海外學術界的理論對話,建構基于中國情境的概念以凸顯自身文章的理論洞見,成為了學者們最大的動力。
就公共行政領域而言,大量基于案例的概念創新多發生在現象(或者因變量)層面,即案例本身有趣、吸引人是研究者對其進行分析的重要原因。但這就會導致一種可能性,就是那些本來可能是同一個概念連續光譜上不同取值的點,被學者們強行通過概念建構而成為不同的類型。從這個角度看,于文提及的Hofstede文化指數模型的確存在著過分簡化和不符合一些地區實際等不足,但是這一概念又確實在一定可比較的維度上,告訴國人“中國情境”到底特殊在何處,這與歷史學家們關于中國文化到底有多少特殊的分析思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針對上述難題,本文嘗試提出一個可能的折中方案。事實上,在社會科學中還存在著機制或者原因的概念創新,例如“弱關系的力量”“集體行動的邏輯”等概念,本身對應著一個或幾個具體的機制,而且在現實社會中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因此,一個好的案例研究,或許應該嘗試從因變量出發思考問題,最后找到一個合適、獨特的因果機制,并對其進行命名。
第二,關于案例研究相關發現理論價值大小的判斷,筆者非常同意趙鼎新教授在其新著中提及的標準,即一個優秀案例研究(或質性研究)的解釋理論,應該是一個相對其他分析框架而言,可以解釋更多(因變量)的理論。這意味著,即使一項案例研究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如果其不能夠避免或者排除其他的分析框架,那么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案例研究是成立的,但是其理論價值卻是不完美的。而且,由于每一個學者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自身價值取向和理論偏好的影響,傾向在案例發現中證實而非證偽自己的理論觀點——在公共行政這樣特別強調實踐導向的學科中,學者過分強調理論貢獻的結果可能會引起政策和制度上的巨大偏差。本文特別且充分認同于文強調的混合研究乃至量化研究在案例分析中應用的建議,因為通過使用相對客觀的統計法則,經由個案歸納和演繹出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觀點,才有機會在比較中確立起自身真正的解釋力大小。
第三,案例研究的結論,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概述或者一般化?這在本質上與案例材料豐富性之間存在著矛盾。這是由于,隨著研究者掌握的案例材料越多,其解釋就越來越趨于一種特殊理論,由于社會機制的多樣性,到最后研究者會發現案例分析的結果是以復雜解釋復雜,而非一般經驗科學所希望的“簡約性”解釋。這一點,正如于文所提及的,在單案例研究中存在著巨大的爭議。不過,也正是單案例研究,提供給學者展示其研究水準的最佳機遇。同時,深入地梳理出案例演進的各類要素,在可以“復制”和“比較”的維度上,歸納特殊個案可能呈現的“一般性”標準,是案例研究一般化的前提。因此,并不是只有大樣本研究才可以形成一般化理論。
結論與討論
綜合上述,相比以往研究偏重分析公共行政領域案例研究需要遵循的一系列方法論要求,本文更加重視從研究者的視角來開展分析,以期彌合“靜態標準”和“動態運用”之間存在著的實踐鴻溝,進而化解案例研究從起點到發現的一系列操作難題。換言之,公共行政學者必須要在研究實踐中保證和堅持案例研究的“敘述邏輯”與“理論建構”等真正的比較優勢,避免呈現出對于強勢學科量化研究的“方法崇拜”而導致的自我矮化,進而失去了評判何為好的案例研究的學科“話語權”,這甚至最終會導致學科認同的一系列危機。在這個過程中,公共行政學者應該有意識地學習和借鑒同為專業學科但發展更早且共同體意識更加濃厚的工商管理學科的一系列經驗教訓。
最后,筆者特別同意于文認為的案例研究類似偵探小說的“隱喻”(Metaphor),亦認同其關于公開相關案例材料的倡議,這意味著案例研究也需要有一定的“可重復性”。有鑒于此,本文并不希望提供給讀者所謂的優秀案例研究操作“菜單”,而是試圖提出一種案例分析的可能“理想方案”:在研究過程中,合格的案例研究者應當像是“本格派”推理小說中的偵探一樣,在掌握與其他人相同的證據和信息的基礎上,最終通過完備的推理和合理的分析敘事將兇手定位出來(“解釋案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