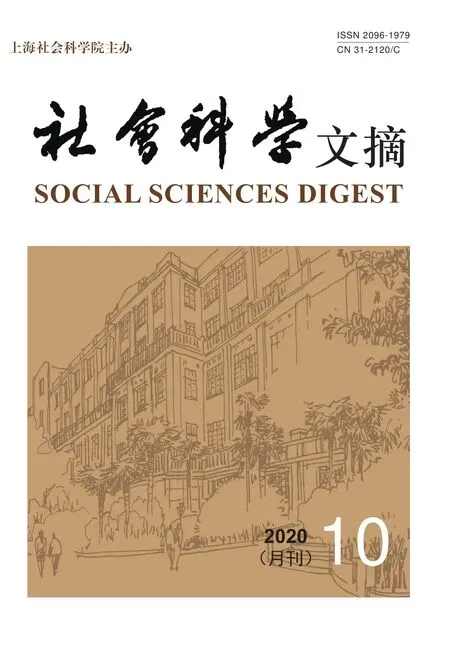不確定條件下社會信任的分化與協調
文/劉少杰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高度不確定狀態,只有清醒地承認這個基本事實,并清楚地認識其發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建立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新型社會信任,社會信任才能有真實的現實根基,社會生活才能在此起彼伏的不確定性中獲得聯系的紐帶和穩定的支撐。否則,人類規避風險、維護秩序和交往合作的意愿,都將成為泡影。
傳統社會信任確立的根基
所謂傳統社會信任,這里意指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確定性基礎上形成的社會信任,包括個體之間、群體之間、民族之間,以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廣泛意義上的信任關系。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中最重要或最基本的確定性是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中的確定性,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土地的不可移動性和機器運行的規律性和準確性。以土地為本的農業生產維持了老守田園、世代相繼的相對靜態的封閉社會;而具有統一規則、確定程序、明確標準和有效控制的機器生產線,要求以之為基礎的工業社會,是一個組織起來的按紀律、章程和法規運行的社會。這些都是明確的確定性,是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可以形成比較穩定的社會信任的可靠基礎。
說傳統社會具有較高程度的確定性,并非認為傳統社會就沒有威脅人類安全、帶來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從古至今威脅人類的不確定性,歸根結底是社會的屬性。嚴格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是不可預測、可能帶來風險的變化。自然界有變化,但沒有不可預測的不確定性。一定時期的自然不確定性,其實質是人類對之認識的局限所致。因為自然現象都有其客觀本質和變化規律,人類一旦認識了自然現象的本質規律,再復雜的自然現象也會轉變為可預測的確定性。社會生活則不然,無論哪個領域的社會生活,都會在人的意志支配下發生著不斷改變的重新選擇,因此,社會生活具有難以預測甚至無法預測的本質屬性。
社會生活這一本質屬性根源于人類的意識自覺性或主體能動性。盡管這并不是太復雜的道理,并且大部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都承認這個事實,可是,名目繁多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幾乎都做出了要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變化客觀規律的承諾,亦即都要幫助人類把握社會生活的確定性。不能僅僅指責人文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的效仿,更重要的是在社會生活中也確實能夠發現很多相對穩定的確定性,并因其客觀本質的規定而呈現出演變的規律性。然而,在社會生活中發現的相對確定性,其實質不是來自人類自身的品質和能力,而是源自自然界的本質規定。
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的是:社會生活的確定性根植于自然界的客觀本質和運行規律,而不確定性則根植于人類的意識自覺性和主體能動性。并且,確定性的程度與同自然界的聯系程度成正比,而不確定性的程度則與同自然界的聯系程度成反比;或者說,確定性的程度同人類的意識自覺性和主體能動性成反比,而不確定性的程度同人類意識的自覺性和主體能動性成正比。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的結論是:傳統社會信任的根基在于自然界的客觀本質和外在規律,物質生產或社會生活其他領域中的相對確定性,也是自然的客觀本質和運行規律使然。
網絡信息社會的不確定性
正像盧曼論述的那樣,在熟悉關系的傳統社會,人們形成了建立在重復性、簡單性的確定性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到了陌生的現代社會,熟悉社會的確定性遭遇了流動、變化和陌生的不確定性的沖擊,必須為信任在不確定性中找到一種新的確定性。而這種確定性即規則、紀律和制度的系統確定性,熟悉信任轉變成了系統信任。盧曼論述的系統確定性是以機器生產為根基的,即機器生產是工業社會的基礎,以之為基礎的系統信任也就有了自己的可靠根據。
然而,這里面臨的問題是,機器生產已經不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力,其展開的生產關系或其支持的經濟基礎也在網絡信息化中發生了改變。更為重要的是,維持著機器生產有序運行和工業社會穩定發展的那套體現著機器運行要求的規則、紀律和制度,其確定性的功能也遭遇了嚴重的沖擊,以之為根據的系統信任也隨之動搖甚至遭遇激烈沖擊。
人類的社會實踐或社會生活都是依據某種信息展開的,在信息匱乏或信息有限供應的條件下,人們通常可以明確地鑒別和利用信息,信息因此而成為人們掌握確定性并形成信任的根據。可是,在網絡信息化條件下,信息供應的匱乏狀態已經改變,人們面臨的問題不是獲得更多信息,而是如何有效地鑒別和選擇信息。當信息經由移動通信和互聯網隨時隨地潮水般涌來時,海量信息供應帶來的已經不是對確定性的認識,而是難以鑒別和難以選擇的不確定性困惑。
特別是在一定的時間段中,不斷更新、前后矛盾甚至對立沖突的信息供應,不僅不是對行為和思維的有效引導與支持,還對行為和思維帶來了嚴重的干擾和激烈的沖擊。與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相比,網絡信息化社會的最突出且具有普遍性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在網絡信息社會人們無法回避不確定性,不確定狀態已經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
網絡信息化以其無所不入的能力,已經把物質生產的大部分領域都納入其中,于是傳統社會的那些確定性在網絡信息化的作用下,或者出現了松動,不那么確定了,或者直接轉變為不確定性。至于通過互聯網和智能通信運行的網絡信息空間(賽博空間),就更是一個超越地方空間邊界、信息可以在其中極速傳播、即時交流和廣泛傳遞的流動空間。網絡信息空間是一個生生不已、瞬息萬變的空間,在其中活動的各類媒體,無論是國內外的知名網站,機構團體的公眾號,還是形形色色的APP,個人的微博、微信、抖音等,難以列數的網絡設置,都爭先恐后地變換著自己內容與形式,傳遞著引人注目的新消息、新視頻。
由于變化是網絡信息空間的生命能量和制勝根本,因此,無論何種網絡設置,變化得越快,吸引力越大,生命力越強,則其影響和能量也越大。而那些稍顯遲鈍、變化較少的網站或網頁,就會很快地被擠向后排,直至變為“僵尸”而無人問津。因此,網絡信息空間是一個不斷變化、充滿不確定性的空間。網絡信息空間不是僅在互聯網線上展開的賽博空間,還包括利用網絡信息技術交流串聯起來的線下空間。凡是通過互聯網連接起來的企業、機構、群體和個體,也屬于進入網絡信息空間活動的主體,他們活動的范圍和內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網絡信息化的影響。在諸多影響中,最明顯的莫過于活躍程度提高和不確定性增強。
不確定性空間中社會信任的分化
已經進入互聯網的社會成員,他們對網絡信息社會的不確定性的認識,不僅是積極的,在不同程度上還形成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社會信任,這支持或推進他們開展了更有效率的社會實踐。相反,那些遠離網絡信息化活動,對網絡社會還比較陌生的社會成員,他們延續著傳統社會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對他人、對群體以及對政府、對國家的信任建立在熟悉關系和制度關系基礎之上,用熟悉信任或系統信任支持著選擇行為、社會參與和交往合作。
雖然這些同網絡社會還有一定距離的社會成員也能感受到網絡信息化時代的不確定性變化,但他們對不確定性的理解和態度,同已經進入網絡社會之中的社會成員一定有很大差別。一方面,這些遠離網絡信息社會的社會成員,把身體不在其中、面目不呈現出來甚至大量的表達與溝通還是匿名或半匿名的網絡活動,看成是虛擬的、不真實、不可靠的。他們對網絡信息、網絡營銷、網絡購物等都心存疑慮,唯恐上當,不愿參與,而是堅持認為,只有書刊文件、商場選購、現場購物才是真實而可靠的。另一方面,以熟悉關系和制度規則等確定性為基礎的信任,在遠離網絡信息社會的社會成員中是根深蒂固的,他們對網絡信息社會的不確定性感受到的越多,對傳統社會依賴客觀自然或物質關系的信任視角、信任原則和信任模式,越是堅定不移。
與此相反,那些深入參與網絡信息社會的社會成員,在海量信息迅速更新且不斷沖擊下,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不確定性已經是社會生活的日常狀態和發展趨勢,在動蕩不定的社會現實中,以熟悉關系和制度原則為基礎而形成的信任,不僅失去了往日的效力,而且也很難在快速變化的網絡信息化社會中找到其存在的根基。盡管不確定性是難以駕馭的社會現象,但這已經是不可回避的普遍現實,只有在不確定性基礎上結成新的信任,才能在網絡信息社會形成合作、規避風險。最復雜的是,還有一些社會成員,一方面進入了網絡信息化社會,對其中的大量不確定現象也有所了解,另一方面還受到在工業社會甚至農業社會形成的思想觀念的束縛,還是以熟悉關系和制度體系為基礎形成信任和展開信任。
進一步說,雖然這些人接觸或看到了網絡信息社會的不確定性,但他們并不是實事求是地順應現實的變化,在不確定性基礎上探尋新的社會信任,而是用舊的信任原則來認識或對待新的信任基礎和形成信任的可能性。作為一般社會成員,如果他們既進入了網絡信息社會又沒有實現思想觀念上的轉變,還是用傳統的熟悉信任或制度信任規定著自己的信任行為,導致的結果是他們的信任同已經深刻變化的現實難以相容,以致他們會感到網絡社會的不確定性使自己進入了一個變動不居、難以信任的世界之中,高風險狀態使他們產生持續的懷疑主義,其行為和思維可能會瞻前顧后、旁顧左右,做事會猶豫不決,唯恐上當受騙。這些人看不清網絡信息社會的本質特征和遠大前程,在網絡信息活動中表現出很大的盲目性。
令人擔憂的是那些掌握著某種資源或支配能力的人,如果他們堅持用傳統社會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支配手段,去行使手中的權力、支配自己掌握的資源,他們就會產生阻擋網絡信息化社會向前發展的消極作用。用傳統的原則去面對網絡信息社會,也可能利用傳統社會的原則給千變萬化的網絡信息社會帶來一些趨向穩定性的限制,但更多的情況是,畢竟傳統社會的確定性同網絡信息社會的不確定性不僅存在性質上的區別,而且是不同條件、不同時代的產物,這種不合時宜的做法,帶來的更多的是對網絡信息化社會的傷害。
網絡信息化的不確定條件下也會生成一種新的信任,即網絡信任。這是一種基于網絡信息交流而形成的新型信任,其特點是:首先,它是憑借計算機、移動通信設備和互聯網等新媒體,以對網絡信息的接受、鑒別和認同為基礎形成的信任,這是其最根本的屬性;其次,因為網絡信息是海量而迅速變化的,以這種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網絡信任也一定要隨接收信息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這是網絡信任最突出的特點;再次,不僅網絡信息是千差萬別的,而且網絡行為主體也是具有鮮明的個性差異的,這就表明網絡信任一定是多樣化、差異化的信任。還有,網絡信任要在網絡主體的對話和交流中生成與維持,并且,對話應當是真誠的,交流應當是平等的。沒有對話交流,不僅網絡信任不能生成,而且即便已經形成了某種網絡信任,也會隨對話交流的中斷而瓦解或崩潰。
網絡信任的誕生,是不確定性條件下社會信任分化最有意義的現象,并且,網絡信任的出現不僅僅是社會信任的分化,同時也是新生事物的誕生。雖然網絡社會已經生成了大量的這種建立在不確定性基礎上的新型信任,但因為其出現的時間較短,無論是社會成員還是網絡社會的研究者,對其觀察和研究的深入程度還十分有限。這些從傳統眼光看來莫名其妙甚至是心理變態的網絡行為,其中包含了我們還未解釋清楚的網絡信任。至于在一些成千上萬人卷入其中的網絡群體事件中,對其即時的不斷變化的信任關系,信任生成和變化的根據,信任表現的形式和形成的后果,都缺乏像關于熟悉信任和系統信任那樣深入的研究。
社會信任多元化的矛盾與協調
社會信任的多元分化并非始于網絡信息社會,在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也存在不同根據的信任:工業社會存在熟悉信任和系統信任;農業社會最普遍的信任是熟悉信任,但也存在對封建制度和封建體制的信任。不過,自網絡社會崛起之后,多元信任之間的關系也開始發生變化。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都以明確的地理邊界把村莊和集市、工廠和農田劃分開了,雖然也有酒館、廟會、咖啡廳和俱樂部等公共空間,各種不同的信任關系也會在這些公共空間中相遇和碰撞,但同互聯網和移動通信展開的公共空間相比,無論是展開的廣度還是活躍的程度,都存在明顯差距。當然,也正是因為在公共空間的范圍廣度和活躍程度上的差別,不同信任的相互關系也大不相同。
在傳統社會,不同信任的持有者,可以因為地方空間的邊界限制而各執己見、互不相干。但在網絡信息社會崛起之后則不然,快速而便捷的移動通信和不斷變換形式的網絡設置,可以使身居不同場所的人們方便地把自己的贊成和信任在網絡交流中表達出來,并且通過這些表達而連接成一個廣闊的公共空間,千差萬別的社會信任在公共空間中交匯。社會信任包含了價值認同、安全寄托和情感依賴,當這些具有不同傾向的價值觀、安全感和情感依賴匯集到可以即時交流、廣泛溝通的網絡公共空間之后,雖然會發生視界融合與觀點共識,但因其豐富的差異性和不斷的變動性,分歧和排斥也在所難免,各種矛盾也一定會隨之生成。
過去幾十年人們曾為之興奮的全球化浪潮,遭遇了狹隘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宗教激進主義、經濟保護主義的強烈沖擊,曾經支持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或不同群體之間開展交流往來與互助合作的社會信任,出現了動搖甚至瓦解。特別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來,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和黨派之間的信任關系也面臨了更加嚴重的沖擊,不僅網絡信任難以形成,傳統社會的熟悉信任和系統信任也呈現了更加嚴重的危機。原來已經形成了熟悉關系的信任或許頃刻間變為反目相對,曾經得到擁護和執行的制度體系,也會因為權力意志的改變而輕易地被撕毀拋棄。
社會信任的分化已經發生于人類社會的各種領域,不僅在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和黨派之間,而且在個體之間、群體之間和階層之間,社會信任都在發生分化。如何清楚認識網絡信息化條件下社會信任出現的嚴重而普遍的分化?怎樣才能找到一種重建社會信任的途徑與方式?這已經是擺在人類面前不可回避的時代課題。雖然社會信任的分裂與重建,都是十分復雜的問題,特別是社會信任同各種層面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和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時,問題就更為復雜,形成正確認識和找到有效協調途徑就更加艱難。然而,無論怎樣艱難,社會信任的分化原因和協調途徑,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