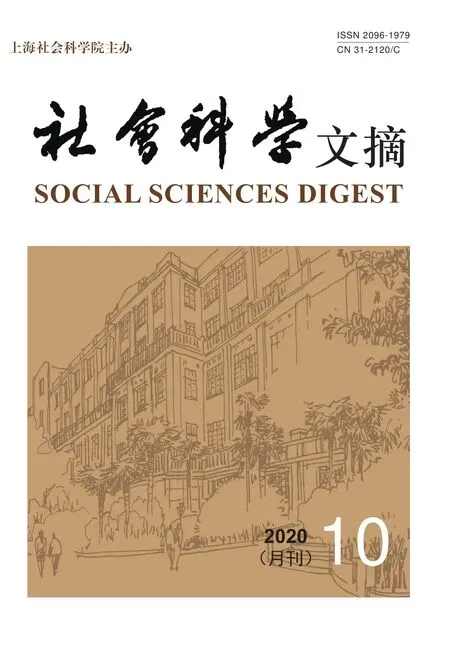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對“人的文學”的再思考
文/李春雨
文學是人學,這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文學的本質是寫人、寫人與自然的關系、寫人與社會的關系,這也不是一個新的結論。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雖然從根本上改變甚至顛覆了以往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但是它改變不了文學寫人的這個本質。在書寫人在重大變動下的生存方面,文學從未缺席,也無法缺席,這既是文學關注人的命運的天然本性,也是文學對時代社會肩負的重要使命。這一點,歷史已經多次證明,現實也正在證明,未來還將繼續證明。從“文以載道”到“人的文學”,從“人的文學”到“時代的文學”,從“人”到“人類”的升華,這些命題貫穿了幾千年來中國文學對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與關注。
從“文以載道”到“人的文學”
“五四”以來,百年中國文學的根本主題就是“人的文學”,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主題是在“五四”新文化對幾千年來“文以載道”傳統的質疑中誕生的,這是“人的文學”命題得以出現的一個歷史邏輯。“人的文學”是否意味著對文學載道傳統的徹底揚棄?我們有必要對文以載道和人的文學都作一點重新的辨析。
第一,文以載道,載的是什么“道”?孔子所謂的“興觀群怨”,柳宗元倡導的“文以明道”,韓愈踐行的“文以貫道”,周敦頤推崇的“文以載道”,雖然各自所指之“道”不盡相同,但根本上強調的是中國文學與生俱來的一種傳統:文學不僅是審美、藝術上的追求,而且必須承載思想層面的價值、理念,它既可以是對社會、國家的批判,也可以是對民族命運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看,“文以載道”其實反映的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學和文化關注現實、關懷天下的一種文化自覺,而絕不僅僅是哪一個具體朝代、哪一種具體制度下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理念。簡單地把“文以載道”理解為某一種政治理念、倫理制度的“文學工具論”,是非常狹隘的。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長河里,我們很少能找到哪一部著作是“純藝術”的,它們背后都要有所載之“道”。
第二,“五四”新文化反對“文以載道”,是反對文學的“載道”功能,還是反對傳統文學所載之“道”?“五四”的現代化轉型是在反傳統的語境下拉開大幕的,作為古典文學核心命題的“載道”自然當仁不讓地成為新文化運動者攻擊的靶子。但這并不意味著“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就是反對載道的文學,恰恰相反,新文學不僅不反對“載道”,反而充分利用起文學的“載道功能”,用來載“啟蒙”之道,用文學喚醒民眾的覺醒,這種使命意識本身就是對“文以載道”的延續。這事實上也意味著“五四”新文學反對的是以一種“道”規范、鉗制所有的文學,而不是反對文學的載道功能。
第三,“人的文學”,“人”到底指什么?“五四”是從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學自然發展而來的,更是世界性文化及文學相互滲透、撞擊和融合的結果。這意味著魯迅的“立人”、陳獨秀筆下“最后覺悟之覺悟”的國民想象、李大釗想要再造的“青春之我”、胡適心目中的“新人格”、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實際上都是西方文明與傳統文化、個人覺醒與社會批判結合的產物。在筆者看來,這些提法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它們都是對新文學主體的現代化想象,所涵蓋的內容大致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層面,個人之人。在“五四”發起之時,想要沖破封建禮教的壓制,就不得不依靠個性解放來張揚個人的價值。我們今天確實也能看到“五四”時期所留下的很多“個人化”的書寫,比如郭沫若的新詩創作熱烈地追求著個性解放,是一種火山噴發式的情感張揚,《天狗》每一行都以“我”開頭,僅僅29行詩歌中出現了39個“我”字。這種對自我的崇尚和對自我力量的認可,是幾千年文學沒有出現過的嶄新面貌。
第二層面,自然之人。在《人的文學》中,周作人對“人”的定義“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顱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在這里,周作人的觀點其實包含了兩個要點:一是“從動物”進化的,二是從動物“進化”的。這其實也是“五四”新文化的一個重要邏輯:只有對自然、生命本身的高度推崇,個體之人才能夠存在。
第三層面,社會之人。個體覺醒是“人的文學”的出發點,但不是落腳點,“五四”確實因為西方文藝影響,對傳統文學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反撥,但這并不意味著“五四”是一場“個人化”的運動。郭沫若看起來是那樣地浪漫抒情,但他也有《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樣高度清醒理性的政論文章;郁達夫再如何私語,如何個人,他也有《廣州事情》這樣犀利的社會批判。高度浪漫,高度關注個性,但又高度關注現實,高度回歸社會性,這兩點的融合才是“五四”最大的特點。
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作為“五四”新文學的重要標志,在張揚人的個性、文學的解放方面具有長久深遠的意義和影響。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是否全面、準確?這是值得反思的。一方面從事實上看,周作人所謂的“人的文學”,從來都不是只強調個人性張揚、人性解放的文學,它是一個包含了個人性、自然性和社會性的復雜思想體系,是從“自然”生命里發現“個人”,從“個人”覺醒達成“社會”的啟蒙的邏輯命題;另一方面從理論上看,“人的文學”的概念也不應該被狹隘到僅僅對“個人性”的理解。從歷史到“五四”再到今天,“人的文學”的概念從來都不只是個人性的突顯,而是個人性、自然性與社會性三個層面的共同融合,這才是“五四”留給我們的真正偉大而深刻的命題。今天看來,新文學確實以不同于傳統文學的全新面貌橫空出世,但這種“新”依然是相對性的,它并沒有改變中國自古以來文學的根本本質,那就是文學不可能離開社會性、不可能離開時代性、更不能離開人和人類而存在,其實這一點到今天也沒有改變,將來也不可能改變。
從“人的文學”到“時代的文學”
如果說“五四”初期更多是在理論上建構了一個“人的文學”,那么“五四”以來的一百年歷史進程則用實踐來證明:人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可能依靠抽象的人性解放,只有融入時代和社會的發展中才能得以實現。
體現在文學創作上,一個最集中的表現就在于災難敘事的頻繁出現。丁玲的《水》、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荒煤的《災難中的人群》、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葉紫的《豐收》等,都貫穿著一個共同的主題——災害。有的是旱災,有的是水災,有的是明明豐收了卻還是迎來破產的“豐收成災”。為什么這些作家執著地寫這樣一個題材?寫災難是為了寫災難背后的人禍,只有在極端的情景下,人與人的關系才能得到更為真實的暴露,這是一種時代的文學,更是一種高層次的“人的文學”。茅盾在成為著名小說家之前,更是一位批評家和理論家,他能夠在1933年就創作出《子夜》這樣的現實主義巨著,就得益于他長期在文學理論上的積累和沉淀。但這樣一位精益求精的理論家和批判家,卻在自己的創作生涯中留下了很多“未完成”的創作殘篇。《虹》《第一階段的故事》《霜葉紅于二月花》《鍛煉》等作品都沒有完成茅盾最初的構想,在主題和情節上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就匆匆結尾。何以至此?茅盾過于想把握時代的脈搏,反映社會的主題,因此他需要長篇小說的體量來容納時代的方方面面,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風云突變的局勢下,長篇小說顯然又不具備能夠時刻貼近時代脈搏的靈活度。茅盾焦慮地想要用文學反映時代、記錄時代、解剖社會,但又無力真正地掌控,這難道不是那個時代里更加真實的“人的文學”嗎?
進入新時期之后的文學依然如此,作家以空前的熱忱關注個體在時代面前的迷茫、反思和追尋,這既是對個人的關注,也是對時代的一種反饋和回音。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說起來寫法并無多大的獨特之處,卻為何能在當時產生震撼效應,并直到今天依然擁有大量的讀者?就是因為作家對現實的熱切關注,他站在同時代人中間,卻有著比普通人更為深切的感知和更為清醒的理智,因而作品直接戳中了時代的痛點,引發了千千萬萬個“人”的共鳴。余華也是如此。余華的創作有三個突出的特點:第一,他尤其擅長直面人生悲苦的一面,在人性最柔弱的地方扎上一刀,把痛苦作為人生的“常態”來描寫;第二,他又始終把這種悲苦緊扣在時代社會變革的節點上加以表現;第三,他總是力圖通過對個人不幸的思考達到對人類命運的理解。從《活著》到《許三觀賣血記》,余華寫的既是一個人的苦難史,也是一個時代的苦難史。福貴的命運其實是經歷了國共內戰、土改、“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的那一代人苦難的濃縮。許三觀一生靠賣血度過了很多難關。我們發現,小說寫的是許三觀一次又一次賣血,但其背后都是鮮明的時代、社會印記。余華的作品里有不少夸張、戲謔的東西,但更多的是真實的、現實的東西,這些糅合在一起,構成了余華作品的根本特質,即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的互為表里,互為因果。莫言常常被稱為“中國的福克納”或“中國的馬爾克斯”,他自己也并不回避對這兩位作家的學習和借鑒。但是莫言作品的根本生命力,是在中國的土地中自然生長起來的,莫言之所以能夠真正地走進世界的視野,并不是在于他魔幻的表現手法,更不是他迎合了西方的審美,而是在于他在作品里描寫的依然是中國人在一個世紀以來所經受的生活、精神的變遷與苦難,這才是莫言作品根本的精神資源。
當下中國正經歷著一場深刻而劇烈的社會轉型,我們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迎來經濟、社會、政治、哲學、道德等眾多方面的迅速發展。回望歷史,唐宋元明清雖然也有著時代內部的更迭,但總體來看,它們更像是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內核影響著我們,但是“五四”以來的這一百年,工業革命、商業革命、智能時代,人類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人的精神日新月異。尤其是最近這些年,從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迅速地變成了現實,人類的命運從來沒像今天這樣與時代如此緊密地聯系起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人與時代的關系會更加密切,這種密切不是簡單的相加、綁定,而是在更高的層面達成融合和升華。
從“人”到“人類”的文學升華
人和人類這兩個詞看上去相差很大,當我們面對人的時候,往往會想起自己,但當面對人類的時候,卻往往覺得這個詞離自己很遠。但實際上,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從歷史到當下,無數的文學經典都生動地演示了這一點。
歷史曾經告訴我們,個人與人類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回顧歷史經典,個人命運與人類命運的休戚與共就是一個永恒不衰的話題。個人與千百萬人的命運相牽連,這一點最集中地體現在了戰爭、瘟疫等重大災難降臨之時。這些災難的爆發,就像一個個即時炸彈,迅速地中斷每一個人的正常生活,并把各種不同的人生拉入一個共同的命運漩渦。小說《鼠疫》深刻地表明了想要避免瘟疫,不過是人類的美好愿望罷了。《鼠疫》繼承了加繆創作一貫的主題,即世界的“荒誕”,以及人對“荒誕”的反抗。所不同的是,小說中面對來勢洶洶的鼠疫,個人的反抗已無力回天,人人團結、直面災難、共同反抗才獲得了最終勝利。在這部小說里,加繆對“反抗”的呈現,其重點已由個體的反抗上升為更有廣度、更有力度的人類行動。醫生、記者、政府職員、病患,這些平凡的普通人面對災難時突破自我,從狹隘、利己走向崇高,所表現出的強大生命力值得贊頌。《鼠疫》出版于1947年,小說中所描繪的情景,卻與當下由新冠疫情帶來的世界性災難有著驚人的相似。只要稍稍回顧一下人類歷史進程,就會發現實際上自然界早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類發出了警告。在全球化越來越成為趨向的當下,面對大自然給我們的挑戰,沒有一個人可以獨善其身,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明哲保身,整個人類的安全和利益都已緊緊地纏繞在一起,綁定在一起。
現實正在提醒我們,個人與人類依然是水乳交融的。全球化、世界化加速的不僅是科技的共享、經濟的合作,更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相互依存。“核威脅”是科技的悲劇,更是人為的災難,它潛伏于人們生活中,隨時可能給整個人類帶來毀滅性打擊。2013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推出長篇小說新作《晚年樣式集》,在2011年發生的“3·11”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核泄漏事件之后,再次表達了對人類潛在的“核危機”的深切關注。大江健三郎一直走在“反核”“反戰”作家的前列,在他半個多世紀的寫作生涯中,曾連續出版了《廣島札記》《沖繩札記》等具有轟動效應的紀實性隨筆作品,并多次在“反核”集會上發表演講,而在《晚年樣式集》中,他又將福島與廣島、沖繩因為同一個問題而聯系在一起。這些直面“核威脅”的作品,都在思考著同一個問題:人類該如何避免核災難的重演?當災難從歷史事件變成正在生活中上演的現實,我們也逐漸變成歷史的見證者,成為災難攻擊下的世界的一部分。現實已經一再用傷痛警醒我們,人類永遠不要試圖因為現代科技的發達、文明的發展而漠視自然,凌駕自然之上,否則承受痛苦的必將是人類自身。
未來同樣警示著我們,個人與人類永遠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當面對著更加不可知的未來世界,作家關心的更不僅僅是個人的命運,而充滿著對人類整體命運何去何從的思考。當我們去看待這一類描繪未來、想象未來的作品時,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就出現了:作家對未來的想象似乎總圍繞“世界末日”“人類絕境”“種族滅亡”這樣的話題。拿科幻小說來看,劉慈欣的《三體》寫的就是當面臨著更加高級的三體文明,人類應該如何生存?《流浪地球》更是直接描寫了太陽毀滅之后,人類帶著地球一起流浪的故事。在這樣的作品當中,已經不存在個人式的英雄,甚至也不存在民族的英雄,不同國家組成聯合政府,共同應對著未來世界的巨大挑戰。只有這樣的文學想象,才能觸發一些關于人類共同體的根本性思考。科幻之所以成“文學”而不是科普,就是因為這種未來想象與現實生活的勾連,因為這種宏觀世界朝向微觀生命的關懷與思考。
眼下這場全球范圍的疫情,生動而深刻地突顯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大意義。人類從未像今天這樣意識到“人”自身的根本價值,意識到人與人類密不可分的、休戚與共的依存關系。在疫情面前,科學的治療、政策的規約等是十分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還有人的精神健康、心智的健全和思想的成熟。人類不僅在“常態”下生存,也會遇到類似疫情這樣的“非常態”狀況,如何在復雜的狀態下生活與發展,這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文學無可替代的主題與責任。越是在復雜和困難的狀況下,文學越是應該在場,必須在場,這是中國文學已經延續了數千年并將不斷延續的悠久傳統和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