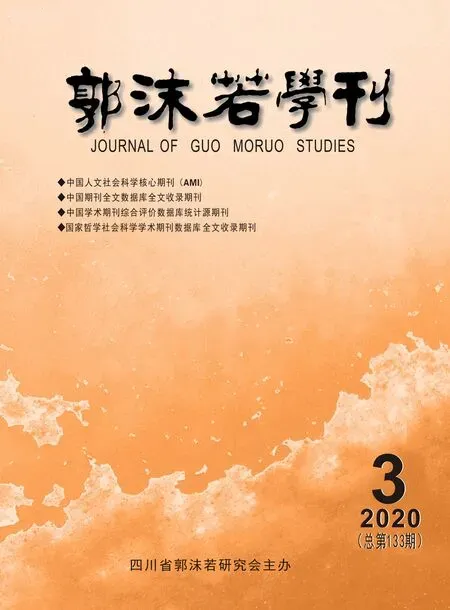郭沫若與老舍關于“蘭亭論辯”的互動
——兼說對論辯發言者評價的新向度
劉 銳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1965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第6期上發表了《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以下簡稱“郭文”)一文,由此引發了一場在20世紀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的書法論辯,甚至有學者說,這場論辯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全社會意義,其規模、規格、層次和深度均使它成為整個書法史上絕無僅有的重要事件和震動整個社會,尤其是文化界的奇觀。”①周俊杰:《20世紀中國書法通論》,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4月,第141頁。郭文的主旨,即根據南京新出土的東晉《王興之夫婦墓志》與《謝鯤墓志》,并承襲清代李文田的觀點,認為東晉的書體應該是隸書體,由此判定王羲之《蘭亭序》為偽作。同年7月23日,《光明日報》刊出了高二適《〈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以下簡稱“高文”)一文,對郭文進行了辯駁,以論《蘭亭序》之真。自此圍繞“蘭亭真偽”,展開了一場大論辯。此后隨著各種資料不斷公開,學界對“蘭亭論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總體上來講對這次論辯的背景的認識也趨于清晰,即郭文中提到過康生、陳伯達,在文中包含了二人的觀點,而高文則指名道姓加以批駁,高氏最初投稿遭退,則轉求乃師章士釗舉薦而得以發表,最終是得到了毛澤東的“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的指示,論辯得以展開。對于郭文背后的康生、陳伯達而言,這尤其是不愿看到的結果,為了維護郭文和他們自己的權威,便組織相關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繼續辯偽,對郭文加以支持。從1973年結集出版的論文集《蘭亭論辯》②《蘭亭論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來看,“上編”為支持郭文的“辯偽”一派,作者除郭沫若外,還包括宗白華、啟功、徐森玉、趙萬里、史樹青等人,共收文15篇,具有壓倒性優勢,而“下篇”為“論真”一派,僅收高二適等三人的文章,以數量之多寡暗示學理之是非。
以上是關于“蘭亭論辯”的基本情況,但若說僅此便可稱之為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全社會意義”,是規模很大而“震動整個社會”的一場論辯,好像具體材料還不夠豐富。很明顯,此前研究者更多是以論文集《蘭亭論辯》為中心,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公開的事件而言,實際上的參與者很少,或者說真正在臺面上參與論爭并被加以聚焦的僅十余人,似乎一直以來,對《蘭亭論辯》論文集之外的此事件的發言者,我們都鮮有關注。當然,筆者無意于否定上述學界對“蘭亭論辯”的基本認識,只是覺得要進一步擴充相關材料,對作為“事件”的“蘭亭論辯”的外圍做進一步觀察,如此才能真正體現這次論辯深、廣、大的社會意義。正如有研究者提到的,一些有力的辯駁文章“由于未發表在國家重點刊物《光明日報》、《文物》雜志上,影響不大,以至形成了以《文物》和《光明日報》為平臺,以高二適與郭沫若為主辯手的論戰”,①徐利民:《傳統文士風骨的現代典范——高二適在“蘭亭論辯”中的角色意義》,《中國書法》,2015年第12期。也有研究者認為,“從參加這場爭論的反對者一方來看,腹誹之人不少,但實際參加者不多,大概知道該問題牽扯到重量級政治人物,都不敢輕舉妄動”。②賈振勇:《郭沫若與撲朔迷離的“蘭亭論辯”》,《郭沫若學刊》,2010年第2期。也就是說,要談論“蘭亭論辯”深廣的社會影響,只是聚焦臺面上的論辯是不夠的,還要關注出于臺面之下的或者說局外人的態度或言論,并借此來展示“蘭亭論辯”的社會影響和其復雜性。筆者就曾以沈從文為例,考察過一個作為遠離論辯中心,甚至沒有發言資格的“邊緣人物”對“蘭亭論辯”的態度,并由此引發的其關于相關書法問題的不懈思考與追索。而且,沈從文就是一個典型的“腹誹”者,他只能將“蘭亭論辯”的態度,以零散的文字悄悄嵌藏在自己未刊的文稿中。③劉銳:《沈從文三首論書長詩新證——兼說沈從文的“蘭亭論辯”》,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所:《沈從文研究》第2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20年。
其實,除了臺面上的兩派人,以及遠離臺面的腹誹者,還應該關注到郭沫若身邊的交游圈中的人對“蘭亭論辯”的態度,因為他們既沒有上臺發聲,也未遠離論爭的中心,所處位置相對微妙,但又并未被卷入局中,了解這些局外人的“蘭亭論辯”,我們也可以多一個對“蘭亭論辯”的觀察角度。可以說,老舍就是這樣一位“局外人”,通過老舍與郭沫若以及“蘭亭論辯”的關系,似乎可以豐富對此事件的認識。
老舍明確與“蘭亭論辯”相關的文獻,是其寫的一首七律《呈郭老——讀郭老〈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戲成一律錄呈郭老博粲》:“右軍乏策宋蘭亭,郭老奇師陣氣騰。丹虎從鳳原是女,神龍作浪化為僧。書家時代難顛到,科學精神避愛憎。傳說元權充鐵證,墓碑躍躍出金陵。”④《老舍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712頁。從內容看,老舍明顯也屬于支持郭文的一方。此詩原附于1965年7月22日老舍致于立群信,信中說:
郭老書《送瘟神》大字收到,已送交醫學科學院,并囑代致謝!打油詩一首附奉,博郭老一笑!署甚,恕不一一!⑤《老舍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732、583頁。
郭沫若書大字的緣由,可參閱1965年7月13日老舍致郭沫若的信:
南游歸來,詩囊必富,切盼拜讀佳篇,學習受益!立群同志索扇,已畫好;醫學科學院求您寫毛主席《送瘟神》二律,紙在我處,當與小扇一同送上。何時在府,祈示下(電話55.4879),以便拜謁!⑥《老舍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732、583頁。
可見,在“蘭亭論辯”的醞釀階段,郭沫若老舍二人正有所過從。很有可能是老舍代醫學科學院求字,并送扇送紙往郭府后,郭沫若將其論文給老舍閱讀,并征求其意見。數日后,郭沫若將所書大字寄老舍,老舍致信于立群并附詩,但7月22日這個回信的時間很蹊蹺,郭如果當天收到信,次日高二適的駁文就在《光明日報》上刊發了,標志著“蘭亭論辯”的開始;如果老舍此信是次日送達郭府,則可以說老舍成了“蘭亭論辯”開始后,第一個支持郭文的人。雖說論辯開始的標志是作為駁方的高二適真正登場,但在北京文化界上層,高文在見報之前,估計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老舍在這場論辯真正公開化的前一天,寫詩支持郭文。當然,這只是出于筆者的推測,前提是以老舍于文化界的地位,在高文見刊前就得知了這場論辯將要發生。另一種可能,即老舍提前并不知道關于論辯將要發動的任何消息,7月22日寫信附詩只是一個巧合,但其支持郭文的態度也還是需要進一步辨析。
其實后來人們對“蘭亭論辯”雙方參與者的評價,很大程度上走入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模式,因為支持郭文的人,有些是迫于壓力而做出的違心之論,而高二適這樣的反對者,則是出于客觀的學術態度與敢于跟威權論爭的學術膽識,來撰文反駁的,所以,此后對“蘭亭論辯”參與者的評價,很大程度上已經趨向于政治立場和知識分子的人格討論,對于臺面上的十余位實際參與者,僅從支持與辯駁郭文的立場,而區分出誰是曲學阿世,誰敢對抗權威。例如晚年的啟功雖然想辯白于自己在“蘭亭論辯”中的表現①詳參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縱使世人有同情之理解,可白紙黑字,文責自負,終不免會有“惜公曲學辨蘭亭”②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29頁。之譏。
伴隨著我國時代的進步,市場經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我國生產總值不斷提高,項目管理模式已成為當前市場經濟中的重要研究課題。傳統的項目管理模式已難以適合當前社會發展進程,任何管理模式都應為適應社會發展而摒棄舊觀念和管理模式。當前企業或部門應對傳統與現代項目管理模式,探究其優缺點,并歸納比較,再結合當前市場環境和自身問題制定出一套科學合理的管理方案。
可是,“蘭亭論辯”畢竟有它作為學術討論的一面,參加者也基本限于書法文博圈子,要說由此發動大規模的政治斗爭,確實也很難。故而有研究者認為“康生、陳伯達都對學術文化相當內行,憑其政治經驗及權謀,何至于不能認識及此?必須承認,康生舊學修養相當深厚,陳伯達也至少夠得上附庸風雅的層次,他們跟郭沫若之間,無疑也是風雅之交。所以,不能因為陳伯達介入,就必定是政治陰謀。陳伯達授意郭沫若辨《蘭亭序》之偽,更可能出于‘純學術’的翻案動機;只不過,陳伯達‘口含天憲’的特殊背景,加上郭沫若的學霸身份,使學術論爭顯得政治化罷。”③真是李大嘴(胡文輝):《煙云過眼未能忘:〈啟功口述歷史〉讀后》,見梁由之主編:《我的閑閑書友》,上海:文匯出版社,2010年8月,第347頁。所以,我們對“蘭亭論辯”發言者的評價,隨著考察范圍的擴大,是否可以多出一種向度,關照到出于“純學術”動機的發言者呢?對于在臺面上論爭之外的人,他們針對“蘭亭論辯”的表態,我們還是否僅從簡單的政治立場和知識分子人格來評價,這就要進一步討論了。那么,老舍寫詩對郭文的支持,不論他是否提前知悉了這場論辯的發起,筆者以為都不能簡單地套入政治與人格的模式,來對此作出評價,并由此將老舍歸之為“曲學”一類,那樣反而失之偏頗了。
以下,具體來看看老舍的這首律詩,并以此討論老舍支持郭文的內在理路。張桂興先生對此詩有過箋釋④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第321-322頁。,但不完整,這里筆者將老舍七律與郭文對勘,做相應補箋:
右軍乏策宋蘭亭,郭老奇師陣氣騰
【箋】此句是老舍總起,一說右軍“乏策”,一說郭沫若“奇師”,將《蘭亭序》與郭沫若的論文對立,因為后者對前者真偽的質疑,所以將此喻為一場戰爭,以“奇師”、“陣氣騰”比喻郭文。而且,從詩中流露出的“對立性”,似乎老舍已經得知了“蘭亭論辯”即將開始的消息。
丹虎從鳳原是女
神龍作浪化為僧
【箋】郭文:“智永是陳代永興寺的僧人……不僅《蘭亭序》的“修短隨化,終期于盡”的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宜。因此,我敢于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托。”按,“神龍”代指《蘭亭序》。存世唐代馮承素摹本《蘭亭序》,因為卷首有唐中宗李顯神龍年號小印,故稱“神龍本”。
書家時代難顛到
【箋】郭文:“《蘭亭序》是梁以后人依托的,梁武帝當然不會見到……在梁武帝時,鐘王的真跡已經寥若星辰,而依托臨摹的風氣卻已盛極一時。”
科學精神避愛憎
【箋】郭文:“我說《蘭亭序》依托于智永,這并不是否定《蘭亭序》的書法價值;也不是有意侮辱智永……我自己也是喜歡《蘭亭序》書法的人,少年時代臨摹過不少遍,直到現在我還是相當喜歡它。我能夠不看帖本或墨跡影印本就把它臨摹出來。這是須得交代明白的。”
傳說無權充鐵證
【箋】《老舍全集》中為“元權”⑤《老舍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712頁。,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中為“無權”⑥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第321-322頁。。此處據張氏《輯注》校改為“無權”。原詩載于老舍致于立群的信中,想必《全集》和《輯注》都是根據老舍手跡錄入,筆者無法看到手跡,只能做出推測,應該是《全集》排版之誤。如果老舍用繁體字書寫,書法中“無”與“無”可以混用,在經典法帖中也不乏先例(如米芾《龍井山方圓庵記》),所以不排除老舍用“無”字,被《全集》編者誤植為“元”,若用簡體書寫,則更是如此。其次,從詩句意思上推測,“無權”即沒有權利,全句是說在學術研究中不能或無權將傳說當成是鐵證。郭文:“《蘭亭序》的書法有這樣崇高的盛譽,故在開元、天寶年間所流傳的關于它的‘佳話’,差不多就和神話一樣了。”按,老舍所謂“傳說”,即指流傳的各種關于《蘭亭序》的故事,比如在郭沫若論文中提到的何延之《賺蘭亭記》和劉餗關于《蘭亭序》的說法。
墓碑躍躍出金陵
【箋】《老舍全集》中為“躍躍”①《老舍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712頁。,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中為“遙遙”②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第321、322頁。。此處依《全集》。筆者無法看到手跡,“躍”與“遙”書寫差別較大,只能據詩句文意判斷,“躍躍”形容心情的激動、歡快,“遙遙”形容距離遠,二者都講得通,但似乎前者更好。郭文:“近年,在南京郊外及其近境出土了幾種東晉時代的墓志……頃得南京文管會五月十九日來信,言于興之墓旁又發現王彬長女丹虎之墓。”
這是老舍讀完郭文后以律詩的形式,寫給郭沫若的一篇讀后感,而且老舍在詩中也沒有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將全詩與郭文進行比勘,不難發現,老舍基本上是緊貼著郭文的具體內容在寫。張桂興先生認為,“老舍為郭老的科學精神和治學態度所感動,于是作舊體詩一首相贈”。③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第321、322頁。筆者認為,這種解讀,相比于套用政治與人格的評價模式,更能貼近事實的本質。郭文確實值得商榷,但也沒有必要把所有支持郭文的人,都看作是“曲學”。
況且,老舍這首詩所表達的,也有其內在理路可尋:第一,不論“蘭亭論辯”在政治上發展到什么態勢,也不論其背后的康生、陳伯達,單就郭文來講,畢竟有其“純學術”的翻案動機,況且對《蘭亭序》的翻案文章,自古有之,其將地上文獻與地下文物兩結合的方法,也不能說不科學,至于結論能不能被人認可或接受是另一回事,所以,老舍單純從郭文的科學精神和治學態度出發來寫詩;第二,老舍不屬于文博界的人,嚴格講也不在書法圈子內,更非治魏晉史或魏晉文學的專家,所以不在被點名需要表態的人之列,也就沒有刻意迎合的必要,完全是其出于真誠的表達欲望;第三,從書法的層面講,老舍是由帖學走向碑學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老舍的書法“取法源自《石門銘》和《爨寶子》”④李建森:《關于老舍及其書法》,《小說評論》,2007年第1期。,雖然老舍并沒有留下關于書法的述學文字,但其書法中魏碑風格很明顯,⑤《爨寶子》與《爨龍顏》嚴格來講不屬于魏碑(北碑系統),從時間上說,它們是晉碑,從地域上說,它們位于云南,但是由于其具有魏碑的風格特色,所以,一般來講,不論是書法史還是學書者,都把它們歸入魏碑。而郭文認可并承襲了清代李文田的觀點,即王羲之時代的書法,應該是《爨寶子》與《爨龍顏》的那種風格,這正與老舍后來的取法路徑相同。老舍雖然是以帖學入門,坊間也流傳有其《集王圣教序》的臨本,但并不妨礙他在看到郭文后也對《蘭亭序》進行質疑,應該說他的心態與郭沫若相似,即喜歡《蘭亭序》的書法是一方面,學術研究是另一方面,質疑《蘭亭序》真偽的同時,并沒有否定其書法的高度,⑥郭沫若說:“我自己也是喜歡《蘭亭序》書法的人,少年時代臨摹過不少遍,直到現在我還是相當喜歡它。我能夠不看帖本或墨跡影印本就把它臨摹出來。這是須得交代明白的。”(郭沫若:《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文物》,1965年第6期)。這或許也是老舍寫詩支持郭文的一大誘因。
對于“蘭亭論辯”,很多時候我們都是以預設視角或觀點來審視當年的材料,陷入政治立場和知識分子人格所帶來的“兩點論”(即曲學阿世與對抗權威)評價。所以,從郭沫若與老舍關于“蘭亭”的互動,可以豐富我們對“蘭亭論辯”的觀察視野,而其中涉及到對老舍七律的解讀,也會影響到對老舍的評價。隨著今后對于“蘭亭論辯”觀察視野的不斷擴大,對歷史中發言者的評價,也應該走向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