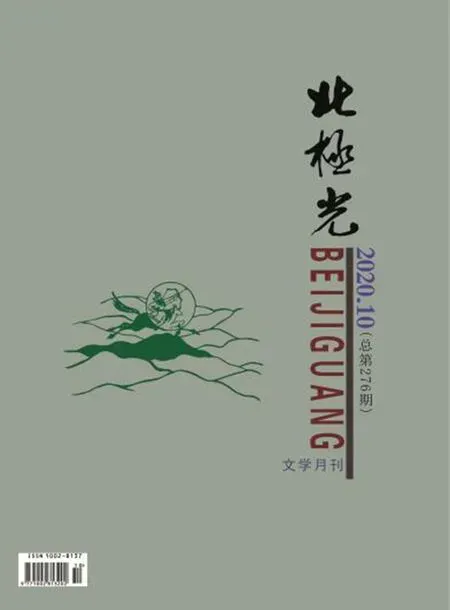苦難·饋贈(zèng)(外二篇)
每當(dāng)我重溫《九重水稻》創(chuàng)作背景的時(shí)候,我的內(nèi)心總會(huì)滋生出一種久違了的情愫,一種純粹的歡欣,一種寧?kù)o的詩(shī)意,以及透明而溫馨的回憶。
我清楚地記得,寫(xiě)作《九重水稻》的時(shí)候,正是我在復(fù)旦大學(xué)求學(xué)最為艱難的時(shí)候。那是一個(gè)充滿陰沉和壓抑的一天,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1990年10月30日。之所以清楚地記得這個(gè)日子,是因?yàn)檫@一天是《西湖》文學(xué)雜志舉辦全國(guó)散文大獎(jiǎng)賽的截止日。大獎(jiǎng)賽一等獎(jiǎng)除了燙金的獎(jiǎng)牌和到美麗的西湖參加頒獎(jiǎng)大會(huì)外,還有令人心動(dòng)的一千元獎(jiǎng)金。說(shuō)穿了,我就是奔這個(gè)獎(jiǎng)金去的。
那個(gè)時(shí)候,我的月工資才45元,但我毅然辭掉了醫(yī)院的工作,借著學(xué)費(fèi),義無(wú)反顧地去讀書(shū),沒(méi)有固定的收入,只靠有限的稿費(fèi)生活,十分拮據(jù),生活有時(shí)難以為繼。一千元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是個(gè)天文數(shù)字。我相信大獎(jiǎng)賽的公正,渴望用自己的文字得到這筆獎(jiǎng)金。當(dāng)時(shí),我正在全力以赴備考當(dāng)年的文藝學(xué)研究生考試,心情的緊張和時(shí)間的匆忙可以想見(jiàn)。
我在復(fù)旦大學(xué)校本部一間簡(jiǎn)單的教室里思考著一路走來(lái)的艱辛和傷痛,很快進(jìn)入到一種熔漿般沖動(dòng)的情境中。我想起自己的苦難生命,想起水稻和悠悠蒼天的耕種者們的辛勞,對(duì)水稻,對(duì)沉重的故鄉(xiāng),對(duì)黑土地的情感豈能是“愛(ài)與恨”就能說(shuō)清得了的!一種發(fā)燙的情感掠過(guò)我的心尖,我在作業(yè)本上飛快地寫(xiě)下了《九重水稻》這個(gè)篇名,然后一口氣寫(xiě)了下去,寫(xiě)到動(dòng)人處,我竟無(wú)聲地哭了——為父母、為水稻、為多災(zāi)多難的鄉(xiāng)村歲月。大約寫(xiě)了兩個(gè)多小時(shí),竟然寫(xiě)了四五千字,寫(xiě)完后,我感覺(jué)是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便找來(lái)一本稿紙,又認(rèn)認(rèn)真真地抄寫(xiě)了一遍。我?guī)缀鮼?lái)不及潤(rùn)色和修改,便原汁原味,于當(dāng)天中午用掛號(hào)信寄了出去。很快,我收到了《西湖》雜志社的回信,說(shuō)我的作品已經(jīng)入圍了。
我很興奮,信心滿滿地等待著大獎(jiǎng)的來(lái)臨,然而,大獎(jiǎng)沒(méi)有降臨到我的頭上,最后連個(gè)優(yōu)秀獎(jiǎng)都沒(méi)有得到。我不免有些沮喪,回頭再看看這篇文章,覺(jué)得還是不錯(cuò),于是將它先后寄給了幾個(gè)有些聯(lián)系的雜志編輯,但都沒(méi)有回音,最后,我投給了只有一面之緣的《人民文學(xué)》的老編輯向前老師,她把我的散文轉(zhuǎn)給了責(zé)任編輯高遠(yuǎn)先生。
大約是1991年1月的某天,我突然收到著名詩(shī)人、時(shí)任《人民文學(xué)》的副主編韓作榮先生的來(lái)信,說(shuō)我的長(zhǎng)詩(shī)《九歌》要在該刊發(fā)表,但因?yàn)橄纫l(fā)表我的散文《九重水稻》,所以何時(shí)發(fā)表詩(shī)歌尚未確定,請(qǐng)不要將詩(shī)作投寄他刊。接到這封信,我欣喜若狂,立即給韓作榮先生寫(xiě)信,希望能夠盡快將兩文發(fā)出來(lái),因?yàn)槲艺郎?zhǔn)備參加研究生考試,如果考不上,就得重新去找工作。
就這樣,1991年《人民文學(xué)》第二期在散文頭題位置推出了《九重水稻》,又在第三期詩(shī)歌頭題位置推出了長(zhǎng)詩(shī)《九歌》。也正是這一年三月,全國(guó)研究生考試錄取分?jǐn)?shù)線也公布了,我考取了研究生!好事接二連三,令人振奮。不久,《九重水稻》被《散文選刊》當(dāng)年第九期頭條推出,責(zé)編張若愚先生還給我寫(xiě)了一封很長(zhǎng)的信,說(shuō)我的散文提高了該刊的品位。之后,《九重水稻》又被選入《1991年散文年鑒》頭題,再后來(lái),這篇散文選入了二十余個(gè)選刊選本。
1991年歲末年初,《人民文學(xué)》雜志的高遠(yuǎn)先生向我約稿,我很快寄給他一篇《保衛(wèi)水稻》,該文再次于1992年2期《人民文學(xué)》散文頭題刊出,也選入了當(dāng)年的《散文選刊》頭題以及多種選刊選本。自1991年至1998年,連續(xù)八年,我每年都在《人民文學(xué)》上發(fā)表作品,為此,我深深感激這個(gè)刊物的老師們!
1994年,《人民文學(xué)》創(chuàng)刊45周年(1949-1994)之際,該作與冰心和周濤等人一起榮獲該刊優(yōu)秀散文大獎(jiǎng),剛到湖南日?qǐng)?bào)做記者的我也應(yīng)邀赴人民大會(huì)堂領(lǐng)獎(jiǎng),當(dāng)晚,中央電視臺(tái)新聞聯(lián)播作了報(bào)道。記得當(dāng)時(shí)《人民文學(xué)》的主編劉白羽先生握住我的手,鼓勵(lì)道:“小伙子,你的創(chuàng)作路子走對(duì)了!”
最不可思議事情的是,《九重水稻》除了獲得一座沉甸甸的獎(jiǎng)牌外,還獲得了一千元獎(jiǎng)金……現(xiàn)在回想起這一切,可謂感慨萬(wàn)千——那真是一個(gè)激情飛揚(yáng)的年代,令人懷想的年代,文心燦爛的年代啊!
一路走來(lái),沒(méi)有文學(xué)的這支火炬,沒(méi)有復(fù)旦大學(xué)的這個(gè)平臺(tái),沒(méi)有作家班同學(xué)的這份友情,沒(méi)有老師、朋友和親人們的真正扶攜、悉心愛(ài)護(hù)與全力幫助,我不可能有今天。我默默銘記這一切,以感恩的心,過(guò)好每一天。
生命因苦難而飽滿,生活因文學(xué)而精彩。
越過(guò)千山萬(wàn)水來(lái)會(huì)你
非常高興、非常激動(dòng)也非常榮幸能夠跟大家講幾句心里話。說(shuō)真的,此刻發(fā)言,我很有壓力,千言萬(wàn)語(yǔ),一時(shí)不知從何談起,我想到一個(gè)題目,叫做《越過(guò)千山萬(wàn)水來(lái)會(huì)你》。是什么力量,讓我們排除一切困難,從大洋彼岸的美國(guó),從南太平洋島國(guó)新西蘭,從祖國(guó)的四面八方,聚到一起?
在此,我想講講我與文學(xué)、我與復(fù)旦、我與作家班的關(guān)系吧。用一個(gè)也許不太恰當(dāng)?shù)谋扔鳎谖铱磥?lái),文學(xué)是戀人,復(fù)旦是恩人,作家班是親人。
首先,文學(xué)是戀人。三十年前,在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最好的時(shí)期,我們聚在了一起。那時(shí)我們青春年少,充滿熱情、幻想和浪漫。與其說(shuō)我們是尋夢(mèng),不如說(shuō)我們?yōu)榱艘粋€(gè)共同的戀人:文學(xué)。因?yàn)槲膶W(xué),我們物質(zhì)上也許貧窮,但精神上絕對(duì)富有。因?yàn)槲膶W(xué),讓我這個(gè)地地道道的鄉(xiāng)下人操著濃濃的鄉(xiāng)音來(lái)到繁華的大都市,來(lái)到心中的圣地:復(fù)旦大學(xué)。那時(shí)的交通極不發(fā)達(dá),從衡陽(yáng)到上海,要坐28個(gè)小時(shí)的火車。車上人齊人,連廁所都擠滿了人。每一次來(lái)校與返鄉(xiāng),都是一次體力和意志的大比拼。我一般是不吃不喝,也不能上廁所,結(jié)果下火車后急匆匆去找?guī)谝慌菽蚴茄颉?梢哉f(shuō),對(duì)文學(xué)這個(gè)戀人,我們傾其所有,愛(ài)得很深,愛(ài)得很苦,愛(ài)得無(wú)怨無(wú)悔。幾天前,一個(gè)年過(guò)花甲的朋友說(shuō),這一輩子,傷害他最深的是文學(xué)。我一聽(tīng)就火了,毫不客氣地說(shuō):你這樣說(shuō)太矯情了。沒(méi)有文學(xué),你算得了什么?對(duì)文學(xué)就像對(duì)待戀人,我們永遠(yuǎn)要懷著感恩和敬畏之心去愛(ài)她,永遠(yuǎn)要懷著飛蛾撲火般的純粹和沖動(dòng)去追求她。你責(zé)備她只能證明你的無(wú)能,你抱怨她只能證明你是假愛(ài),不是真愛(ài)。這個(gè)朋友聽(tīng)了我的話后,感到非常羞愧。
其次,復(fù)旦是恩人。“日月光華,旦復(fù)旦兮”。這是一個(gè)神奇的地方,也是一個(gè)人杰地靈的地方。30年前,我辭掉工作,毅然決然地來(lái)到這里。我不知道會(huì)發(fā)生什么,但我知道,這是我唯一的機(jī)會(huì)。復(fù)旦開(kāi)放、自由、包容的氛圍,老師們的熱情、睿智和高山仰止的風(fēng)骨,校園洋溢的書(shū)香氣、青春氣和無(wú)處不在的讀書(shū)聲,特別階梯教室和中文系圖書(shū)館的祥和、安靜,這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我早年的散文代表作《九重水稻》就在這里寫(xiě)成的,我的研究生也是在這里考上的,這是我的福地。每當(dāng)我在追夢(mèng)的路上取得一點(diǎn)點(diǎn)成績(jī)的時(shí)候,我總是把它歸功于復(fù)旦,默默地朝著復(fù)旦的方向,像一個(gè)卑微的人頻頻向恩人送去祝福。正因?yàn)榇耍彝馍膬鹤酉臑t,也就是我的曾外甥,三年前,15歲的他高考成績(jī)十分耀眼,北京大學(xué)、浙江大學(xué)、香港大學(xué)等都有意錄取他,當(dāng)他征求我的意見(jiàn)時(shí),我毫不猶豫地說(shuō),去復(fù)旦大學(xué)吧,我的外甥說(shuō):“好,就這么定了,沿著舅爺爺?shù)淖阚E,去復(fù)旦,不會(huì)錯(cuò)!”這就是復(fù)旦在我心目中的份量。如果有人問(wèn),復(fù)旦是什么?我說(shuō),復(fù)旦是恩人;如果有人再問(wèn):作為恩人的復(fù)旦究竟是什么?我會(huì)說(shuō):他總是讓你在關(guān)鍵時(shí)刻,起著一錘定音的作用;總是讓你在抉擇的時(shí)候,目標(biāo)變得特別清晰;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shí)候,勾起你的鄉(xiāng)愁,勾起你對(duì)他的種種想象,包括對(duì)他的思念和感恩。
再次,作家班是親人,是家人,同學(xué)們是我的兄弟姐妹。這么多年來(lái),我們不僅有共同的戀人,共同的恩人,我們還有共同的思想紐帶和精神家園。作為親人、家人和兄弟姐妹,無(wú)論世道如何變化,我們互幫互助,親密無(wú)間。我依然記得,1990年鄒立孟為我出版第一本詩(shī)集墊付的800元;我依然記得,凡一平在《三月三》雜志工作時(shí)給我發(fā)表的中短篇小說(shuō)和詩(shī)歌;我依然記得,久無(wú)音訊的東蕩子突然來(lái)到我家,送來(lái)他剛剛出版的詩(shī)集;我依然記得1999我去新西蘭留學(xué),徐彥平送我去機(jī)場(chǎng);我依然記得肖長(zhǎng)春、張秉毅等同學(xué)對(duì)我的種種關(guān)愛(ài)與幫助;我也依然記得,當(dāng)翁亮、高福廳、東蕩子、綠風(fēng)和李希曾五位同學(xué)英年早逝的消息傳來(lái),我心里的震驚、悲痛與每位同學(xué)感同身受,淚流滿面。而這樣的震驚、悲痛,只有親人、家人和兄弟姐妹才會(huì)有的。這些年來(lái),我給多位同學(xué)寫(xiě)過(guò)評(píng)論文章。我指導(dǎo)自己的學(xué)生,以凡一平、施瑋、虹影、盧文麗、東蕩子、張秉毅、肖長(zhǎng)春、王琰等近10位作家班同學(xué)的個(gè)人作品作為研究生、本科生畢業(yè)論文的研究對(duì)象。在選題分析時(shí),每當(dāng)有老師說(shuō)一些同學(xué)的份量不夠、不能作為畢業(yè)論文分析對(duì)象的時(shí)候,我總是很激動(dòng),說(shuō)當(dāng)年的無(wú)名之輩沈從文,如果不是北大教授林宰平先生為他的《遙夜》寫(xiě)下第一篇評(píng)論,并極力推薦,沈從文的文學(xué)之路究竟怎樣也很難說(shuō)。每個(gè)作家,哪怕就像沈從文這樣的文學(xué)大家,也總得有人給他寫(xiě)第一篇評(píng)論文章、作第一篇畢業(yè)論文。因此,我會(huì)繼續(xù)努力,為我的親人、我的家人和我的兄弟姐妹在文壇上閃閃發(fā)光貢獻(xiàn)自己的綿薄之力。
現(xiàn)在,我要回答,是什么力量,讓我們?cè)竭^(guò)千山萬(wàn)水來(lái)相會(huì)?很顯然,是文學(xué)的戀人、復(fù)旦的恩人和作家班的親人,這樣磅礴的力量,足以讓我們戰(zhàn)勝一切困難。
我要感謝這個(gè)偉大的時(shí)代;感謝文學(xué)給我們帶來(lái)了不一樣的生活;感謝復(fù)旦大學(xué)的不拘一格和海納百川;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栽培和無(wú)私奉獻(xiàn),你們的治學(xué)態(tài)度、理想情懷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未來(lái);感謝中文系和出版社,是你們精心策劃、組織好這么一次有意義的聚會(huì);感謝到場(chǎng)和沒(méi)有到場(chǎng)的同學(xué)。因?yàn)槲膶W(xué),我深深感恩。
總之,這是一場(chǎng)文學(xué)的盛典,更是一次友誼的見(jiàn)證。這是一個(gè)注定要誕生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的時(shí)代。雖然我們不再青春年少,但文學(xué)是一場(chǎng)馬拉松賽,只要我們的激情依舊,只要我們的追求依舊,只要我們的夢(mèng)想依舊,我們的未來(lái)就一定無(wú)可限量,我們的未來(lái)就一定更加精彩!
夢(mèng)想在哪里,追求就在哪里
非常高興參加這個(gè)會(huì)議,能夠見(jiàn)到這么多的領(lǐng)導(dǎo)、師長(zhǎng)和朋友,能夠在闊別20年之后回到湖南日?qǐng)?bào)這個(gè)光榮的集體,參觀它的成就,感受它的發(fā)展,見(jiàn)證它的騰飛,我十分激動(dòng)。
我是1994年來(lái)到湖南日?qǐng)?bào)工作、1999年離開(kāi)這兒的,我一直把這5年當(dāng)成是人生中最閃亮、最充實(shí)、最快樂(lè)、最美好的一段時(shí)光。由一個(gè)地地道道的農(nóng)家子弟成長(zhǎng)為一個(gè)黨報(bào)記者,我感恩、知足,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勁兒。我從湖南日?qǐng)?bào)記者部到三湘都市報(bào)政法部后來(lái)又到湖南日?qǐng)?bào)文體部,最后做了湘江文藝副刊的編輯,可以說(shuō),每一個(gè)不同的崗位,我都任勞任怨,從來(lái)沒(méi)有懈怠過(guò)。
在湖南日?qǐng)?bào)工作有四件事讓我永遠(yuǎn)不會(huì)忘記:一是因揭露一個(gè)地痞流氓,我被人追殺,報(bào)社領(lǐng)導(dǎo)出于安全考慮,把我悄悄安排到南岳避風(fēng);二是《三湘都市報(bào)》創(chuàng)辦之初,我到浙江、福建參加全國(guó)統(tǒng)一的“打拐”行動(dòng),整整28天,我克服一切困難,保證每天一篇報(bào)道,弄得頭發(fā)全白了。萬(wàn)茂華總編很感動(dòng),親自到株洲來(lái)迎接我,當(dāng)年被省政府記功一次;三是跟夏陽(yáng)老總?cè)コ5陆蚴懈惆l(fā)行,他們晚上搞活動(dòng),我躲在房間寫(xiě)關(guān)于津市的長(zhǎng)篇通訊。第二天,一個(gè)整版的報(bào)道發(fā)了出來(lái),夏陽(yáng)老總覺(jué)得很有面子,津市書(shū)記十分高興,當(dāng)即拍板,追加一千份發(fā)行量;四是我出國(guó)后,連續(xù)四年,每年都收到一包花生,洗得干干凈凈的。后來(lái)才知道,我在作政法記者時(shí),收到一個(gè)婁底婦女寄來(lái)的錄相帶,一伙流氓剝光她的衣服,押著她在大街上游行。我看后十分氣憤,寫(xiě)信向時(shí)任省政法委書(shū)記反映,最終那伙流氓得到了應(yīng)有的懲罰。這個(gè)婦女一直沒(méi)有跟我見(jiàn)過(guò)面,但她用最質(zhì)樸的方式表達(dá)了內(nèi)心的一份感激。
我講這些,并不是說(shuō)我有多大能耐,而是說(shuō)湖南日?qǐng)?bào)這個(gè)平臺(tái)有特殊的力量。它不僅可以為你擋雨避風(fēng),而且可以讓你為公平吶喊、為正義助威!
湖南日?qǐng)?bào)不僅是我的娘家,更是我的福地;是我事業(yè)的起點(diǎn),更是我事業(yè)的支撐點(diǎn):早在我讀研究生時(shí),湖南日?qǐng)?bào)不僅多次發(fā)表我的文學(xué)作品,還兩次發(fā)表對(duì)我的新聞報(bào)道。1999年我去新西蘭懷卡托大學(xué)(現(xiàn)在的新西蘭總理就是這所大學(xué)畢業(yè)的)留學(xué),拿到了這所大學(xué)有史以來(lái)第一個(gè)人文社科類全額獎(jiǎng)學(xué)金的亞洲學(xué)子(這個(gè)紀(jì)錄至今還沒(méi)有被打破),靠的是我在湖南日?qǐng)?bào)工作的經(jīng)歷和當(dāng)時(shí)出版的6本著作;2004年我到中南大學(xué)任職,從助教直接破格晉升為教授、學(xué)科帶頭人,靠的也是湖南日?qǐng)?bào)的這段經(jīng)歷和我的博士文憑。
多年來(lái),我一直把湖南日?qǐng)?bào)作為內(nèi)心的發(fā)光點(diǎn)和動(dòng)力源,我想向各位領(lǐng)導(dǎo)、師長(zhǎng)和朋友報(bào)告的是:在中南大學(xué)從教15年來(lái),光是我指導(dǎo)畢業(yè)的研究生就有53名,為此,我感到欣慰。目前,我?guī)Я?名博士生(含一名留學(xué)生)、12名碩士生和15名本科生,我將一如既往,將他們培養(yǎng)成國(guó)家需要的有用之材。實(shí)際上,湖南日?qǐng)?bào)也有多名編輯記者是我的弟子。湖南日?qǐng)?bào)不久前還招了一個(gè),她是今年新畢業(yè)的傳播學(xué)碩士生,本來(lái)在一家知名房地產(chǎn)公司工作了,看到招聘信息,立即前來(lái)報(bào)考,筆試考了個(gè)第一名,她說(shuō)來(lái)老師的福地工作,會(huì)有光明的前程。
2018年我一次性推出了7大卷、300余萬(wàn)字的《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與文學(xué)湘軍發(fā)展研究》,算得上是一個(gè)人的湖南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也正是這一年我的學(xué)術(shù)專著《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的文學(xué)表達(dá)》由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推出后,獲得國(guó)家社科基金對(duì)外翻譯項(xiàng)目立項(xiàng),將被譯成英文由權(quán)威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蘭登公司向全球發(fā)行。《湖南日?qǐng)?bào)》用將近一個(gè)整版對(duì)我這些年的努力進(jìn)行了報(bào)道。
2019年7月我的散文集《保衛(wèi)水稻》出版,并在上海書(shū)展上舉行新書(shū)發(fā)布會(huì),書(shū)中很多作品都是當(dāng)年在湖南日?qǐng)?bào)工作時(shí)完成的。其中《九重水稻》1994年獲得《人民文學(xué)》大獎(jiǎng),我應(yīng)邀到人民大會(huì)堂領(lǐng)獎(jiǎng),湖南日?qǐng)?bào)也報(bào)了報(bào)道。
2019年,我還推出萬(wàn)行長(zhǎng)詩(shī)《共和國(guó)英雄》,《詩(shī)刊》《解放軍文藝》《芙蓉》等雜志都大篇幅刊發(fā)了其中的章節(jié),《鄂爾多斯》雜志更是以整本雜志刊登了這部詩(shī)稿的全部。其中,這部長(zhǎng)詩(shī)最早的一組詩(shī)《英雄兒女》寫(xiě)于1988年,寫(xiě)的是毛岸英、黃繼光、董存瑞、劉胡蘭等;長(zhǎng)詩(shī)中的《歌唱長(zhǎng)江》1998年在湖南日?qǐng)?bào)發(fā)過(guò)副刊頭條,并獲得當(dāng)年報(bào)紙副刊作品金獎(jiǎng);今年3月寫(xiě)的《致敬!偉大的雷鋒》和5月寫(xiě)的《五四的火焰》,龔政文總編和金中基編委都十分重視,這兩首詩(shī)先后在《湖南日?qǐng)?bào)》發(fā)了大半個(gè)版。萬(wàn)行長(zhǎng)詩(shī),《湖南日?qǐng)?bào)》就發(fā)表了至少500多行。可以說(shuō),湖南日?qǐng)?bào)見(jiàn)證并推動(dòng)了這部長(zhǎng)詩(shī)的最終完成。這部長(zhǎng)詩(shī)在中宣部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guó)平臺(tái)和黨建網(wǎng)等全國(guó)數(shù)百家主流媒體連載,又先后在望城融媒體中心、長(zhǎng)沙實(shí)驗(yàn)劇場(chǎng)和中南大學(xué)等地舉辦專場(chǎng)演誦會(huì),引起很大反響。所有這一切,都是我要來(lái)到這里,像老農(nóng)對(duì)待水稻,像小草致敬春天,我要當(dāng)面感謝報(bào)社的娘家人,感謝我的恩人們。
我想說(shuō),是天時(shí)、地利、人和成全了我。這“天時(shí)”就是偉大的時(shí)代,這“地利”就是湖南日?qǐng)?bào)和中南大學(xué)這個(gè)平臺(tái),這“人和”就是各位領(lǐng)導(dǎo)、師長(zhǎng)和朋友的關(guān)愛(ài)與支持。飲水思源,我永遠(yuǎn)不會(huì)忘這些年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走過(guò)來(lái)的。
今天,看到新湖南的蓬勃發(fā)展,我感到由衷的高興和自豪。我相信,湖南日?qǐng)?bào)的明天一定更加輝煌!
最后我想說(shuō):
夢(mèng)想在哪里,追求就在哪里;
信念在哪里,堅(jiān)持就在哪里;
初心在哪里,起點(diǎn)就在哪里;
使命在哪里,終點(diǎn)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