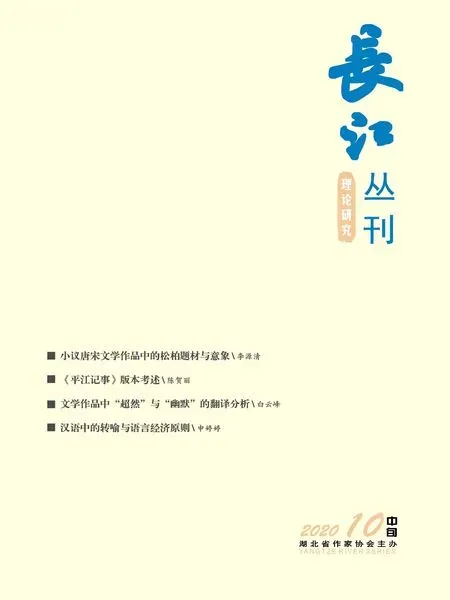如何理解伊德技術現象學中的詮釋關系
孫 鈺/嘉應學院
一、詮釋的概念與層次
詮釋這個詞語本身所具有的歷史淵源非常久遠,對于唐·伊德所提出的詮釋關系中的詮釋(hermeneutic)其主要意思對于文本的解釋,但是在伊德的觀念中所存在的詮釋關系是存在于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并非單純對于文本的解讀與解釋。伊德對詮釋學分為兩個層次進行認識:第一,文本解釋;第二,閱讀。
第一,文本解釋。人—(技術—世界)在這一位置中(技術—世界)是作為人類“閱讀”的最終級目的,但是閱讀的手段則是通過技術工具的形式而不是文本的閱讀形式。因此,唐·伊德表明,“文本的透明性是詮釋學的透明性,而不是知覺的透明性”[2]唐·伊德在《技術生活與世界》中對于詮釋關系的提出舉了一個非常形象的例子:“書寫中需要所有技術性工具,書寫是一種以技術為中介的語言。書寫轉化了我們對于語言的知覺和理解。書寫是一種嵌入在技術中的語言形式。”[3]由此可以得出,伊德對于人與技術關系的定義其主要來源是來自于詮釋學當中對于文本的閱讀就是對于文本理解方式,但是在此基礎之上伊德將詮釋學中對于文本的詮釋與理解進一步引申至技術哲學中對于人與技術之間關系的詮釋。詮釋學中的詮釋的是文本,技術詮釋所詮釋的是人的身體、并且將這種技術性工具嵌入到文化的大環境背景。詮釋學中的詮釋關系主要關系直接明了,所需要的只是人——紙質的書籍,但是對于技術物質則不同,在技術哲學中人與索要展現的世界之間多了一層關系,即技術工具。有了這一層中介的存在使得人-技術-世界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非常重要的改變。
第二,閱讀。“在一般的閱讀活動和由此延伸的閱讀活動中,被閱讀的東西都放在眼睛的前面或下面,我們從一種微型的鳥瞰視角來閱讀。”[4]由此可以看出,閱讀看似是眼睛的活動,實際上牽扯的是我們身體上全部器官的運動。伊德對于閱讀這一層次舉例如下:航海圖是人類海上活動最常用的地圖,人們要想獲得海上的任何航線必須遵守航海圖上的標識,在這一層上,人類的視覺本身就有了中介,因為人對于航海圖的閱讀行為,“其本身知覺關注的焦點是航海圖,而航海圖是風景的替代物。”[5]我們對于任何物的閱讀其實質都是為了解釋其物背后所代表的世界。我們讀書,文字是具有透明性的,我們透過文字的想象可以有很多,但是這將發動人的所有知覺,由此得到的詮釋關系是建立在人—(技術—世界)當中,而在具體的詮釋關系中技術和世界成為有機的一體,成為人所詮釋和所要理解的對象。在具身關系中的人與技術之間是相互依存,物我合一的,技術工具的自身將透明性表達的非常清晰。
二、詮釋的本體論地位
詮釋關系在唐·伊德的技術哲學關系中一直是在具身關系之后所發展的階層關系,級根本來源就是來自于具身關系的在發展。可以說每一階層關系的發展都必然要遵循前一階層發展中所具有的特點與不完善或并不安定之處,進而在發展。技術哲學中關系人—技術之間的關系同理如此。在歷史的發展中,人類所發展的讀書、寫字、音樂、樂器、美術、文學等等文化的衍生品的出現都是在將人類對于世界的感受具體的表現出來,書寫所發明的工具為了方便人們去記錄,記錄的終極目的因為人終究會死亡,需要有比人的記憶更為長遠的保存手段來駐留這些事情,因此產生了寫字與紀錄,但是人們所發明的樂器卻在模仿大自然各種各樣的聲音,我們所認為的樂器可以模仿大自然的聲音,其實不然,樂器的制造與開發正是為了將大自然的聲音進行有效的保存。美術、聲樂等等藝術、文學等多種的形式或者是工業、科學技術等等的形式其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記錄、記錄的目的為何?即為了后人可以將其閱讀、理解、闡釋、最終穿越時間的屏障回到過去,看到歷史的發展。
在人類對于技術的詮釋過程中,我們所閱讀的“文本”成為知覺的對象,在詮釋中,對于詮釋步驟來說,知覺是詮釋的第一步,有了知覺性的感受才會存在詮釋。知覺層次的詮釋是屬于身體范疇內,人類的大部分經驗獲得都是通過身體的知覺進行感知。詮釋技術當中所獲得對于外界事物的感受之初則是由人類的感官,我們的視覺,聽覺、觸覺等等。所以唐·伊德在技術詮釋中始終強調,閱讀其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實踐技術和感知的活動,我們對于事物的“閱讀”即對于事物的知覺,在知覺的過程中已經存在工具,人類的直覺即為人類生存所必須的工具,而我們所衍生出的其他具有物質性實質的工具其根本就是為了將我們的知覺進行擴張。
唐·伊德提出對物質的詮釋,對物的詮釋同時引申為“文化詮釋”,因為物質技術工具是在文化背景中產生的,因此認為技術的產生于發展都是脫離不開文化的產生中國著名的文學大師林語堂有這樣的一句話“思想是一種藝術,而不是一種科學。”啟發和檢驗都是一種雙向關系的表達,啟發主要是受外界某事物的刺激與開導從而產生不同的思想意識的表現形式,而檢驗則是來自于外界對自身的考核或實驗。所以前面兩項主觀性因素直接導出后面兩項異己性因素,由主觀性因素的準備到醞釀最后產生于外界想慣量的啟發與檢驗正是思想藝術化的過程。這一循環的過程對于思想的形成與藝術化的誕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鋼琴表演中的表演者經過這四個過程的準備從而形成實踐技術與身體的融合,進一步形成新的深層次藝術技術。所謂深層次的藝術技術就是思想的“技術”,在這一層次的技術與實踐性技術進行區別。這四個階段的主客觀關系對于表演者自身的實踐性技術展示是一個契機同時對于表演者思想上的“技術性”同樣也是一個機會,因為在展示實踐性技術的同時會得到來自外在的思想意識交流,這種交流會對表演者自身的實踐性技術產生一個積累性的跨越。馬克思曾說過“思想是人類無肌的肉體”,正因為具備了這種思想我們的身體才會產生表達的意向。
三、詮釋與差異
首先將詮釋分為兩個層次進行分析,淺層關系的影響。首先,淺層次的詮釋主要集中在對于文本詮釋。因為詮釋這一層次的理解一定是經歷的吸收與內化的過程最終形成的。所以就如唐·伊德描述的那樣,溫度計上的數字是你的知覺所傳達給你的信息,但那只是數字,從知覺上來說其本身感受不到溫度計上的溫度,我們最直觀看到的便是溫度計上的“文本”,可文本背后傳達的信息則是溫度的冷與熱。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對于文本閱讀的知覺既是詮釋的第一步,也是第二步,因為這一步的感知直接決定接下來我們對于其深層次內涵的感受。
其次,知覺的獲取與分析都是有人類的身體所控制,其最為深層次的根源也在與人的思想意識層面,對于每一個數字背后所代表的溫度都有所感受,詮釋的含義一定是內化之后的再釋放,再次,就詮釋關系中更深層次的引申則需要將技術或者我們詮釋的文本背后所要詮釋的文本背后思想。而我們開始所有活動的最根源目的就是要解讀出背后所要表達的意義。唐·伊德在詮釋關系層次中對于人與技術的關系引申是通過具身關系,在具身關系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變化為一體,在一體的基礎上人要融入技術的世界才會成為一體,因為,我倒認為應該是先產生詮釋關系,才會產生具身關系。我們只有知道其背后索要展現的是何物,何是,我們才可以與之成為一體。
人——技術的相互作用關系從其詮釋角度來講是詮釋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正是通過閱讀為手段,通過為探索路徑從而獲得對于詮釋關系的把握。同樣也正是因為對于關系的詮釋也是唐·伊德技術哲學關系中核心思想。唐·伊德認為在(我—技術)—世界這三者關系中我與技術在詮釋關系這一層當中處于迷之位置,因為在具身關系中的我與技術通過融合成為互相依存的關系,在這種關系的衍生下形成了技術的透明性,因為技術的透明性但是知覺的不透明所以使得接下來的詮釋關系可以增加閱讀的透明性,透明性的技術加上非透明性的人形成了宏觀層次上的詮釋,在宏觀視角中的詮釋關系為了與具身關系形成本質的差別而這一差別的主要根源則是源自技術大環境中的元素位置差異,從而無論是具身關系還是詮釋關系同樣如此。對于鋼琴表演活動中所有要素之間的關系所進行詮釋的顯現則是鋼琴表演中所產生的音樂音響效果帶來的互動性反應。
思想的“詮釋性技術”核心是從實踐層面的指導作用,技術性身體對于人來說具有局限同樣也有發展,如果僅從實踐性技術的層面分析人在使用技術的同時也在被技術所限制,同樣,技術也因為人的使用方式而產生發展方面的限制。或許這就是我們思想技術上的缺乏。我們一直在追求認識世界、認識自身,如何借助技術性工具來認識世界,如何通過技術身體的探索來認識人類自身,我們將思想賦予“技術”正如將音樂表現賦予人性化的表現方式一樣“‘人性化’了得(換句話說,通過人對現實的關系而得到表現的)客觀現實,也就是音樂的內容,正如它同樣是繪畫、雕塑、建筑、詩、舞蹈的內容一樣。”[6]
四、結語
詮釋關系或許不是每一個行為或活動最開始的目的,但一定是最為核心的目的。唐·伊德的詮釋關系的提出,其靈感正式來源與詮釋學,而詮釋學一直追求視域的融合將文本進行徹底的通讀進而理解出文本背后的意義,視域的融合對于詮釋關系來說具有同樣的應用性作用,因為無論是詮釋學當中的詮釋關系,還是技術哲學中的詮釋關系都是針對所要閱讀的真性文本與假性“文本”進行雙重解釋。文本性詮釋是針對文本的詮釋而技術哲學中的詮釋是針對技術工具的詮釋,這兩種詮釋關系的比較下,技術哲學的詮釋較比文本性的詮釋更為全面的是實踐方面。詮釋關系中詮釋的雙方并不是完全具有透明性在我—技術—世界的關系中技術就是全部的世界,因為在技術哲學的詮釋關系中技術所代表的背后意義就是世界,世界將技術帶到更為優越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