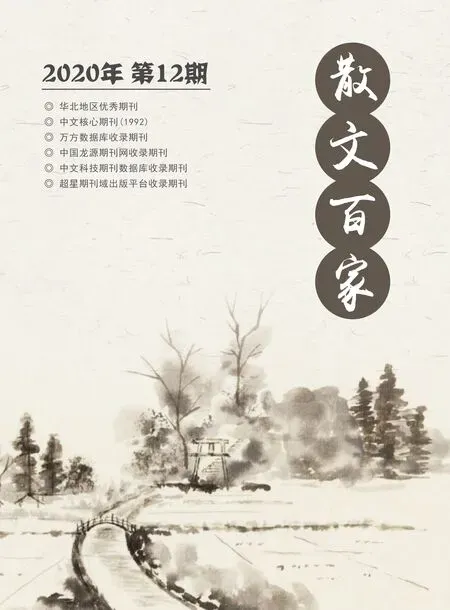王家屏與“國本之爭”
耿志偉
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王家屏與“國本之爭”
對于王家屏的研究,學術界多是對其一生的總括性概括。其中涉及王家屏的著作有李宏哲先生編寫的《王家屏年譜》和《王家屏行實三論》、樊樹志先生編寫的《晚明史1573-1644年》等。這些論著并沒有專門針對王家屏在“爭國本”事件中的作用來進行研究。本文結合以上研究成果,在《王文端公奏疏》、《明神宗實錄》等史料的基礎上,將研究方向放在王家屏在“爭國本”的事件中的相關活動,梳理并分析王家屏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理想。
一、王家屏生平簡介
王家屏,字忠伯,號對南,山陰縣河陰堡人(公元1535-1603),明隆慶二年獲第二甲第二名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這里還出現了一段小插曲:“隆慶戊辰成進士,廷試讀卷,擬一甲第二,穆廟稍錯綜之,得二甲第二,二選庶吉士高第。”[1]隆慶四年,授編修,作為進士朝廷按例任王家屏為編修,主要職務是纂修《世宗實錄》,這個職位雖然遠離權力中心,但卻是高級官員的預備隊。
之后王家屏的升遷速度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跡,在萬歷十二年正月由侍讀學士升任禮部右侍郎。十二月,又改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了明帝國的權力中心。“由隆慶戊辰進士萬歷十二年以吏左侍東閣學入。”[2]由一名默默無聞的史官到入閣輔政僅用時兩年,這創造了明代政壇上的神話,“去史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3]
二、王家屏在“國本之爭”當中的作用
1.王家屏對于諫官的申救。
神宗不理朝政的行為迅速引起朝官的不滿,同年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雒于仁的一本奏疏吹響了向神宗抗議的號角:“即王妃有皇冢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則溺愛貴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未建。”[4]首先雒于仁概括了皇上的病源在于酒、色、財、氣四個方面,從這些小毛病入手,逐步展開列舉神宗的荒謬行為并給予更深層次的批判。
雒于仁犀利的筆鋒毫不隱諱地直指神宗皇帝,并且系統的批評了皇帝的酒色財氣,并且舉出大量例證來證明,這本奏疏讓神宗勃然大怒,便與內閣諸臣商議,希望嚴懲雒于仁這只出頭鳥,內閣首輔申時行本人也對神宗皇帝不理朝政和停止經筵日講不滿,所以積極主張從寬處置,為雒開脫。王家屏也立即上疏為雒辯護,他主動承擔責任:“臣職親于庶官專任于輔導,乃尚有所不知不諫,夫不知,失職也,知之而不諫,失職也。安可獨罪于仁哉!”[5]他認為,假如雒于仁的話的確有很多的錯誤,那么嚴懲他還說得過去;但是如果他所說有的有一兩件事不幸言中,那么這樣處置,恐怕有妨于進諫之路。他向神宗指出:“甘言疾也,苦若藥也......此臣所以謂于仁為忠也。”[6]王家屏以藥喻人,用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樸素的道理為雒于仁辯護。在多方的努力下,雒于仁被從輕發落,削職為民。
神宗的我行我素也讓內閣首輔這個職位越發不好坐,時常處于風口浪尖,緣于張居正死后神宗有意利用放寬對言官的限制來抨擊張及其得力助手,從而為自己親政掃除障礙,持續的輿論高壓讓申時行、許國、紛紛離開了內閣。萬歷十九年,王家屏被推上了歷史的前臺,“樞機要地遺臣一人,發下本章無事體茫然莫知。”[7]但內閣成員的迅速減少也給王家屏帶來了沉重的工作壓力,而他們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留給了接任的王家屏,其中最重要最有爭議的莫過于爭國本事件。神宗不喜宮女所生的長子朱常洛,而因寵愛鄭貴妃,想要立次子朱常洵為太子。但這與文官集團共同認可的統治理念相違背,對于他們來說,推長而立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繼承制度層面,更代表著秩序和穩定,尤其貴為皇帝,即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更需要做出表率。比起一個有想法、敢作為的皇帝,文官集團更需要一個守制遵法的吉祥物。申時行被逼退也意味著爭國本事件的雙方進入白熱化階段,而內閣首輔便是中間的連接處也是緩沖帶,王家屏上任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上任之后首先也是必須解決的必然是冊立皇位繼承人的問題。
于是他接連四次上疏神宗,表達了他的立場以及觀點:“今五年矣,諸臣以為請皇上又不許也......而身為輔弼之臣,不能勸上早定大計方且為眾所疑為眾所詆。”[8]在王家屏及諸臣的再三請求下,為了讓自己不變得孤立,也為了堵住眾人尤其是科道官的嘴,神宗口頭上許下了明年舉行冊立的承諾。
萬歷二十年(1592),神宗的長子朱常洛已經十一歲,于是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同六科諸臣上疏催促神宗早日批準舉行豫教之典,這使得神宗勃然大怒,找出其奏疏中因不小心誤寫了“弘治”年號,以此為借口給這些諫官扣上了侮辱君上的帽子,為首的貶黜外地,其余的扣六個月的俸祿。之后申救他們的官員也受到了嚴厲的懲處,王家屏責無旁貸,立即封還御批:“詳閱疏詞第請諭教非請冊立,皇上念諭教當早宜納其言,即不然宜貸其過,而遽加降罰竊恐轉滋爭論煩聒無寧時。”[9]王家屏以彼之道還之彼身,從奏疏中摳出群臣只是請諭教并沒有直言冊立這一關鍵點,說明了李獻可等人從原則上并沒有違反神宗的命令,從輕處罰是最明智的決定。神宗此舉引起極大的爭議,這讓王家屏更加難以從中調停,只好以退為進,讓神宗體諒自己的苦衷:“謹奏為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事。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廟享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10]王家屏引用漢汲黯例子,也希望神宗不嫌棄自己的逆耳忠言,從此振作精神,改變當前的政治狀況,并希望神宗能夠像漢武帝一樣禮賢納諫,從而早日確定儲君,穩定政局,讓自己能夠更好的發揮作用,君臣共同開創宏圖盛世。
嚴懲的指令一旦下發,身為輔弼的王家屏必然成為群臣攻擊的對象,且神宗一拖再拖,還小題大作,王家屏不惜屢次以辭職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但句句肺腑之言也沒能夠改變神宗的孤注一擲,接下來牽連了更多的人,也讓兩人的矛盾升級。“名,非臣所敢棄......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為。”[11]王家屏堅守自己的名節,不愿以阿諛奉承換取現實利益,這讓神宗與他在冊立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
之后的王家屏因積勞成疾,身體每況愈下,各種不利因素消耗著他堅守崗位的信心,而神宗也對于他的堅持沒有給予肯定,反而日加冷淡,“上益不悅,遣內史至其邸,責以徑激駁御批,故激主怒。”[11]神宗的言行擊碎了王家屏盡忠職守的一片赤誠之心,也終結了他幾十年的政治生命。“伏望皇上......嘗于九廟視朝聽講一如萬歷之初年......惟是皇儲冊立之儀系宗社根本之計。”[12]在離開京城之際,王家屏仍不忘國事,提出許多有建設性意義的施政方略,比如整頓吏治,修備邊防,改善水利,評判要略。言簡意賅,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朝政的關心和留戀,并希望神宗能像早期一樣勤理朝政。
2.下野之后對輿論的影響。
王家屏從萬歷二十年(1592年)罷歸,在家賦閑,“憲成舉王家屏,而家屏以爭國本去,上意雅不欲用。”[13]憑借在官場建立的良好的人際關系以及王家屏自身剛正不阿的秉性,之后屢次有人建議重新啟用他,但是未能如愿。萬歷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顧憲成推舉王家屏重新入閣,引起神宗的不滿,導致顧憲成被削籍謫歸。顧憲成回鄉后,和高攀龍等人講學于東林書院,諷議時政,品評人物,整個國家的政治風氣也受其影響,也是東林黨逐漸走上政治舞臺的開端。
而王家屏的離去也使得后繼的王錫爵及朝官迷失了斗爭的方向,在冊立的態度上產生的分歧,后來的王錫爵偏向與皇帝妥協這一立場,提出“三王并封”之說,就是將長子朱長洛,三子常洵、五子常誥同封為藩王,這顯然與之前神宗許諾的定期冊立太子相差甚遠,當然這正中神宗下懷,這樣便可使冊立問題再延期以待轉機,雖然此舉得到神宗的首肯,卻難平群臣的竭力反對,最終作罷,王錫爵的仕途也因此迅速結束。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紛爭許久的爭國本事件最終落下帷幕,十月,神宗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已經六十六歲高齡的王家屏得知后,十分高興,上疏表示慶賀,神宗皇帝念及當初家屏的功勞,專門派遣使者表示慰問。“閱八年,儲位始定。遣官赍敕存問,賚金幣羊酒。”[14]
“爭國本”事件表面上是皇帝家務的內部紛爭,實際則是神宗想跨越文官集團而實現自己意志的一次嘗試,即皇權不斷強化的過程,之后的礦監、稅使的泛濫也是這一意志的體現。這一過程像一場拔河比賽,另一端的文官集團始終做著不懈的斗爭。王家屏作為神宗朝眾多輔弼大臣中的一位,他不可能徹底扭轉這一趨勢,這一趨勢實際上是不可阻擋的,這也是后世許多對于王家屏的評價限于“愚忠”這一層面的原因。而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必須要考慮到歷史條件的局限性,正是有像王家屏這樣的人不畏強權,敢于為捍衛禮法而奮起,中華民族的精神才能經久不衰,中華文明才能自豪地稱自己為“禮樂文明”,我認為王家屏的精神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
注釋:
[1]于慎行:《谷城山館文集》卷17《少保王文端公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7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62頁.
[2]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45《內閣輔臣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44頁.
[3]張廷玉:《明史》卷217《王家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727頁.
[4]《明史》卷234《雒于仁傳》,第6101頁.
[5]《明神宗實錄》卷218,臺北,中央研究院,1962年版,第196頁.
[6]《王文端公奏疏》卷1《申救大理寺評事雒于仁疏》,第488頁.
[7]《王文端公奏疏》卷3《請敦趣給假輔臣還朝揭》,第515頁.
[8]《王文端公奏疏》卷2《請冊立揭》,第502頁.
[9]《明神宗實錄》卷244,第383頁.
[10]《王文端公奏疏》卷4《乞罷歸以全臣節疏》,第528頁.
[11]《明史》卷217《王家屏傳》,第5730頁.
[12]《王文端公奏疏》卷4《辭朝疏》,第535頁.
[13]夏燮:《明通鑒》卷70《紀七十·神宗萬歷二十二年》,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81頁.
[14]《明史》卷217《王家屏傳》,第57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