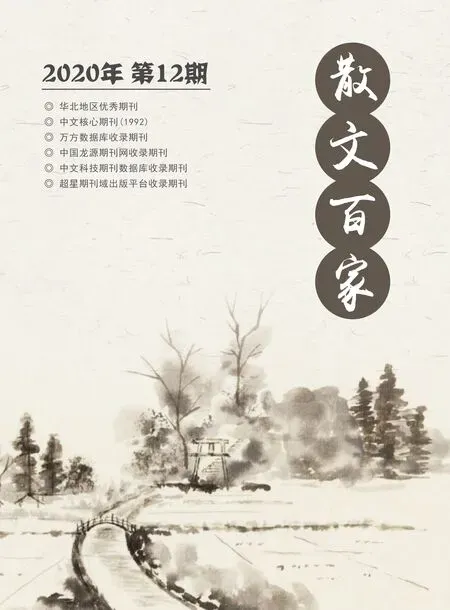符號文本的雙向建構(gòu)
——重讀《特別響,非常近》
蔣一鳴
上海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
回首21世紀(jì)的頭10年,最有影響的國際大事莫過于2001年的美國“9.11”事件。“9.11”事件不僅直接導(dǎo)致美國的歷史、文化裂變?yōu)樗^的“前9.11”時代與“后9.11”時代,恐怖襲擊與反恐戰(zhàn)爭也因此成了國際社會最為關(guān)注的焦點。文學(xué)是時代的反映。但是小說追蹤這一時代大事的步伐不僅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各色傳媒,也跟不上其它文學(xué)門類。
遲至今天,很多人對“9.11”的認(rèn)識仍舊停留在個人和集體意識中的情感層面,并未對這一事件獲得清晰透徹的認(rèn)知。小說家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對時事問題進(jìn)行消化、反芻和新陳代謝。很多大名鼎鼎的小說家至今不敢涉足“9.11”,是因為他們擔(dān)心自己的認(rèn)知存在錯誤,或不夠完整,難免導(dǎo)致錯誤的或不完美的再現(xiàn),寫出蹩腳的作品。
盡管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仍有幾十位功成名就或初出茅廬的小說家鋌而走險。美國作家喬納森.薩弗蘭.福爾的《特別響,非常近》便是一部廣受贊譽(yù)的后“9.11”小說。福爾在書中運(yùn)用了語言符號以及多種多樣的圖片,彩筆涂鴉等非語言文字符號,構(gòu)建了具有多重意義維度的小說空間。
本文將從符號敘述學(xué)角度出發(fā),從敘述主體和敘述接受者兩個維度研究福爾的小說是如何敘述和如何為閱讀者所“二次敘述”的。在符號文本敘述和符號文本接受的張力中,小說又是如何參與到“9.11”歷史事件書寫當(dāng)中去的。
一、符號與符號敘述學(xué)
1.何為符號。
著名符號學(xué)家皮爾斯認(rèn)為整個世界是淹沒在符號之中的。這句著名的論斷指出了符號在人類認(rèn)識和表征世界方面的重要作用。
符號是什么?著名符號學(xué)家趙毅衡認(rèn)為“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趙毅衡1)。文化學(xué)者霍爾則認(rèn)為“我們用于表述帶有意義的詞語、聲音或形象的總的術(shù)語是符號”(霍爾24)。對此趙毅衡又進(jìn)一步做出了補(bǔ)充說明;“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dá),符號的用途是表達(dá)意義。反過來說,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dá),也沒有不表達(dá)意義的符號”(趙毅衡2)。趙毅衡在這里想表達(dá)的是符號與意義的鎖合關(guān)系。符號不僅是表達(dá)意義的工具與載體,而且符號還是意義的條件。有了符號才能進(jìn)行意義活動。德里達(dá)也說過,“從本質(zhì)上講,不可能有無意義的符號,也不能有無所指的能指”(德里達(dá)20)。
由此我們得出結(jié)論,想要了解符號,我們必須了解定義“意義”。判明一個事物是有意義的,就是說它是引發(fā)解釋的,可以解釋的。而一切可以解釋出意義的事物都是符號。至此意義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定義,“意義就是一個符號可以被另外符號解釋的潛力,解釋就是意義的實現(xiàn)”(趙毅衡2)。當(dāng)然這個定義也可以進(jìn)一步推導(dǎo),即“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解釋,也沒有不解釋意義的符號。一個意義包括發(fā)出(表達(dá))與接受(解釋)這兩個基本環(huán)節(jié)。這兩個環(huán)節(jié)都必須用符號才能完成。符號與意義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是符號學(xué)最基本的出發(fā)點。
2.符號文本與解釋。
了解了符號與意義鎖合關(guān)系之后,如何將符號用于到“文本”闡釋中去是符號研究者要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中文中的“文本”一詞是由英文翻譯而來。在文學(xué)理論中,“文本”是任何可以“閱讀”的對象,無論該對象是文學(xué)作品,路牌,城市街區(qū)的建筑物排列還是服裝樣式。它是一組連貫的符號,可以傳遞某種信息。這組符號是根據(jù)信息性消息的內(nèi)容來考慮的,而不是根據(jù)其物理形式或表示它的介質(zhì)來考慮的。“文本”是符號的組合,是符號用以表征的一種形式。符號與意義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文本”也是如此。“文本”的創(chuàng)立在于表意,而意義也憑借“文本”,這一更具效率的符號表意形式,解釋事物,影響認(rèn)知。艾柯看出了“文本”與解釋之間的循環(huán)。他認(rèn)為“文本不只是一個用以判斷解釋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釋在論證自己合法性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一個客體”(艾柯78)。也就是說,文本是解釋是為了自圓其說而建立起來的,它的意義原來并不具有充分性。艾柯認(rèn)為這是一個解釋的循環(huán),因為“被證明的東西成為了證明的前提”(艾柯78)。趙毅衡對此得出的結(jié)論是“有了意義的追求,才有意義;有解釋,才能構(gòu)成符號文本”(趙毅衡4)。簡單來說就是在追求意義的過程中,人類自覺地通過符號表達(dá)意義,傳遞意義。而在解釋意義的過程中,符號相應(yīng)的建立起一個闡釋意義的文本空間。以此類推,文學(xué)文本也是文本的一種,因此考察文學(xué)文本的意義需要從文學(xué)文本中的諸符號著手。在后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中,傳統(tǒng)語言符號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作家們開始使用多種不同的符號,例如:圖片,數(shù)字等來追求意義的表達(dá)。在這樣一個意義的追求過程,又構(gòu)建了多維符號組成的豐富文本空間。豐富的文本空間又為意義提供了巨大的闡釋空間。在小說《特別響,非常近》中,福爾同樣運(yùn)用了多種形式的符號,包括語言符號和大量非語言符號,試圖在一個后“9.11”時代構(gòu)建起一個對“9.11”歷史事件的闡意空間。
3.敘述轉(zhuǎn)向與符號敘述。
敘述轉(zhuǎn)向的大潮,始自二十世紀(jì)七八十年代的歷史學(xué)。海登.懷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學(xué)》,推動用敘述研究改造歷史學(xué)的“新歷史主義”運(yùn)動。此后,閔克、格林布拉特、丹圖等人進(jìn)一步加以哲理化。閔克1987年的著作《歷史理解》清晰地總結(jié)了新歷史主義的敘述觀,使整個運(yùn)動的影響溢出歷史學(xué),沖擊了整個人文學(xué)科。
在符號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同樣也出現(xiàn)了“敘述轉(zhuǎn)向”。一些以往不認(rèn)為是敘述的符號文本,現(xiàn)在被認(rèn)為是具有敘述性。因此對于敘述文本的概念需要重新定義。對于敘述學(xué)界的混亂局面,趙毅衡提出將敘述成立的條件歸結(jié)為“由特定主體進(jìn)行的兩個敘述化過程”:(1)某個主體把有人物參與的事件組織進(jìn)一個符號文本中。(2)此文本可以被被接收者理解為具有時間和意義的向度。
趙毅衡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而提出,“任何一個敘述文本必須包含特定的敘述主體和接收者”(趙毅衡7)。具有敘述性質(zhì)的符號文本必定是由某個主體有意圖組成的文本,該文本攜帶了各種意義,需要接收者的理解和重構(gòu)加以實現(xiàn)。在這里趙毅衡強(qiáng)調(diào)了敘述的雙向建構(gòu),即敘述主體的建構(gòu)和敘述接收者的建構(gòu)。兩者的互相配合,共同建構(gòu)了文本的敘述性。
二、《特別響.非常近》中敘述主體對文本的建構(gòu)
1.敘述主體之爭。
2001年,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使得剛進(jìn)入21世紀(jì)的美國社會陷入一片混亂。“9.11”是繼二戰(zhàn)中珍珠港被日軍偷襲后美國本土首次遭遇的外敵襲擊。該事件給美國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chuàng)傷。隨后,美國社會和第三世界國家對“9.11”事件都有很多反思,作家們試圖從多方面對這一事件及其對各自社會和文化的沖擊進(jìn)行描述,從而涌現(xiàn)出大量反映“9.11”事件的作品,被稱為“9.11”文學(xué),或后“9.11”文學(xué)。如果按照虛構(gòu)性和記實性劃分?jǐn)⑹鑫谋荆瑲v史學(xué)家對于“9.11”的敘述屬于記實性文本,而以福爾的小說《特別響.非常近》為代表的“9.11”小說則屬于虛構(gòu)性文本。但是符號文本的底線是“事實性”,不然符號接收者沒有接受的理由。
趙毅衡認(rèn)為,“虛構(gòu)文本必須在文本主體之外,構(gòu)筑另一對文本主體,它們之間能做一個事實性文本的傳遞”(趙毅衡323)。小說的作者只是引錄一個特殊發(fā)送者(小說中的敘述者)對一個特殊人物(聽故事的人,即“受述者”)所講的“代理事實的故事”。
這樣符號文本的發(fā)送者產(chǎn)生了分裂。一個是作者,一個是代理的符號發(fā)送者即小說中的敘述者。在小說中,我們一般將代理的符號發(fā)送者稱為敘述主體。這是將符號發(fā)送者置于虛構(gòu)文本情景下的考慮。如果我們將小說《特別響.非常近》視為一個攜帶意義的符號敘述文本的話,那么該文本發(fā)送者不是作者福爾,而是小說中的敘述主體,即奧斯卡、奧斯卡的爺爺和奧斯卡的奶奶。作者借由他們之口,講述了一個在戰(zhàn)爭和“9.11”事件中飽受摧殘的創(chuàng)傷故事。
2.敘述主體對文本的建構(gòu)。
在文本層面,作者將敘述的大旗交給了敘述主體,由敘述主體代為行使敘述之職。在小說《特別響.非常近》中,敘述主體顯然不止一個。從章節(jié)目錄可以看出來,有幾個標(biāo)題重復(fù)出現(xiàn),即“我的情感”和“為何我不在你身邊”。在以“為何我不在你身邊”為題的章節(jié)中,敘述主體為奧斯卡的爺爺老托馬斯,是第一人稱敘述。在“我的情感”為標(biāo)題的章節(jié)中,敘述主體是奧斯卡的奶奶,也是第一人稱敘述。其余章節(jié)均由奧斯卡擔(dān)任敘事行為的主體。
在奧斯卡敘述的部分,敘述主體奧斯卡以一個兒童的視角回溯“9.11”事件中如何失去父親,如何與自己和解的心路歷程。在奧斯卡的敘述部分,作者與敘述主體之間的分裂是最為明顯的。福爾作為一名成年作家與小說主人公奧斯卡之間的身份差異無疑是巨大的。許多評論家因此質(zhì)疑福爾小說敘述的可靠性。事實上作家有權(quán)利選擇任何他認(rèn)為合適的代理敘述者,這是小說這一虛構(gòu)文本賦予作者的權(quán)力與自由。最關(guān)鍵的部分在于敘述主體所傳遞的信息是否準(zhǔn)確真實。
奧斯卡作為小說中的一個獨(dú)特的敘述主體,他對于“9.11”事件和在事件中失去父親的經(jīng)歷有著自己獨(dú)特的體悟。小說開篇就是奧斯卡的一段類似“白日夢”的內(nèi)心獨(dú)白:“要不要發(fā)明一種茶壺?茶壺嘴在冒熱氣的時候可以張開,合上,所以它能變成一張嘴……”(福爾1)這段“白日夢”般的內(nèi)心獨(dú)白似乎和小說整體的敘述無關(guān)。但是敘述主體發(fā)送的信息應(yīng)與敘述主體自身相符合。奧斯卡是一位未成年的兒童,他的生活閱歷和他的知識水平,讓他無法深入表述“9.11”事件的意義。奧斯卡以兒童的眼光去觀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間,從而打造出一個非常別致的世界,展現(xiàn)不易被成人所體察的原生態(tài)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種面貌。奧斯卡天馬行空的想象,朦朧的性意識,符合一個8歲兒童的心理世界。作者借由奧斯卡這個兒童敘述主體,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兒童的視角。通過孩子另一種眼光的觀察和透視,表現(xiàn)與兒童感知發(fā)生聯(lián)系的那部分現(xiàn)實生活景觀,揭示了成人所難以體察到的生存世界的可能面貌。
小說的另外兩個敘述主體是奧斯卡的爺爺和奶奶。這兩個敘述主體分別從男女兩性的不同角度敘述德累斯頓轟炸和“9.11”事件,敘述視角互為補(bǔ)充。
奧斯卡的爺爺老托馬斯在德累斯頓轟炸之后得了失語癥。他只能通過手上紋出的“是”和“否”兩個字和記有簡單日常用語的記事本和他人進(jìn)行最基本的溝通。他會在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和人交流,但他會選擇英語而非母語德語交流,試圖與過去的經(jīng)歷隔絕。在由奧斯卡爺爺為敘述主體的部分,他選擇通過信件的形式進(jìn)行敘述。不同與以往的書信體小說,在《特別響.非常近》中,書信是小說敘述形式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這從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小說的敘述形式,使小說具有多重文體特征。書信在書寫之初就有明確的信息接受對象。在小說文本中,信件的接收者是奧斯卡的爸爸,但小說自始至終奧斯卡的爸爸都沒有收到那些信。敘述主體借由書信這一敘述形式進(jìn)行的敘述文本缺少了信息的接收對象,信件這一文體所預(yù)設(shè)的雙向交流被無限擱置,敘述主體的交流對象重新指向了敘述主體自身。這樣,書信這一敘述形式成了一個空殼,它所預(yù)設(shè)的交流方式并沒有得到實現(xiàn)。因此,敘述主體所建構(gòu)的敘述文本成為了一種類似自我懺悔式的敘述文本。在小說267頁上,只有區(qū)區(qū)幾個字“我不能說話,對不起”(福爾267)。敘述主體老托馬斯通過寫信這一敘述行為,擺脫了自我封閉的內(nèi)心世界,逐漸打開心扉。敘述主體托馬斯給小說文本提供了一個自我反思的視角,從德累斯頓轟炸和“9.11”事件親歷者的角度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有創(chuàng)傷與救贖的故事。
奧斯卡的奶奶是老托馬斯昔日戀人安娜的妹妹。對于老托馬斯而言,她更像是安娜的替代品。奧斯卡的奶奶在敘述中采用了左對齊排版。左對齊排版并不符合常人的閱讀習(xí)慣,但是卻和敘述主體的認(rèn)知和表達(dá)習(xí)慣相符合。在奧斯卡的敘述部分,奧斯卡的奶奶以一種奇異的方式守護(hù)著孫子。她住在孫子的對樓,他們之間會通過對講機(jī)交流,保持著一種親切的距離感。她織毛衣時會把毛線的一頭栓在奧斯卡身上,生怕孫子丟失。戰(zhàn)爭帶來的強(qiáng)烈心理沖擊雖然沒有帶來像老托馬斯那樣嚴(yán)重的失語癥,但在奶奶的世界中,她努力的拼接出一個完整的認(rèn)識世界,最顯著的體現(xiàn)就在她的左對齊排版上。左對齊排版是奶奶這個敘述主體基于自身認(rèn)知和表達(dá)方式的選擇,符合人物的經(jīng)歷和表達(dá)習(xí)慣。
在小說中福爾借由不同的敘述主體,用符合敘述主體的敘述視角和敘述形式構(gòu)建敘述文本,豐富了“9.11”的創(chuàng)傷表達(dá),構(gòu)建了富有多層意蘊(yùn)的敘述文本空間。
三、《特別響.非常近》的敘述接收者對文本的建構(gòu)
1.二次敘述化和能動的敘述接收者。
一次敘述化,簡稱敘述化,發(fā)生于敘述主體對文本的建構(gòu)過程中。二次敘述化,發(fā)生于文本接受過程中。只有敘述化,只有敘述文本,而沒有接收者的二次敘述化,文本就沒有完成敘述傳達(dá)過程,任何文本必須經(jīng)過二次敘述化,才能最后成為敘述文本。這個過程“不僅僅是理解敘述文本,也并不是回顧情節(jié),而是追溯情節(jié)的意義”(趙毅衡106)。
《特別響.非常近》中繁復(fù)的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組成了一個符號文本,敘述主體敘述的情節(jié)和人物使得符號文本經(jīng)歷了第一次敘述化。這只能說明該敘述文本具有可以被理解為敘述的潛力,也就是被“讀出故事”的潛力。小說中同時還存在許多非語言符號,例如涂鴉和排列混亂的圖片等。這些非語言符號似乎無情節(jié)的進(jìn)展。趙毅衡認(rèn)為“單個的接受者是一個充分的主體,一個充分的主體有自主的自由”(趙毅衡12)。因此,單幅圖像不能敘述情節(jié)的觀點事實上忽略了“敘述接收者構(gòu)筑情節(jié)的能力”(趙毅衡11)。在這里,符號的接收者和符號的發(fā)送者處于平等的位置,符號的接收者也積極地參與到了信息傳遞和意義表達(dá)的活動中。
2.創(chuàng)造式二次敘述與“9.11”事件書寫。
在小說《特別響.非常近》中,各種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交織纏繞。小說內(nèi)部的時間呈非線性發(fā)展,敘述因果和邏輯鏈也很混亂。小說的閱讀者無法按照常規(guī)邏輯對文本進(jìn)行建構(gòu),可能會中斷二次敘述。但是沒有接受環(huán)節(jié),符號文本就不能成立。這時,閱讀者必須憑借文本提供的少量線索,給予文本以創(chuàng)造空間。這個過程被稱為創(chuàng)造式二次敘述。
對于福爾小說的閱讀者來說,小說中的突然出現(xiàn)的圖片和雜亂的涂鴉令人費(fèi)解。圖片符號并不能主動敘述情節(jié),所以依靠信息接收者的二次敘述賦予圖片以敘述性。我們在進(jìn)行創(chuàng)造式二次敘述的時候要將非語言文本和語言文本比較對照,要從整個敘述文本的角度來考察。
在小說中,奧斯卡有一本題為《發(fā)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圖片剪貼簿,里面裝有各種各樣的圖片,有的是他收集的,有的是用他爺爺?shù)南鄼C(jī)拍攝的。翻開小說,這些看似雜亂的圖片躍然紙上:霍金的照片、哈姆雷特劇照、烏龜交配圖、寶石盒、墜落的人、紐約與中央公園俯瞰圖、空中飛鳥、鑰匙、門鎖、門把手、掛在墻上密密麻麻的鑰匙、各種標(biāo)有編號的指紋印、裸體猿人情侶、流淚的大象、人頭的后腦像、空中墜落的貓、過山車、彩筆書寫的英文字母、寫有“是”與“否”的左右手、旋轉(zhuǎn)門、以及公寓外墻等,共計有60張之多。這些圖片符號散落在小說的語言符號文本之中,與語言符號敘述的文本相呼應(yīng)。
圖片符號記錄了奧斯卡的生活,是奧斯卡用于認(rèn)知、接觸世界的途徑與方式。當(dāng)奧斯卡在翻閱自己制作的剪貼簿的時候,小說的讀者實際上也跟他一起瀏覽這些圖片。在這個能動的圖片符號接收過程中,閱讀者在瀏覽閱讀中闡釋那些圖片,逐步了解奧斯卡的內(nèi)心世界。這樣零散的圖片符號就形成了一個有意義且松散敘述文本,讀者通過零散的圖片文本,還原了主人公奧斯卡天馬行空的內(nèi)心世界。
在創(chuàng)造式二次敘述中,不同形式的符號并沒有從屬關(guān)系。語言文本和圖像文本共同構(gòu)筑了敘述性的符號文本。
與此同時小說中還出現(xiàn)了一些重復(fù)的圖像符號。在老托馬斯的信件中鑰匙、門鎖、門把手的圖片反復(fù)出現(xiàn)。“鎖”意味著封閉的內(nèi)心,開“鎖”意味著打開封閉的內(nèi)心。語言符號文本中主人公封閉的內(nèi)心與圖片符號中的“鎖”形成了有趣的呼應(yīng)。對于讀者來說,門鎖的圖片也可以看成是語言符號中敘述情節(jié)的實體化,甚至比語言符號更具有視覺上的沖擊力。閱讀者在閱讀中,自覺將圖片符號與語言符號結(jié)合起來。圖片文本因此也參與到了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過程中。“鎖”不僅是奧斯卡的尋“鎖”之旅,更暗示了爺爺?shù)膶ぁ版i”之旅。對于閱讀者來說,他們也參與到了這場尋“鎖”之旅中去。
“9.11”是一個極限事件,它粉碎了文化中的象征之源,打垮了意義生成和語義學(xué)的正常過程,因此被認(rèn)為是“語言邊界之外的”創(chuàng)傷性事件。但“9.11事件”的創(chuàng)傷效果一方面阻隔了語言的意指功能,另一方面?zhèn)€體卻需要憑借敘述和指號過程來尋求創(chuàng)傷的治愈。所以,“9.11小說”的創(chuàng)傷敘事就不僅僅是一種再現(xiàn),而變成了一種治療的文本,它旨在通過講述來緩解焦慮,甚至修復(fù)創(chuàng)傷所導(dǎo)致的語言斷鏈。而且,作為一次被全球見證和分享的間接“9.11事件”所導(dǎo)致的創(chuàng)傷亦是全球性的,所有人都需要去理解、去解釋和去恢復(fù)。
對于《特別響,非常近》的讀者來說,他們積極參與到了符號文本的二次敘述之中去,并對符號文本進(jìn)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建構(gòu)。在這個創(chuàng)造性的建構(gòu)過程中,他們得以潛文本底部,與遭受“9.11”重創(chuàng)的主人公一起體會災(zāi)難降臨之后的生活,深入他們的內(nèi)心,治愈災(zāi)難過后的心靈重創(chuàng)。
四、結(jié)語
在小說《特別響.非常近》中,作者福爾別出心裁,采用了多種不同形式的符號,敘述了一個在“9.11”事件中飽受心靈創(chuàng)傷的故事。小說中的敘述主體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建構(gòu)了一個多重意蘊(yùn)的“9.11”小說文本。對于閱讀者來說,他們根據(jù)圖片符號與語言符號之間的隱秘聯(lián)系,對文本進(jìn)行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建構(gòu)。在建構(gòu)過程中,他們與人物一起重新回顧了“9.11”事件,試圖在這個創(chuàng)傷文本中,尋找自我療愈的可能。福爾放棄了傳統(tǒng)作者高高在上的敘述權(quán)威,邀請閱讀者進(jìn)入文本的建構(gòu)和釋義環(huán)節(jié)。這種擁抱平等的對話姿態(tài)讓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