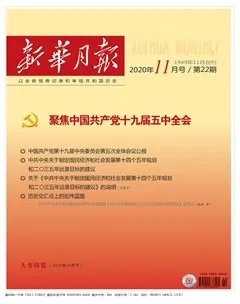古典文明如何孕育現代科學
陳芝
吳國盛的《什么是科學》一書,是非常好的科普讀物,深入淺出的講述科學的起源、歷史與精神。讀者在閱讀完作者的剖析后會發現,所謂的科學是西方世界獨有的產物,其形成與發展仰仗西方獨一無二的社會—文化結構,人類大多數文明缺乏這些要素,因此無法誕生科學。本書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作者更多的是從思想史的角度進行梳理,相對缺乏社會史的理解。
在本書的開篇,作者便強調西方語境中,科學有狹義與廣義之分,英語與法語的science代表了狹義的科學,即引進數學工具,注重實驗,可觀察可重復可實證的現代經驗科學;德語的Wissenschaft則代表了廣義的科學,即希臘以來對事物系統的理性探究,追求確定性、可靠性知識的體系。這個意義上的科學,在古希臘是數學和哲學,在中世紀加入了神學,在現代又加上了現代科學。狹義的現代科學與傳統科學相比,剔除了神學,以數學為根基,處理的是傳統上由自然哲學負責的內容。
無論哪種科學都必須溯及古希臘,而對于古希臘人來說,追求科學知識就是追求自由。與現代人相比,古希臘人沒有私人自由的概念,只有不屈從于他人的政治/公共自由和認識必然性的心靈自由,科學知識帶來的自由指的就是后者,同時這又是按照前者形塑的。
波普爾認為,伯利克里前后的幾代希臘人,處在一個不斷革命、動蕩與戰爭的社會環境中,對現實的厭棄,促使他們去追求一個永恒不變的美好世界。永恒不變的事物為什么值得追求,因為它獨立不依,自主自足,是“自由”的終極保證,就像自由人不從屬于他人一樣,只有通過永恒的事物,人才能確定自身的存在,不會因世間的動蕩而迷失自己、感到恐懼,才能獲得心靈上的自由和寧靜。
由于認為永恒的事物就是好的,是至真至善至美,因此所謂的科學知識,對古希臘人來說專指事物的本質,必須是確定性的,不夠確定的,被柏拉圖輕蔑地認為只是一種意見,而人的意見是會變來變去的。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即知識,即正義。

于是古希臘人形成了一種追求確定性的理性主義傳統,任何事物都有“本性”(nature),“本性”是屬于事物自己的。追求事物的“本質”就是追究事物的“自己”,這是理性的內在性原則,即從事物自身中為它的存在尋求根據。因此,自由就是自知,就是認識你自己。
用科學史家勞埃德的話來說,希臘人就此發明了自然nature這一概念,這一概念在中國古代沒有對應物,古代漢語里“自然”是兩個詞,合一起意思是自己如此,后來被日本人拿來翻譯英文里的nature,是舊瓶裝新酒的產物。
所謂自然的發明,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希臘人發明了以追究“本質”的方式對存在者的存在進行把握的理性思維,標志理性科學的誕生。其次,希臘人開辟了一個特定的存在者領域,即“自然界”(自然物的世界)。
前者意味著形而上學的誕生,和西方文化對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本質和之所以表現如是的內在原因不斷追問的熱忱和傳統。這是這一發明最重要的地方:在古希臘人以前,知識的增長來自瞎貓碰到死耗子茫無目的一點一滴的積累,人們缺乏從現象中發現一般規律的動力和興趣。只有從古希臘人開始,人們才主動從現象中尋求本質,再用一般推衍出新的個別。
后者先是意味著“事物自身”與“事物”分裂,在事物的世界之外另有一個理據的世界,即主客兩分,將天地萬物視作獨立于人的客觀對象——在希臘和希臘繼承者以外的社會里人們處在交感巫術的支配中,相信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后是內在根據的“自然物”和外在根據的“人造物”的分離。
在本書作者看來,沒有自然的發明,就沒有理性科學。而這種追求自由/自己的學術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一,希臘科學純粹為“自身”而存在,缺乏功利和實用的目的。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我們追求它并不是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唯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而如果任何知識若是成為實現他者的手段和工具,就不是純粹為著“自己”的知識,因而也就不是自由的知識,學習這樣的知識,就不能起到教化自由人性的作用。
其二,發達的演繹科學,不借助外部經驗,純粹依靠內在演繹來發展“自身”。希臘人的知識構建通過推理、證明、演繹來進行,而所謂證明、演繹,只是順從“自身”的內在邏輯而已。古希臘人最發達的兩門學問:數學與哲學,都可以不假外求,從一個個概念開始,不斷推衍、擴展。
之前提到,古希臘人只對確定性知識感興趣,因為這是永恒且自由的,外部經驗對他們來說變來變去,不值得追求與引用。因此相對于同時研究概念與現象,掌握邏輯演繹與經驗歸納的現代科學相比,存在嚴重的局限性。
盡管如此,古希臘依舊有結合數學演繹和經驗觀察的學術范式,那就是托勒密的天文學體系,這一學說在建立理論的過程中,自始至終使用數學工具去研究、證明與解釋現象,開創了現代科學的先河。由于受到意識形態的污染,托勒密被今天的大眾理解成一個丑角,但他的“地心說”理論之精巧,要到理論誕生1300年后也就是哥白尼時代歐洲人才掌握了足夠的數學水平去改造和推翻它,明清之際天主教傳教士將當時這已過時的體系帶到中國,依舊能令本土的天文學家們紛紛為之折服。
而現代科學革命,往往也是從哥白尼對托勒密的繼承算起,只不過我們不能無視中世紀的作用。中世紀對科學的影響,首先是在組織上,一個是大學一個是行會——后者作者沒有詳細講,本文認為有必要補充一下——兩者與十一世紀前后復興的自治城市一樣,最大的特征便是從領主手上獲得特許證,自我治理,有自己的法庭。
人類歷史上曾誕生過許多高等學校,但都不像西歐大學這種類型的學術組織那樣,有至今一千年左右的學生或教師自治傳統。由于中世紀政治破碎,大學有很強的獨立性,可以從封建君主、教會領主乃至共和城邦等勢力的爭斗中左右逢源,獲得特權,因此“藏污納垢,包含種種異端邪說”。
行會有著大學類似的特權,而大學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學生或教師行會。中世紀各自治城市的各行會一方面有自治權,并且人們是通過行會來參與城市政治,另一方面有意識的控制成員人數,使加入的成員有生活保障,無后顧之憂。
他們不必考慮商品的售賣,一心一意投入技術研究當中,數百年積累下來使得中世紀結束后16、17世紀的歐洲在大多數技術領域,尤其是機械領域都是世界領先地位,并且在很早的時候就已超越希臘羅馬人,兩次工業革命首先也是從機械的進步開始 (像紡紗機、蒸汽機、內燃機等)。這一方面為同時期的現代科學革命提供了技術支持,另一方面也影響了科學家對世界的認知。
最后是經院哲學的出現,與托勒密相似,這一范式體系在過去也受到了過多的污名化,以至于忽略了它的重要性。經院哲學是中世紀中后期對古典世界遺產,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學術吸收消化的產物。雖然具體內容非常繁瑣,在神學家以外的人看來相當無聊,但它的成型意味著一千年后,歐洲人終于在思辨上重新達到了希臘人水平,將神學提高到與古希臘哲學相當的程度,為超越它奠定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古典世界的繼承者,拜占庭一直是死氣沉沉的僵尸不提也罷,像伊斯蘭曾經是歐洲的導師,最終也遺憾的停滯不前,別說超越希臘人。
不過,單從經院哲學也無法導向現代經驗科學,因為神學家處理的內容同樣與經驗無關。但經院哲學內部的異端唯名論派解構了主流唯實論派所建立的理性化世界,否定了共相的存在,將上帝從一個服從于自身理性的仁慈造物主,解釋成一個擁有完全自由,不受自然法則約束,甚至不受祂從前約定約束喜怒無常的暴君,個人的得救不再取決于人做善事的努力,而完全取決于上帝毫無征兆的恩典。
這種對神的看法把自然秩序變成了一連串混亂無序事物的總和,將唯實論建構的理性安寧的自然秩序化為齏粉,使人落到一個孤立不安缺乏希望和救贖的處境中來,尤其中世紀臨近結束之際,西歐正處在又一次的教會大分裂、黑死病和一連串戰爭當中,使唯名論充滿了說服力。
本書作者認為,為了應對和處理這一危機,于是有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現代科學。為了應對唯名論革命中人與上帝不可分割的鴻溝,一部分學者將人提高到與神明相當的位置,擁有自由和創造的意志,在征服和控制自然中顯示自己的力量,從而在唯名論所設定的混亂世界中保護自己、建立秩序,這一理論深刻地影響了現代科學。
我們可以看到,與希臘科學相比,現代科學呈現兩個不同的特點。第一,現代科學能轉化為技術和生產力,因為現代科學有意識的以征服和改造的姿態對待自然界。
基督教出現以后,歐洲人引進了意志自由的概念,即人本可以不做其做過的事情,如果人還是做了,那么人應當為自己做過的事負責。反之,人的行為如果不是基于自由選擇,那么就無責任可言。意志自由是一個神義論命題,為了解釋上帝既然全知全能全善,為什么創造的世界充滿不幸。護教學家辯護道,世界的災難來自亞當夏娃的自由意志,他們本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在伊甸園中,卻偏偏違逆上帝犯下了原罪。上帝的確能阻攔人類的犯罪,但祂認為人的自由意志更加重要。如果要消滅世間罪惡,就必須消滅自由意志,但消滅了自由意志,就無所謂善惡了。
而隨著唯名論將上帝改造成無所不能的隨其意志行動的暴君,自由意志的重點逐漸過渡到通過人的“行動”使自己的“意志”得以實現,伴隨著人類中心思潮的涌現,使這個無限的意志首先表現在對外界的征服和掌控上,而不是像希臘人那樣停留在觀察世界。再加上唯名論否定共相,否定自然物的自主性和內在根據,他們認為否則萬物就會自行其是,連上帝都奈何不得。由于這個唯名論的上帝能隨意改變任何事物的形式和本質,所以變化是最值得研究的事情,上帝就體現在自然的運動上,或者說,自然就是上帝的意志運動。這顛倒了希臘人的價值規范,使經驗而不是本質成為現代科學的研究重心,特別是歸納法和實驗法被總結出來,成為共識以后。
第二,現代科學大量使用數學,以至于一門學科的成熟程度取決于它使用數學的程度;而且正因為大量使用數學,現代科學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所向披靡。
古希臘對數學非常重視,但對他們來說數學與物理學是兩個分開的,數學的對象要么完全不運動(算術與幾何),要么參與永恒的圓周運動(天文學),而物理學是研究運動的學問。兩者的結合,一是來自經院哲學對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特別是運動理論的修正,二是高度數學化的力學脫穎而出,占據了新物理學的核心位置。
更重要的是,歐洲人改造了數學的概念。在古希臘人那里,數學的對象是一次抽象,數學中的概念都意指個體對象本身,是關于具體對象的概念。而從笛卡爾開始的現代數學概念所意指的是一般概念,是關于概念的概念。他所創立的解析幾何統一代數和幾何,把單位概念與具體圖形相分離,使之變成純粹的量的單元,這樣量的次方就是同類量,從而完成了幾何學的代數化。
在此基礎上,笛卡爾試圖將世界進行同質化處理,使不同性質的事物能夠被統一量化。這一方法被后繼者繼承,現代科學統一將質還原為量,宏觀還原為微觀,整體還原為局部,復雜還原為簡單,第二性的事物(顏色、聲音、味道)還原為第一性的東西(廣延、運動)。這一做法帶來了技術爆炸與生產力革命,通過數學化,世界更容易被理解和分析,世界重新回到了理性的軌道中來。
但諸事物之間質的差異被抹平,也導致了人與世界的疏離:事物的意義取決于它對人的意義,人成為一切意義的根源。但世界的無意義又消解了人存在本身的意義,人不再被賦予了一個既定的意義,意味著人必須為自己活著找到一個意義。而這對于被強行拖進現代世界的大多數人來說,是痛苦茫然,不知所措的。
(摘自8月10日《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