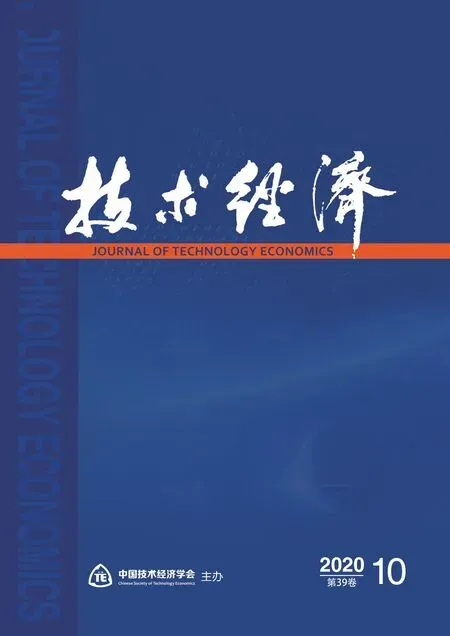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如何催生員工的知識(shí)共享?
(江南大學(xué)商學(xué)院,江蘇無錫 214122)
在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僅僅依靠傳統(tǒng)資產(chǎn)不再能保證組織的長期生存,人力資源作為重要的戰(zhàn)略資產(chǎn),對于提升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的意義已在理論與實(shí)踐界達(dá)成共識(shí)[1]。過去10 年,人力資源管理(HRM)領(lǐng)域主要集中于內(nèi)容型HRM 研究,考察人力資源實(shí)踐內(nèi)容本身的優(yōu)缺點(diǎn)如何影響企業(yè)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過程型HRM 研究,強(qiáng)調(diào)員工心理過程的重要性,認(rèn)為人力資源實(shí)踐的效果并不是按預(yù)期的設(shè)想自動(dòng)產(chǎn)生的,員工首先會(huì)先積極地感知、認(rèn)識(shí)、構(gòu)想和推斷人力資源實(shí)踐,繼而做出反應(yīng)[2]。
過程型HRM 研究以歸因理論為基礎(chǔ),提出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human resources attribution,HRA)的概念,以描述員工如何理解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施的動(dòng)機(jī)[3]。組織的整套HRM 實(shí)踐可以看作一個(gè)信號(hào)系統(tǒng),持續(xù)地向員工發(fā)送信號(hào)[4]。歸因是對信號(hào)的解讀,員工接收到組織的人力資源系統(tǒng)的信號(hào)后,可能認(rèn)為HRM 實(shí)踐(如績效工資)是為了員工福祉,產(chǎn)生承諾型HRA;也可能認(rèn)為是為了剝削員工,產(chǎn)生控制型HRA,經(jīng)歷信號(hào)編碼與接收的過程,同一套HRM 政策對于不同員工產(chǎn)生了差異化的效果。作為解開人力資源實(shí)踐與組織績效之間“黑箱”機(jī)制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近年來國外已有一系列研究對于HRA 如何影響員工態(tài)度與行為展開探索,Karina 和Beijer[5]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高績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tǒng)通過HRA 影響員工組織承諾;Chen 和Wang[6]研究顯示,HRA 通過組織支持感影響個(gè)體績效。
知識(shí)共享是組織知識(shí)管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提升企業(yè)績效和競爭優(yōu)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踐是影響員工知識(shí)共享行為的有效途徑,史富文[8]研究發(fā)現(xiàn),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踐對知識(shí)共享水平具有顯著影響。Flinchbaugh 等[9]實(shí)證研究指出,高承諾人力資源實(shí)踐顯著提升員工的知識(shí)共享行為。然而上述研究均為內(nèi)容型HRM 研究,考察HRM 本身的特點(diǎn)對于知識(shí)共享的影響,過程型HRM 研究幾乎沒有關(guān)注人力資源實(shí)踐如何影響組織知識(shí)管理能力。已有學(xué)者呼吁,與人力資源政策相關(guān)的心理變量對知識(shí)共享行為的影響需要進(jìn)一步探索[10]。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踐如何通過員工的主觀心理體驗(yàn)發(fā)揮作用,催生員工的知識(shí)分享行為?該問題成為本文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
知識(shí)經(jīng)濟(jì)為組織帶來的另一重大變化,反映在團(tuán)隊(duì)工作方面。隨著工作性質(zhì)的變化,僅憑一己之力已經(jīng)難以完成復(fù)雜性、挑戰(zhàn)性的任務(wù),團(tuán)隊(duì)取代個(gè)體成為工作組織的基本結(jié)構(gòu)單元。同時(shí),團(tuán)隊(duì)中的個(gè)體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角色和任務(wù)嵌入在團(tuán)隊(duì)中,團(tuán)隊(duì)成員為彼此提供必要的靈感、信息、資源和支持[11],成員之間的工作任務(wù)緊密相依,任務(wù)互依成為團(tuán)隊(duì)運(yùn)行過程中的一個(gè)重要任務(wù)情景。在高任務(wù)互依性的環(huán)境中,個(gè)體需要與其他團(tuán)隊(duì)成員進(jìn)行頻繁的交互,其任務(wù)的完成情況也受到其他成員的影響,團(tuán)隊(duì)中的成員對這一任務(wù)環(huán)境的感知又會(huì)如何影響知識(shí)共享過程?
由此,本文從社會(huì)認(rèn)同的理論視角,剖析員工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內(nèi)在機(jī)理,構(gòu)建被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模型,嘗試解答員工對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踐的動(dòng)機(jī)進(jìn)行判斷,如何影響其知識(shí)共享行為,同時(shí)探討任務(wù)互依性的調(diào)節(jié)作用,為企業(yè)的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踐提供參考。
一、理論基礎(chǔ)與研究假設(shè)
(一)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與知識(shí)共享
關(guān)于HRM 對于員工的作用,戰(zhàn)略人力資源管理領(lǐng)域一直存在著理念分歧。統(tǒng)一主義觀點(diǎn)認(rèn)為,組織的目標(biāo)和員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對組織好就是對員工好。高績效工作系統(tǒng)的部分研究發(fā)現(xiàn)支持了這一觀點(diǎn),Piening 等[12]研究發(fā)現(xiàn)員工感知到的高績效工作系統(tǒng)與個(gè)體的工作滿意度積極相關(guān)。相反,多元主義觀點(diǎn)認(rèn)為,企業(yè)管理層和員工的利益之間存在根本的差異,組織對利潤的需求凌駕于員工幸福之上[13],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踐只是控制和監(jiān)控員工的工具。相關(guān)研究發(fā)現(xiàn),員工感知到的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踐提升了員工的壓力感[14]。然而現(xiàn)有關(guān)于人力資源管理的理念的討論大多從組織的角度出發(fā),從而產(chǎn)生了以上矛盾的研究結(jié)論[15]。本文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員工對HRM 管理動(dòng)機(jī)的評(píng)價(jià),因?yàn)閱T工對管理理念的認(rèn)知和判斷影響著雇主與員工關(guān)系的本質(zhì)[3]。
歸因理論為上述分歧找到了出口,基于歸因理論,個(gè)體不是對外部事件本身作出反應(yīng),而是對他們判斷的事件發(fā)生的原因作出反應(yīng)[16]。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從信號(hào)接收端的角度,解讀了戰(zhàn)略人力資源的兩種管理理念,指員工會(huì)對組織的人力資源政策和實(shí)踐(如培訓(xùn)、福利、招聘、薪酬和員工管理辦法等)背后的管理動(dòng)機(jī)進(jìn)行理解、判斷、解釋,其本質(zhì)是員工對工作環(huán)境進(jìn)行意義建構(gòu)的方式,是一種認(rèn)知。承諾型HRA 指員工將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yàn)閹椭鷨T工提高產(chǎn)品或服務(wù)的質(zhì)量并提升員工的幸福感;控制型HRA 指員工將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yàn)楸M量降低成本并從員工身上獲得最大的產(chǎn)出。
知識(shí)共享指個(gè)體在一定范圍內(nèi)(組織、團(tuán)隊(duì)、社區(qū)等),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自愿向他人提供與解決問題、發(fā)展創(chuàng)意或改進(jìn)流程等相關(guān)的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觀點(diǎn)的行為,是一種利組織積極行為[17]。做出承諾型HRA 的員工判斷組織的人力資源實(shí)踐是為了員工幸福感提升和工作質(zhì)量的提高,感受到組織服務(wù)顧客的社會(huì)責(zé)任,出于對組織價(jià)值觀的認(rèn)可,員工將自己視為組織的“內(nèi)部人”,愿意為組織付出,產(chǎn)生更多的主動(dòng)性行為。同時(shí),員工感受到組織對于員工幸福的重視,會(huì)認(rèn)為組織在尋求與員工建立長期關(guān)系,基于社會(huì)交換過程,員工同樣會(huì)將自己的知識(shí)與技能共享出去作為回報(bào)。
另一方面,做出控制型HRA 的員工判斷人力資源政策的目的為降低成本與剝削員工,感受到組織對員工幸福的忽視。在這種情況下,員工會(huì)認(rèn)為組織沒有履行對員工的責(zé)任,也低估了員工的價(jià)值。從而在團(tuán)隊(duì)互動(dòng)中表現(xiàn)出較少的協(xié)作、利他行為,可能降低知識(shí)共享的水平。由此提出如下假設(shè):
承諾型HRA 對知識(shí)共享有正向影響(H1a);
控制型HRA 對知識(shí)共享有負(fù)向影響(H1b)。
(二)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與組織認(rèn)同
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指出,作為個(gè)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社會(huì)認(rèn)同源于個(gè)體對依附于一種群體成員資格的共同價(jià)值重要性的認(rèn)識(shí)[18]。組織認(rèn)同在社會(huì)認(rèn)同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本質(zhì)上是與組織統(tǒng)一性的感知,反映了員工的自我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與組織融合。Hogg 和Terry[19]研究表明,自我提升和減少不確定性兩種心理動(dòng)機(jī)共同激發(fā)了組織認(rèn)同。
首先,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認(rèn)為,當(dāng)個(gè)人認(rèn)為一個(gè)組織擁有良好聲譽(yù)時(shí),組織的成員身份會(huì)增強(qiáng)他們的自尊,由此他們會(huì)對組織產(chǎn)生更強(qiáng)烈的認(rèn)同[20]。員工將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yàn)閹椭鷨T工給顧客提供更好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時(shí),能夠感受到組織的社會(huì)責(zé)任,利他的組織形象使員工感受到了組織成員身份帶來的自豪感,提升其自我概念,從而增強(qiáng)組織認(rèn)同。同時(shí),員工將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yàn)樘嵘龁T工幸福感時(shí),他們會(huì)認(rèn)為組織在以積極的方式對待員工并為其提供穩(wěn)定的經(jīng)濟(jì)或社會(huì)情感資源,減少了員工的不確定性,員工會(huì)將組織的價(jià)值和利益視為自己的,并將其整合到自我概念中,認(rèn)為自己與組織成為“命運(yùn)共同體”,通過對組織的心理投資產(chǎn)生更高的組織認(rèn)同[21]。
反之,員工將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yàn)楸3值统杀緯r(shí),員工將自己視為企業(yè)的“成本”,隨時(shí)面臨企業(yè)成本削減帶來的辭退風(fēng)險(xiǎn),感受到的不確定性提升,從而降低了組織認(rèn)同。員工將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yàn)閺膯T工身上獲得最大的產(chǎn)出時(shí),員工產(chǎn)生“被剝削感”。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指出,社會(huì)認(rèn)同過程加劇了由相對剝奪產(chǎn)生的不滿情緒,因此此時(shí)員工更有可能認(rèn)定所在組織為“自私”的組織,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個(gè)體的組織認(rèn)同感[22]。由此,提出如下假設(shè):
承諾型HRA 對組織認(rèn)同有正向影響(H2a);
控制型HRA 對組織認(rèn)同有負(fù)向影響(H2b)。
(三)組織認(rèn)同的中介作用
對于人力資源管理系統(tǒng)影響員工的態(tài)度和行為的確切過程,以往研究大多以社會(huì)交換理論解釋,然而近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認(rèn)為,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具有超出互惠原則之外的解釋力[22]。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指出,認(rèn)同的實(shí)現(xiàn)過程是促使個(gè)體從認(rèn)同對象(即組織)處獲得目標(biāo)感和依附感,從而引導(dǎo)個(gè)體表現(xiàn)出組織所期望的行為與態(tài)度。本文關(guān)注組織認(rèn)同這一概念,已有大量研究證實(shí)了組織認(rèn)同對知識(shí)共享行為的預(yù)測作用[23]。同時(shí),前文論述了HRA 顯著影響組織認(rèn)同與知識(shí)共享,由此,組織認(rèn)同在HRA 與知識(shí)共享間發(fā)揮中介作用。
做出承諾型HRA 的員工,從組織的人力資源實(shí)踐中感受到來自組織的關(guān)懷、支持與尊重,此時(shí)員工出于對組織價(jià)值觀的認(rèn)可,產(chǎn)生更高的組織認(rèn)同。當(dāng)個(gè)體的組織認(rèn)同較高時(shí),強(qiáng)化了個(gè)體與組織的利益、心理關(guān)聯(lián)以及身份感,促使其表現(xiàn)出更多的利組織行為,員工會(huì)以超出“義務(wù)”的心態(tài)進(jìn)行知識(shí)共享。相反,做出控制型HRA 的員工,從人力資源實(shí)踐中感受到來自組織的利用、剝削與壓榨,削弱了個(gè)體的組織認(rèn)同。個(gè)體的組織認(rèn)同較低時(shí),會(huì)減少對組織的“投資”,員工知識(shí)共享的頻率和質(zhì)量隨之降低。由此,提出如下假設(shè):
組織認(rèn)同在承諾型HRA 和知識(shí)共享之間起中介作用(H3a);
組織認(rèn)同在控制型HRA 和知識(shí)共享之間起中介作用(H3b)。
(四)任務(wù)互依性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已有研究指出,組織、團(tuán)隊(duì)、個(gè)體等變量共同構(gòu)成了知識(shí)共享影響機(jī)制的分析框架。本文認(rèn)為,團(tuán)隊(duì)成員對任務(wù)環(huán)境的感知,是HRA 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重要邊界條件,由此聚焦于任務(wù)互依性這一任務(wù)特征。任務(wù)互依性指團(tuán)隊(duì)成員為了完成工作而向其他成員提供信息、材料和支持的程度[24]。本文將任務(wù)互依性視為個(gè)體層面變量,因?yàn)閳F(tuán)隊(duì)中的個(gè)體區(qū)分并承擔(dān)了不同的工作任務(wù),因此個(gè)體在團(tuán)隊(duì)中可能感知到不同程度的任務(wù)互依性[25]。
首先,高任務(wù)互依性的個(gè)體需要與其他團(tuán)隊(duì)成員進(jìn)行廣泛與頻繁的互動(dòng),以獲得完成任務(wù)的關(guān)鍵資源,這一過程使得團(tuán)隊(duì)成員之間對于彼此的能力與專長更加熟悉[26]。根據(jù)角色理論,每位員工都在團(tuán)隊(duì)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其角色集內(nèi)的成員(如同事、主管等)會(huì)根據(jù)員工的角色設(shè)定對其產(chǎn)生期望。個(gè)體為了滿足來自其角色集內(nèi)成員的期望,會(huì)更加積極地共享自己擅長領(lǐng)域的知識(shí),為團(tuán)隊(duì)成員提供幫助。其次,高任務(wù)互依性團(tuán)隊(duì)的任務(wù)完成情況與每位團(tuán)隊(duì)成員的任務(wù)進(jìn)度息息相關(guān),員工需要共享自己的知識(shí)與技能以確保團(tuán)隊(duì)任務(wù)順利完成。
換言之,任務(wù)互依性正向調(diào)節(jié)了組織認(rèn)同與知識(shí)共享之間的關(guān)系,任務(wù)互依性越高,承諾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對知識(shí)共享的正向影響越會(huì)得到強(qiáng)化,控制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對知識(shí)共享的負(fù)向影響越會(huì)得到弱化。基于此,提出假設(shè):
任務(wù)互依性正向調(diào)節(jié)組織認(rèn)同在承諾型HRA與知識(shí)共享關(guān)系間的中介效應(yīng)。當(dāng)任務(wù)互依性較高時(shí),承諾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對知識(shí)共享產(chǎn)生的正向影響較強(qiáng)(H4a);
任務(wù)互依性正向調(diào)節(jié)組織認(rèn)同在控制型HRA與知識(shí)共享關(guān)系間的中介效應(yīng)。當(dāng)任務(wù)互依性較高時(shí),控制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對知識(shí)共享產(chǎn)生的負(fù)向影響較弱(H4b)。
綜上所述,本文構(gòu)建理論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調(diào)查問卷在我國江蘇省8 家企事業(yè)單位進(jìn)行抽樣,涉及餐飲、醫(yī)院、制造多個(gè)行業(yè),其中生產(chǎn)制造業(yè)占樣本總數(shù)的23.60%、酒店服務(wù)業(yè)51.50%、公共事業(yè)單位24.90%。兩輪調(diào)查各發(fā)放問卷700 份,第一輪回收問卷679 份,第二輪回收問卷630 份,共得到有效配對問卷615 份,刪除不合格問卷后剩余602 份有效配對樣本。樣本中,男性占比37.80%,女性占比62.20%;員工平均年齡31.1 歲,其中24 歲以下占33.00%,25~34 歲占40.80%,35~44 歲占17.10%,45 歲以上占9.10%;大專以下學(xué)歷占48%,大專及以上學(xué)歷占52%;服務(wù)年限3年以下占45.55%,3 年以上占46.55%。
(二)測量工具
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采用Nishii 等[3]開發(fā)的HRA 量表,分為承諾型HRA 和控制型HRA 兩個(gè)獨(dú)立維度各10 個(gè)題項(xiàng),要求組織員工分別對組織員工培訓(xùn)、員工福利、聘用政策、薪酬水平、員工管理辦法5 種人力資源管理政策的動(dòng)機(jī)進(jìn)行判斷。人力資源歸因的Cronbach’sα為0.856,KMO 為0.881。
組織認(rèn)同:采用Smidts 等[27]開發(fā)的組織認(rèn)同量表,共5 個(gè)題項(xiàng),樣題如“我為自己為這個(gè)組織工作感到驕傲”。組織認(rèn)同的Cronbach’sα為0.718,KMO 為0.743。
知識(shí)共享:采用Bock 和Kim[28]開發(fā)的量表來測量知識(shí)共享,含4 個(gè)題項(xiàng),樣題如“在工作中,我與同事共享我的工作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共享的Cronbach’sα為0.755,KMO 為0.750。
任務(wù)互依性:采用Pearce 和Gregersen[24]開發(fā)的任務(wù)互依性量表,由個(gè)體報(bào)告他們工作目標(biāo)的完成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團(tuán)隊(duì)成員,含3 個(gè)題項(xiàng),樣題如“我必須經(jīng)常與他人協(xié)調(diào)我的工作”,任務(wù)互依性的Cronbach’sα為0.880,KMO 為0.872。
控制變量:為了使研究結(jié)果具有普遍性,本文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變量作為控制變量,以求更為準(zhǔn)確地解釋HRA、組織認(rèn)同與知識(shí)共享等變量間的影響關(guān)系。
三、實(shí)證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yàn)方法,對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進(jìn)行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各變量內(nèi)部結(jié)構(gòu)清晰,第一個(gè)主成分解釋變異23.583%,未占到總變異解釋量(60.879%)的一半。共線性檢驗(yàn)結(jié)果表明,各變量的容忍度在0.940~0.724,方差膨脹因子(VIF)在1.064~1.380,遠(yuǎn)低于推薦臨界。因此同源偏差和共線性問題均未對本文造成嚴(yán)重影響。
(二)區(qū)分效度檢驗(yàn)
使用Mplus7.0 軟件對收集的有效樣本數(shù)據(jù)進(jìn)行驗(yàn)證性因子分析,結(jié)果見表1。在研究模型中,檢驗(yàn)了承諾型HRA 和控制型HRA 的區(qū)分效度,同時(shí)由于組織認(rèn)同、任務(wù)互依性與承諾型HRA 三者之間相關(guān)系數(shù)均超過0.4,故將三者逐步區(qū)分。由表1 可知,承諾型歸因、控制型歸因、組織認(rèn)同、任務(wù)互依性、知識(shí)共享組成的五因素模型擬合指標(biāo)數(shù)據(jù)明顯優(yōu)于其他4 個(gè)比較模型(χ2=1855.22;RMSEA=0.054;CFI=0.967;TLI=0.956;SRMR=0.052)。由此可見,本文模型整體擬合度達(dá)到參考標(biāo)準(zhǔn),研究變量之間相互獨(dú)立。

表1 變量區(qū)分效度檢驗(yàn)
(三)描述性統(tǒng)計(jì)
所有變量之間的相關(guān)系數(shù)、均值和標(biāo)準(zhǔn)差見表2。由表2 可知,承諾型歸因與知識(shí)共享(r=0.175,p<0.01)呈顯著正相關(guān);控制型歸因與知識(shí)共享(r=-0.164,p<0.01)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組織認(rèn)同與知識(shí)共享(r=0.234,p<0.001)呈顯著正相關(guān)。相關(guān)性分析結(jié)果支持了部分研究假設(shè),為后續(xù)分析提供了初步依據(jù)。

表2 主要指標(biāo)間的均值、標(biāo)準(zhǔn)差及相關(guān)分析(N=602)
(四)假設(shè)檢驗(yàn)
構(gòu)建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考察人力資源歸因與知識(shí)共享的關(guān)系,使用Mplus7.0 軟件對研究假設(shè)進(jìn)行檢驗(yàn)并得出分析結(jié)果,結(jié)構(gòu)方程路徑系數(shù)見表3。

表3 結(jié)構(gòu)方程路徑系數(shù)
1.主效應(yīng)檢驗(yàn)
構(gòu)建承諾型HRA 和控制型HRA 對知識(shí)共享的影響模型檢驗(yàn)H1a、H1b。表3 中M1 顯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影響后,模型擬合指數(shù)分別為χ2=817.687,df=315,χ2/df=2.596,RMSEA=0.072,CFI=0.858,TLI=0.844,模型擬合尚可。承諾型HRA 影響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路徑系數(shù)為0.126(p<0.01),控制型HRA 影響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路徑系數(shù)為-0.112(p<0.05),即個(gè)體對組織的人力資源政策做出承諾型歸因時(shí),知識(shí)共享行為提升,做出控制型歸因時(shí),知識(shí)共享行為下降,H1a、H1b 得到驗(yàn)證。
2.中介效應(yīng)檢驗(yàn)
構(gòu)建承諾型HRA、控制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中介機(jī)制模型。表3 中M2 顯示,模型擬合良好(χ2=858.696,df=356,χ2/df=2.596,RMSEA=0.049,CFI=0.936,TLI=0.927)。組織認(rèn)同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中介效應(yīng)顯著(β=0.337,p<0.001),此時(shí)承諾型HRA(β=0.031,p>0.05)、控制型HRA(β=-0.050,p>0.05)對知識(shí)共享的影響由原來的顯著變?yōu)椴伙@著,說明在HRA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過程中,組織認(rèn)同起完全中介作用。表4 顯示了基于5000 個(gè)Bootstrap 樣本導(dǎo)出的偏差校正置信區(qū)間(bias corrected CI),Bootstrap 檢驗(yàn)支持中介效應(yīng)顯著的結(jié)果。承諾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中介效應(yīng)顯著(β=0.059),偏差校正置信區(qū)間不包括0(0.014,0.103);控制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中介效應(yīng)顯著(β=-0.015),偏差校正置信區(qū)間不包括0(-0.032,-0.002)。綜上,H2、H3 得到驗(yàn)證。

表4 Bootstrap 分析方法的中介效應(yīng)檢驗(yàn)
3.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檢驗(yàn)
構(gòu)建被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模型,表3 中M3 顯示,模型擬合良好(χ2=893.172,df=386,χ2/df=2.236,RMSEA=0.050,CFI=0.922,TLI=0.030)。為檢驗(yàn)任務(wù)互依性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本文使用Hayes 提出的系數(shù)乘積法進(jìn)行被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效應(yīng)分析,即通過檢驗(yàn)交互項(xiàng)與因變量之間路徑系數(shù)乘積的顯著性判斷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是否顯著。同時(shí)根據(jù)Edwards 和Lambert[29]提出的差異分析法進(jìn)一步進(jìn)行驗(yàn)證,即通過直接檢驗(yàn)中介效應(yīng)之差的顯著性判斷被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效應(yīng)是否顯著。表4 中M3 顯示,在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影響知識(shí)共享的路徑中,任務(wù)互依性與組織認(rèn)同的交互項(xiàng)對知識(shí)共享的影響顯著(β=0.135,p<0.01),任務(wù)互依性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成立。
進(jìn)一步,Bootstrap 分析的有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效應(yīng)檢驗(yàn)結(jié)果見表5。結(jié)果顯示,在高任務(wù)互依性組中(均值之上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承諾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到知識(shí)共享的中介效應(yīng)值為0.069(p<0.01),95%的偏差校正Bootstrap 置信區(qū)間為[0.034,0.114],不包含0;在低任務(wù)互依性組中(均值之下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承諾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到知識(shí)共享的中介效應(yīng)值為0.014(p>0.05),95%的偏差校正Bootstrap 置信區(qū)間為[-0.032,0.058],包含0;任務(wù)互依性高低組之間間接效應(yīng)差異的效應(yīng)值為0.054(p<0.01,CI[0.014,0.102])。說明在互依性更強(qiáng)的任務(wù)環(huán)境中,組織認(rèn)同在承諾型HAR 與知識(shí)共享之間的中介效應(yīng)顯著增強(qiáng)。

表5 Bootstrap 分析方法的有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效應(yīng)檢驗(yàn)
在高任務(wù)互依性組中(均值之上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控制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到知識(shí)共享的中介效應(yīng)值為-0.012(p<0.05),95%的偏差校正Bootstrap置信區(qū)間為[-0.032,-0.001],不包含0;在低任務(wù)互依性組中(均值之下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控制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到知識(shí)共享的中介效應(yīng)值為-0.002(p>0.05),95%的偏差校正Bootstrap 置信區(qū)間為[-0.017,0.004],包含0;任務(wù)互依性高低組之間間接效應(yīng)差異的效應(yīng)值為-0.009(p<0.05,CI[-0.029,-0.001])。說明在互依性更強(qiáng)的任務(wù)環(huán)境中,組織認(rèn)同在控制型HAR 與知識(shí)共享之間的負(fù)向中介效應(yīng)顯著削弱。
綜上,在高任務(wù)互依性的環(huán)境下,承諾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產(chǎn)生了更高水平的知識(shí)共享,控制型HRA通過組織認(rèn)同降低的知識(shí)共享水平得到緩和,即任務(wù)互依性提升了組織認(rèn)同與知識(shí)共享之間的正向關(guān)系,進(jìn)而正向強(qiáng)化了中介效應(yīng),H4a、H4b 得到驗(yàn)證。
五、結(jié)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jié)論
基于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利用602 份員工數(shù)據(jù)檢驗(yàn)了人力資源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qū)χR(shí)共享行為的影響及其作用機(jī)制,分析了組織認(rèn)同的中介作用以及任務(wù)互依性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首先,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基礎(chǔ)上,證明了HRA 對知識(shí)共享的影響作用。本文提出的H1a、H1b 描述了承諾型與控制型HRA 對知識(shí)共享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獲得了實(shí)證檢驗(yàn)的支持。其次,本文依托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證明了組織認(rèn)同在HRA 與知識(shí)共享之間的中介作用。實(shí)證結(jié)果支持了H2、H3,表明組織認(rèn)同完全中介了HRA 對員工知識(shí)共享行為的影響。最后,本文發(fā)現(xiàn)組織認(rèn)同在HRA 與知識(shí)共享關(guān)系中的中介作用具有情境性,實(shí)證檢驗(yàn)了H4a、H4b,表明HRA 影響員工知識(shí)共享的過程受到任務(wù)互依性這一邊界條件的限制,即當(dāng)任務(wù)互依性較高時(shí),承諾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對知識(shí)共享產(chǎn)生的正向影響較強(qiáng),控制型HRA 通過組織認(rèn)同對知識(shí)共享產(chǎn)生的負(fù)向影響較弱。
(二)理論意義
首先,本文從微觀層面的心理渠道探索了HRM 與員工利組織積極行為之間的關(guān)系。過程型HRM 屬于尚未成熟的研究領(lǐng)域,HRA 仍是一個(gè)有待發(fā)展的理論。現(xiàn)有HRA 的影響效應(yīng)研究大多基于社會(huì)交換理論的互惠原則,盡管這些研究對于理解理解HRA 的影響機(j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卻局限于HRM 政策本身的外在引導(dǎo),而忽視了員工對組織的內(nèi)在認(rèn)同,導(dǎo)致員工的利組織積極行為缺乏內(nèi)在的動(dòng)機(jī)支撐。本文基于社會(huì)認(rèn)同的理論視角證實(shí)了HRA 對于知識(shí)共享的影響過程,豐富了HRA 理論,啟發(fā)未來研究從更多的理論視角如資源保存理論等,探討HRA 的影響效應(yīng),同時(shí)呼吁未來研究基于HRA 的視角對員工的利組織積極行為做更為廣泛的探討。
其次,本文將HRA 理論運(yùn)用到知識(shí)管理領(lǐng)域,豐富了知識(shí)共享的研究視角。以往研究多從工作設(shè)計(jì)、團(tuán)隊(duì)關(guān)系等角度探索知識(shí)共享的影響前因,本文從組織環(huán)境因素(即組織人力資源政策和實(shí)踐)和員工對管理動(dòng)機(jī)歸因的角度出發(fā),在個(gè)體心理層面驗(yàn)證了承諾型HRA 對于提升員工知識(shí)共享行為的顯著積極作用,拓展了知識(shí)共享的研究視角,對知識(shí)共享的研究框架做出了有益的補(bǔ)充。
(三)管理啟示
在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企業(yè)如何設(shè)計(jì)并實(shí)施人力資源政策和實(shí)踐,以激發(fā)員工的工作熱情,促使員工在工作中產(chǎn)生更多利組織積極行為,成為學(xué)界關(guān)注的重要命題。企業(yè)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有必要重視員工的培訓(xùn)和發(fā)展項(xiàng)目,傳遞組織支持、尊重、關(guān)愛員工的管理理念,同時(shí)主動(dòng)承擔(dān)更多的社會(huì)責(zé)任,引導(dǎo)員工認(rèn)可自己組織成員的身份并為之感到自豪,提升員工對企業(yè)的歸屬感和認(rèn)同度,從而提升知識(shí)共享行為。同時(shí),在高任務(wù)互依性環(huán)境中,團(tuán)隊(duì)成員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通過強(qiáng)化個(gè)體對組織的歸屬感而使其自發(fā)產(chǎn)生利組織的行為。因此企業(yè)在進(jìn)行工作設(shè)計(jì)時(shí)需要認(rèn)識(shí)到團(tuán)隊(duì)內(nèi)部互動(dòng)和成員協(xié)調(diào)的重要意義,重視組織內(nèi)部的團(tuán)隊(duì)建設(shè),形成個(gè)人與團(tuán)隊(duì)發(fā)展協(xié)同推進(jìn)的理念,為員工的知識(shí)共享行為提供沃土。
(四)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研究資源的局限,僅集中選取了江蘇的部分企事業(yè)單位員工作為調(diào)研樣本,雖然通過縱向收集兩輪數(shù)據(jù)控制了同源偏差,但研究結(jié)果是否適用于其他行業(yè)和地區(qū)的企業(yè)需要進(jìn)一步檢驗(yàn)。其次,僅證實(shí)了個(gè)體層面上HRA 對知識(shí)共享的影響,而知識(shí)共享一直被認(rèn)為是充分利用團(tuán)隊(duì)內(nèi)各成員掌握的信息和知識(shí),推動(dòng)團(tuán)隊(duì)創(chuàng)新,提高團(tuán)隊(duì)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因此,在團(tuán)隊(duì)層面上HRA 是否也能發(fā)揮作用,值得進(jìn)一步研究。
- 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的其它文章
- “與主編面對面”
——中國技術(shù)經(jīng)濟(jì)學(xué)會(huì)第二十七屆學(xué)術(shù)年會(huì)學(xué)術(shù)期刊交流論壇 - BIM 應(yīng)用下項(xiàng)目主體間信任關(guān)系對虛擬協(xié)作有效性的影響
——信息共享質(zhì)量的中介效應(yīng) -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為對女性知識(shí)型員工情感承諾的影響機(jī)制研究
- 品牌標(biāo)識(shí)的隱性設(shè)計(jì)線索對消費(fèi)者品牌創(chuàng)造性感知的影響
- 產(chǎn)業(yè)集群知識(shí)創(chuàng)新的重要觀點(diǎn)*
- 省內(nèi)城市間經(jīng)濟(jì)關(guān)聯(lián)結(jié)構(gòu)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中Kij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