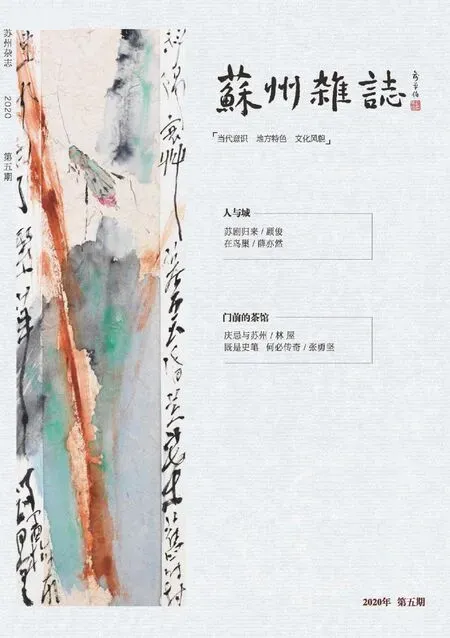以夢為馬
呂一禾
一
我問劉瀟,做戲劇這么多年,最難的是什么?
孤單吧,他說。
這回答讓人意外,我料想中的答案,應該是現實而確切的,一是一二是二的。
后來聽說他喜歡俄國文學,喜歡契訶夫,于是我有點明白了。
還記得契訶夫小說《苦惱》里那個老車夫約納嗎?成千上萬的人中,沒有誰愿意聽他的傾訴,在乎他的悲痛,他只好跟自己的馬訴說衷腸。偌大世界里,只有這匹馬是他的唯一慰藉。作為文藝青年,劉瀟應該很能體會這種無處傾訴、無法消解的寂寞感吧:面對一個沸騰、喧嘩的世界,無論是吶喊或哭泣,都像泥牛入海;每個人都活在套子里,活成了一座孤島。

☉ 話劇《小城之春》劇照
我猜想,戲劇應該是他對抗孤單的方式:沒有戲劇,他的孤單是浮游抽象的;通過戲劇,他將其冷凝或蒸發,可以賞玩,也可以一筆勾銷。
選擇《小城之春》,正是因為他喜歡契訶夫。作為劇作家的契訶夫認為,生活就是日復一日地流逝,悲喜交集都從乏善可陳里孕育和誕生。而在劉瀟看來,《小城之春》正是一個十分“契訶夫”的作品,它用散文化的敘事,講述了一個非常“中國”的故事。全劇所有的矛盾沖突都是暗藏于視線以下,暗藏于內心的,絲毫沒有刺刀見紅的凌厲之氣。
“《小城之春》的本子是我2015年寫的,從那時開始,每年都演幾場。雖然本子是一個,但每年演出都不一樣。最初是舞臺劇,后來我們把演出搬到了平江路的茶館里,也在一個破舊的水塔里演出過。今年,我們想在一個廢棄的園子里來演,利用老宅后花園作為實景舞美,通過‘環境戲劇’的表現手法,讓觀眾與故事人物互動。舞臺表現方面,我們每年都會去找一個點切入,再加以放大……”這部脫胎于經典影片的改編之作,也是劉瀟的心血之作,提起來就放不下:
“像今年,就把費穆這個角色搬上了舞臺。也是很巧,那本來是我寫的另外一個本子,名字就叫《費穆》。我有時候寫得很快,一個本子一兩個星期就寫好了,寫好就放在那里。這次覺得,放著也浪費,就把兩個本子揉到一起去了。舞臺表現上也增加了一些元素,將當年電影《小城之春》上映后的評論在劇中呈現了出來。”
說起來,《小城之春》確實是一部與蘇州有淵源的戲。電影導演費穆原籍蘇州,據說,影片的內景和外景均取自陸巷古村。半個多世紀后,導演田壯壯重拍《小城之春》,選外景時又相中了陸巷的王鏊故居惠和堂,里面的庭院搭建和家具擺設,都由身為編劇的作家阿城親自設計。費穆的《小城之春》如今已被時間過濾成經典之作,最初上映時卻遭受冷遇與批評。批評界有人指責其為“在革命和反革命斗爭特別尖銳時期的懦弱動搖”。所以現在看來,中國電影史上有“兩個費穆”:一個是創作了“國防電影”《狼山喋血記》、抗戰紀錄片《北戰場精忠錄》的費穆,一個是留下了《人生》《小城之春》的費穆。這兩個面目迥異的費穆,究竟哪一個更有生命力,更具有永恒的藝術價值,已毋庸贅述。
而在當初那個戰亂紛擾的時代,費穆苦惱的心緒只好借助文字抒發出來,“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寂寞。”
二
2014年,劉瀟從蘇州大學文學院戲劇專業畢業,成立了自己的文化策劃公司,取名“普羅公園”。
“我在上海的一個公園里,看見各色各樣的人,他們的訴求是迥異的,然而都在那里各自呼喊……我覺得這就是‘普羅’的意思。”而“普羅公園戲劇計劃”,正是他對于戲劇市場化道路的個人嘗試,“我們‘普羅公園’團隊四個人,我是專門負責戲劇這一塊的;另一個是瞿子竣,從事當代藝術、舞臺美學的;還有一個是古典文學專業的,人人都有一個藝術夢。”
當然,這條“夢之路”并不好走。
“就我來說,現在特別辛苦,因為還處在文化產業比較初級、原始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很成熟的管理制度,我現在很多的時間花在管理上。上海現在實行制作人制度,以制作人為中心,導演、劇本都由制作人去找,然后根據導演要求去找演員……”這種運作模式區別于以前的導演中心制,那時的制作都聽導演的,不需要考慮成本,甚至是不惜成本來做。市場化以后就完全是兩回事了,需要找到經費,控制成本,然后再安排演出場次,演員工資,宣傳媒體等等。
“前兩年房地產發展不錯的時候,還是能找到一些投資的,這兩年明顯少了。我們挺缺人的,特別是制作人。制作人缺就說明市場不好,找不到錢。現在我們團隊的制作人主要就是我,太累了。因為人基本處于一個分裂的狀態,晚上要寫劇本,白天要忙另一攤事,不是同一種思維方式。”
望著坐在對面的年輕人,一副叫苦卻決不言棄的架勢,讓我忍不住好奇,戲劇到底給了他什么,讓他如此執迷?
“對于做戲劇,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心理預期。就是做這個,不賺錢。但我們又希望能夠賺到錢。特別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可,尤其是家庭的認可。最近我慫恿我太太辭了職,因為我希望她能和我一樣,做點讓自己開心的事。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我們可以一起去努力。”看樣子,劉瀟堅信,讓自己開心,比追求更多的收入和更舒適的物質生活,都要來得重要。而戲劇,恰恰就是這個讓他痛并快樂著的事業。
“將來我們老了之后,起碼可以跟后輩們說,自己年輕時候曾經做過這么牛的事情:不計得失,不論成功與否,我們為了理想,都去嘗試過,努力過了!”
以夢為馬,他簡單直白的話語中透著一種孩子氣式的驕傲和詩意。

☉ 實景版喜劇《金榜題名時》劇照

☉ 話劇《玩偶日志》劇照
當然,“普羅公園”的其他業務可以掙錢,家庭生活不會受影響。可是演職人員收入低是個現實問題。“我們甚至有些演員,一邊排戲,一邊在賣腳氣藥。”劉瀟說。所以,可以將戲劇當成理想中的事業,但顯然,這不是個理想的謀生手段。關于演員收入,在我的刨根問底下,劉瀟也“幽了一默”,“我們是按照北京人藝的標準來執行,排練一場100塊,一場大約四五個小時。以今年新排的《小城之春》為例,按項目制運作,從建組開始到首演為止,一個人到手的收入也就兩三千塊吧。”
然而,演出經費拮據還不是劉瀟最頭疼的事。在他看來,劇本才是靈魂。
“今年新寫的一個劇本,涉及的是一個我完全不懂的領域——暗網,所以要做很多的知識準備,還要跟相關的專業人員,甚至黑客打交道。采風結束,前后寫了兩三稿,當時是疫情防控關鍵時期,心緒起伏,也影響了作品的進度。本子最初叫Hamlet.exe,取了個病毒程序的名字,后來是全盤推翻,一遍遍改寫,寫成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本子。”這就是在今年第二屆中國蘇州江南文化藝術·國際旅游節上首次亮相的舞臺劇《玩偶日志》。
將自己的原創劇本順利搬上舞臺,就像一個母親親歷子宮里的胚胎成長為呱呱墜地的嬰兒,這是一個充滿希望與期待,也不無妥協與煎熬的過程。劉瀟一直行走在戲劇理想和現實環境之間的蹺蹺板上,尋找著微妙的平衡。
他深深明白,戲劇是一門特別綜合的藝術,是單個人無法獨立完成的。從文本、舞美、音效,到演員、觀眾及空間劇場,缺一不可。既需要詩歌一般的情感沖擊力,又要能讓觀眾感受到這種沖擊,一個好的劇作者要具備從象牙塔到世俗社會之間來回穿梭的能力。
三
“我是白羊座,閑不下來。”劉瀟帶著少許的靦腆,笑著說。就在不久前,他辭掉了蘇州文旅集團的工作。
“我還在文旅的時候,知道要做‘江南小劇場’,很是開心,然后就單槍匹馬地開始張羅起來。開始就想做個喜劇,考察了很多劇目,出了很多方案;當時我們正在排一部戲,就組織了集團的中層干部去看,想讓他們知道,還有這樣一群年輕人,在不計回報地做這樣的事。鈕家巷3號潘世恩故居東部,就在狀元博物館隔壁,很早的時候我們就計劃把這里的老宅子打造成小劇場。經過修繕的潘家老宅,后來終于搖身一變成了‘江南小劇場·太傅第’。”
作為蘇州首部室外沉浸式喜劇,實景版《金榜題名時》5月上旬在狀元故居正式首演。當時的項目負責人劉瀟有著更為長遠的設想:憑借“江南小劇場”的東風,搭建一個蘇州本土青年戲劇人才的孵化器,扶持更多的青年戲劇創作團隊,孕育出更多植根于蘇州的優秀原創劇目。在這個新鮮出爐的“江南小劇場·太傅第”,既可以上演傳統的地方戲曲劇目,也可以推出非常現代的先鋒話劇和實驗戲劇。
隨著劉瀟的辭職,這些設想大概都成了愿景。他就像那個始終追逐著理想之光的人,身后投下那些長長短短的暗影,喻示著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一直都在。
我有個疑問,“你畢業后一直是個體創業,為什么會在去年選擇進文旅集團工作呢?”
“首先是因為有了孩子,覺得生活似乎應該有所變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知道別人的生活是什么樣的,想體驗一下那種相對穩定的上班狀態。”劉瀟說。
在他身上,有種豁達、年輕態的特質,沉悶而乏味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是一場充滿先鋒意味的實驗。實驗可以結束,但頭腦風暴一刻未停,他寫劇排劇的日子還將繼續:“田漢有個獨幕劇《蘇州夜話》,我覺得主題很好,就計劃著寫一個《蘇州夜話》的本子,與‘江南’非常契合,目前只寫了個梗概。”
“我還想給東吳劇社寫個本子,就叫《東吳劇社》……”在讀研究生期間,劉瀟曾擔任東吳劇社版《哈姆雷特》的藝術指導,在這里結識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人,劇社亦可視作他的戲劇之路起步的地方。
“東吳劇社”和“普羅公園”,一個是老大哥,一個是小字輩,如今都是蘇州具有代表性的青年戲劇社團。而近年來本土民間戲劇社團的發展,與“蘇州青年戲劇節”這類平臺的搭建不無關系。
“青年戲劇節最早是在2016年,由蘇州文化藝術中心發起。時間在春末夏初,五六月份的演出淡季,參與的多是本土學生劇團。一開始很原生態,臺上臺下很多人都認識,演得雖然有點青澀,氛圍很好,10塊錢一張票。大部分是學生自己花錢去看,主要是培養了青年觀眾。”
從首屆青年戲劇節到今年的“燃”第三屆江南青年戲劇節,“普羅公園”從最初參與“競演單元”的“青苗”,長成了如今樹的姿態。年輕的戲劇人劉瀟,則完成了自己戲劇生涯的10個劇本,其中包括《小城之春》《渡僧橋》《悉達多》《人間》《天堂》《詩人劉浪的一生》《玩偶日志》等。
一提起《渡僧橋》,劉瀟興沖沖地將劇情梗概發給我,說本子已經有了,只等今年戲劇節上的《小城之春》演完,就開始做這個劇。“我希望可以將一些好劇扎扎實實地做出來,市場需要時間來沉淀,觀眾也需要培養。急不得!”
是不急,因為對他來說,“戲劇是我一輩子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