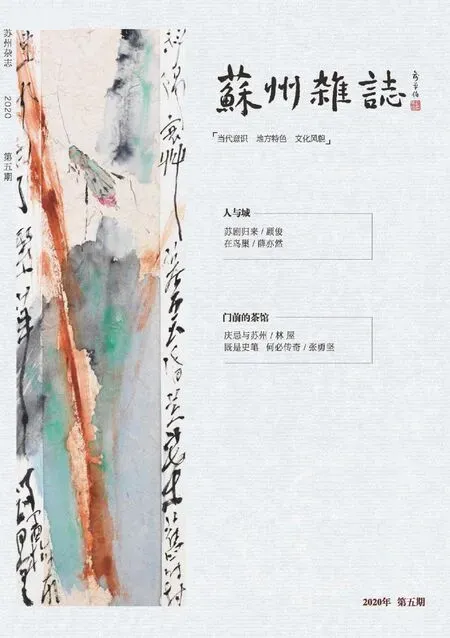由《琉球國書》碑文說開去
倪祥保
2019年國慶期間,我隨蘇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專家方漢文教授、同學馬亞中教授及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張榮興、張龍龍老師等一起,回家鄉常熟方塔公園走走看看,和他們一起參觀了其中的碑刻博物館。
自上大學以來,我一直比較喜歡看古代碑刻,只是時間不給我以更多便利及可能,殊以為憾。我喜歡看古碑,先前主要是為了了解碑文內容,順便練習古文斷句,后來更多是為了欣賞書法藝術及鐫刻技藝。常熟碑刻博物館,確有不少好碑,其中就有《琉球國書》碑。經方漢文老師介紹,蘇州文史學者張曉旭在《蘇州碑刻》一書中有過介紹,并稱其“鮮為人知”。所以我對此特別感興趣,當時就有要寫幾句的想法。

☉《琉球國書》碑文
清代書法金石學家錢泳在《琉球國書》碑文前有題記:“草書一段,族叔復齋先生令象山時從海舶所得也。為之刻石,以廣異聞。”這寫出了碑文來源及鐫碑目的。按方漢文先生說法,這內容簡略,但極為可靠。清代著名書法家王文治為《琉球國書》碑文寫跋:“此琉球國國書也,如中國草書而其文不可識。余嘗有詩云:‘蛟龍滿紙我不識,但覺體類芝與顛。’(“芝”指東漢書法家張芝,“顛”指唐代書法家張旭)觀是卷可證。庚戌年冬十月記于吳趨經訓堂。”比較真實地寫出了他對《琉球國書》文字書寫的感受及理解。
關于這碑文,方漢文老師與前國際比較文明學會會長、東京大學特聘教授伊東俊太郎,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等專家合作,曾經做了如下翻譯:
吉田歌僧昔曾有詩:棠棣花萼艷復嬌,藤花紫云霞光燦。終憶芳菲難忘情。
當此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應有群賢之雅集,詩家酒客,暢敘幽情,感懷賦詩。寄情于萬類矣。
某啟
年月日
就這翻譯來看,碑文是一份很有文學性的邀請書,內容寫某年春天,作者邀請朋友雅集共享美景。碑文開篇引用名叫吉田的詩僧寫的一首小詩。由于這翻譯由中日多位語言大家聯合進行,應該比較權威而可信。就筆者淺昧認知來看,在某些小地方,似乎還有推敲完善之處。
首先是其中落款部分,就碑文大致可以辨識的內容來看,竊以為“某啟”似應為“(某)頓首”。當然,這“頓首”在日本專家的中文翻譯中,很可能會比較習慣于將其翻譯成“某啟”,這基本無傷翻譯的信、達、雅。但是在中文語境中,直接使用“頓首”一詞,不僅毫無錯誤,而且其表達邀請者禮尊被邀請者的意思更加明確,情感更為虔敬,顯然應該更加符合相關禮儀規范。落款里的時間,就碑文相關字跡構形來看,其中“年月”似乎是連體表達的。這在當時行草書寫中,很可能是一種簡潔表達習慣。或者,在琉球國及此類邀請書中,“年月”就是習慣連體寫讀的,如書寫并連讀為“乙亥正月”,而不是書寫并讀成“乙亥(年),正月”。其中“(哪)日”可以屬前一并連讀,也可以單獨句斷,因為邀請雅集那天,單獨寫讀的效果會比較好些。
其次是更為重要的個別標點斷句問題。也許有人會說,這個別的標點斷句還能是重要問題?其實是的。且不說古文斷句及標點使用的不同有時會導致對相關文句意義理解的大相徑庭,關鍵是這里涉及到對吉田所寫詩歌體裁的認知,涉及對中國詩歌藝術發展歷史以及與日本、琉球詩歌文化交流方面的認知。筆者認為,吉田所寫的詩歌,應該屬于典型而工整的“三句體”,其標點應該這樣才比較好:“棠棣花萼艷復嬌,藤花紫云霞光燦,終憶芳菲難忘情。”即在這三個詩句中間不應該使用句號,強調這三個詩句之間的情懷、情感內容是完全直抒胸臆而一氣呵成的。為了很好地說明這一點,筆者在此將中國詩歌中歷史悠久的“三句體”及日本俳句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內容略作介紹,因為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少之又少,一般中國古代詩歌研究者也基本不了解。
“三句體”這個命名是筆者于2000年自撰并獲得學術界認可的。這既有數量眾多詩歌實體的客觀事實基礎,又有先人相關概括提煉作為其學術支撐。“三句之歌”的說法最早可能來自宋代詩論家嚴羽、魏慶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絕句……有三句之歌。”郭紹虞在其“三句之歌”后注:“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詞。”魏慶之《詩人玉屑·詩體·上》:“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三句之詩”的說法最初可能見于明代楊慎《升庵詩話》,其在專門列“三句詩”名目后指出:“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于二十一字之中,最為難工。”筆者認為,古人所謂的“三句之歌”、“三句之詩”,首先可以看作是只由三句組成的詩歌,但并非楊慎所言均為七字句的,比如在清代蘇州人沈德潛編纂的《古詩源》中,就收錄了不少每句字數不完全相同的古老“三句體”詩歌:
《大風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
《歸風送遠操》:“涼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多慨慷。”
《楚聘歌》:“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蟪蛄歌》:“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
《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獲麟歌》:“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衣銘》:“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后必寒。”
《筆銘》:“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答夫歌》:“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之所以如此繁瑣羅列,是為了尊重先人關于“例不滿十法不立”這約定俗成的規約。筆者所謂的“三句體”,首先指古人所言的“三句之歌”、“三句之詩”,即由三句成篇的詩歌,如《大風歌》《李夫人歌》;其次,即古人所言的“三句一換韻”、“三句隔韻”、“三句為一截”,指通篇由三句組成一個意義層次(不是一章)的詩歌,如曹丕的《燕歌行》、岑參的《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再次是指介于前面兩個類型中間的,通篇由三句成章或成闋的詩詞,前者如《詩·王風·采葛》,后者如按曲牌《浣溪沙》填寫的詞。
在簡單介紹中國“三句體”詩歌的時候,需要提一下它與日本俳句之間的關系。一般認為,“俳句”作為日本詩體之一,學習中國“絕句”而來。日本俳句原為俳諧連歌的第一句,十七世紀詩人松尾芭蕉提倡后始成為獨立的詩體,以三句十七音組成一首短詩。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國內有研究者認為:“俳句被稱為世界上最短的律詩,也是對世界文學產生較大影響的詩歌形式之一。泰戈爾坦承他被俳人營造的意境所折服,歐美文壇有英文俳句雜志《美國俳句》《俳句》《西方俳句》等。而與日本一衣帶水的中國,早在清末民初便有詩人開始學習并用日文創作俳句,羅朝斌是其中佼佼者。”其實,這句話后半部分表達的內容,恐怕有點顛倒了本末。不僅出現很早的“絕句”,在唐朝及此前的中國“三句體”詩歌,其實都有很好的傳承影響力。就“三句體”發展而言,方玉潤認為:“唐人多有此體。”日本在唐朝時期向中國學習最為鼎盛,想來日本學習者對唐代及此前的“三句體”詩歌應該會有所關注,并且很可能是崇尚簡潔的日本詩歌藝術家創造“俳諧連歌”時會蘊含有“三句體”特征的“發句(即后來的俳句)”的起源因素之所在。中國古代“三句體”詩歌以三句單獨成篇或成章的均有不少,以三句為一個意義層次的則相對更多。這與日本俳句原先存在于三十一音節的短歌中的情況非常相同,想來應該是其能夠被創設成為獨立詩體的主要學習基礎之一。
關于日本俳句與中國詩歌之間這種可能的傳承相關,有不少研究者只關注詩意的借用學習方面,比如日本學者正岡子規在《芭蕉雜談》中就認為,日本著名俳句詩人松尾芭蕉的名作《秋景》是從漢語中的“枯木寒鴉”脫胎而出的。筆者則主要關注其在結構形態方面向漢語詩歌的學習傳承。松尾芭蕉的代表作《秋景》,其“三句體”特征不僅在形態上非常明顯,在詩意表達結構方面也同樣非常優秀。
晚秋少生機,
蕭索枯枝寒鴉棲,
慘淡夕陽西。
撇開其向中國古代詩歌“借意”的做法,該詩的詩意結構確實與“三句體”完全相似(字數并不是問題,正如筆者對楊慎的觀點所說的那樣)。如果說該詩第一句主要寫生情的時間,以情的抒寫為主,那么第二句主要寫生情的空間,以景的描摹為主,而第三句則更具有時空寥廓的情景相生之表達,可以讓前面的人物情感抒寫與景象呈現得到更為強烈的渲染與延展,使詩歌的情意表達更為深廣而無盡。這個詩歌意境的營造,其實非常像早于其四百年的中國詩歌《天凈沙》,而《天凈沙》前面三句亦為一個意義層次。也就是說,松尾芭蕉這首著名的俳句,不僅像中日學者都認為的那樣是學習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詩意,其實很可能也學習了中國古典詩歌“三句體”的形式。明代楊慎《升庵詩話》曾引述多位同時代人創作的“三句詩”,以此來看,松尾芭蕉時代的中國“三句體”詩歌創作還時有新作,這很可能也是其學習借鑒的重要來源之一。
宗白華先生早年曾說過:“唐人的絕句,像王、孟、韋、柳等人的,境界閑和靜穆,態度天真自然,寓秾麗于沖淡之中,我頂喜歡。后來我愛寫小詩、短詩,可以說承受唐人絕句的影響,和日本的俳句毫不相干,泰戈爾的影響也不大。”宗先生這句話,一方面說明近代以來中國詩歌的“三句體”已經不怎么為人了解,其次也說明中國人寫現代小詩,并非是向日本俳句學習。耐人尋味的是,宗白華先生比較著名的短詩《夜》,其每章的第一個意義層次都由三個詩句組成。由此可見,部分人覺得漢語俳句很可能學習日本俳句而來的認識及觀點,其實并不符合中日詩歌文化交流事實。
《琉球國書》碑文里有中文、日文以及被注音的琉球語,其中一般認為最特殊的當是被注音的琉球語。其實,被注音的琉球語與日文平假名使用古代漢字草書表音的做法內在相通,所以古今觀者都會對此有“蛟龍滿紙我不識,但覺體類芝與顛”的感受。由此可見,中國與日本、琉球之間的文化交流、融通是多方位深入的,其發展歷史也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