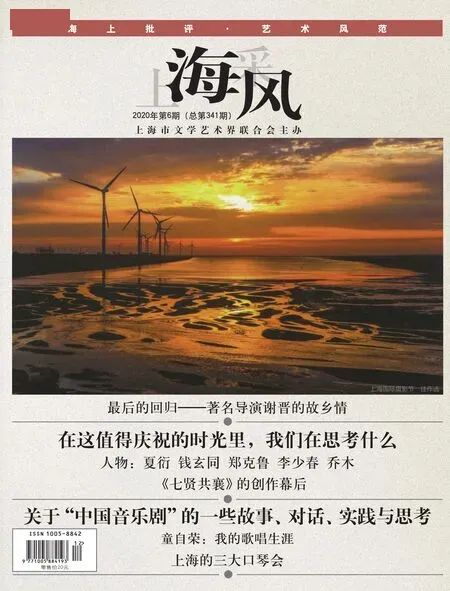無用的藝術
■ 茅威濤
不知歷史,不能明曉過去;不知過去,無法走向未來。
七十年前,上海文聯正式成立,也是新中國正式成立后的第一年。在那個年代,沒有微信、沒有微博、沒有抖音、沒有智能手機和網絡,我們的前輩們用自己的智慧讓原本屬于宮廷的藝術走往民間,讓原本屬于草臺的曲藝走進城市,讓原本屬于中國的文化走向了世界……那是一段讓人心潮澎湃的歷史,至今當我們重溫前輩們留下的字字句句、留聲影像,都還能從中感受到那份滾燙的虔誠與純粹的熱情。
烈士們用鮮血換來了全新的中國,文藝家們用靈魂鑄造了新中國的氣質。經過一個年頭又一個年頭的努力,熬過一個十年又一個十年的艱辛。七十年、七十一年,我們承接著前輩們的心愿走到了今天,親眼看到了他們為之努力、熱切期盼的一個嶄新的時代。這是一個物資充盈的新世紀,新科技、新機遇使人眼花繚亂。今天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從小就知道藝術,他們甚至比我們更清楚藝術與娛樂的區別。今天在上海的家庭,應該每家每戶都有電視機和電腦,電視機里有幾百個頻道,電腦聯網不出門就可以看遍世界。
那么,面對這樣的今天,我們還需要再做些什么呢?如何承上啟下更好地完成前輩們的心愿呢?吳冠中先生曾說:“現在文盲不多了,但是,美盲卻很多。”
今年九月初,我在位于西湖邊寶石山下的小百花越劇場,辦了一個名為“粉筆頭·戲劇+創造營”的暑期活動。邀請了濮存昕、金星、牟森等藝術家,還有上海本土音樂劇青年才俊劉令飛、鄭云龍,為杭州師范大學的學生以及馬云公益基金會鄉村教師計劃的教師們上了為期一周的藝術課。七天的課程,我和我們的學員們都受益良多。
在活動期間,鄉村老師們告訴我,他們的學校沒有藝術課,就算有藝術課,也是體育老師和數學老師代上的,因為校領導們普遍覺得藝術沒用,當然更是師資匱乏。我一時無法找出合適的言辭替他們反駁校領導的觀念。我也問我自己:藝術有用嗎?有什么用呢?我們既無法直接帶動經濟的發展,也無法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既不能代替米飯填飽肚子,也無法代替磚瓦修補漏雨的屋頂。可是與此同時,我又想起了我們的前輩,想起了那個與現在相比不算太好的年代。所以當初的他們到底做了什么,才把我們一步一步帶到了今天?
藝術可以和知識一樣改變命運嗎?普通人也許不會相信,但我相信很多與藝術結緣者是實實在在的藝術受益者。我們這一生若沒能邂逅藝術,沒能邂逅那位讓我們一瞬間的回想就眼眶濕潤的良師并受其啟蒙,我們的命運又當如何?
浙江省戲劇家協會主席這個新身份,使我在深感責任重大的同時,也對自己長期的信念更加清醒與堅定。
當下,我們的現實生活仍然存在物欲橫流、精神匱乏的現象。即便在今天,還是有很多的孩子沒有接觸過藝術;即便在今天,還是有無數的觀眾沒有走進過劇場。我們不能在娛樂釀成的酒里迷醉,亦不該在虛名匯成的海中沉浮。我時常和我的學生們說:“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是特別幸福的。”但時代的變遷、科技的發展,不得不逼著我年近六十了卻依然像個孩子一樣跌跌撞撞繼續探索,個中滋味很艱難也很快樂。因為我知道,我正在做我的老師們曾經做過的事情。但是,我的學生們非常不解,她們時常眨巴著清澈的眼睛問我:“茅老師,您讓我們只做好一件事,可您自己為什么忙于各種身份而未曾停下來呢?”
我無法解答學生們的疑惑,就像無法向那位鄉村教師解釋藝術是否有用。但我相信學生們有一天會理解的,就像我們曾經也未必完全理解我們的老師。我希望我的學生們有一天也能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驕傲,正如我一直帶著老師們的驕傲,才終于堅持走到了今天。
日前,《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國劇協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陳彥的文章,其中提出:“我們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傳統,不僅僅是思想靈魂、精神價值,也包括講述技巧,進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構建這個大時代的戲劇藝術格局,讓文化傳統與現代審美深度契合,從而貢獻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脈動。”讀來感同身受。我理解中的文化,是所有藝術家們對故鄉和祖國的情感。就像杭州人對于西湖,上海人對于黃浦江,中國人對于天安門,那是一種流淌在代代人血脈中永恒的情感記憶。我理解中的初心,就是我們的老師與無數藝術前輩們的心愿。由于這個心愿,他們和偉大的人民群眾、社會各界精英們一起,為我們建設了對他們而言像夢一樣的今天。而我們又將帶給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學生們什么樣的明天、什么樣的未來呢?我想,這就是我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