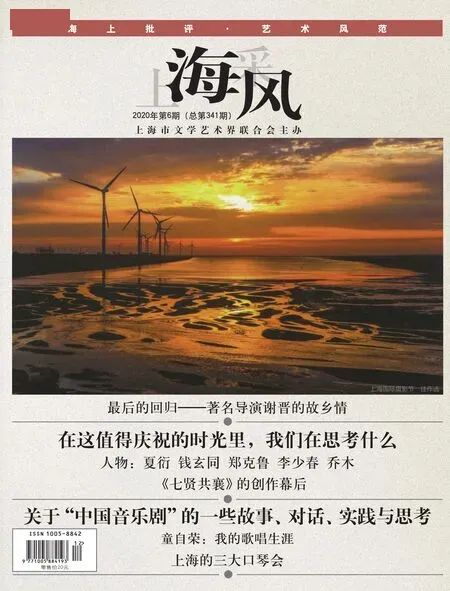為什么要寫閣樓上的瘋女人
■ 黃佟佟
這兩年,我用業余時間寫了一部十二萬字的小說《頭等艙》,縮略版發在《上海文學》上,之后還被《小說選刊》選登了。
有朋友看后,笑著對我說,哎,你怎么也去寫閣樓上的瘋女人了?
眾所周知,《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主義的輝煌名著,帶著某種諷刺的語調說每一個單純可愛的女人都會變成閣樓上的瘋女人:當你年輕美麗單純溫順時,你是善良的簡·愛;而當你人老珠黃索要權力時,你就會變成羅切斯特那被關在閣樓里的妻子。這是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的想象,而我的小說《頭等艙》寫了四個70后女性三十年的起伏際遇。其中確實有一個瘋女人,她曾經是外語系的天之驕女,嫁給了暴富的地產商,最后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瘋女人。這完全是深埋于我內心的一個疑惑:為什么我們這一代女大學生在畢業三十年之后,有如此多的瘋婦。
我自己是在一個三線城市的化工廠廠區長大的。在我小的時候,只有遭受極端不幸的人才會瘋,死了老公孩子極度貧窮的、沒有母親被繼母虐待、遇到極端渣男虐待的……“瘋”離我的生活很遠。上了中學大學,周圍都是天之驕子,我從來也不曾想過那些優秀的漂亮的小伙伴有朝一日會瘋,她們不是理所應該走上云端坐進頭等艙收獲幸福嗎?但是現實是,二十年后,赫然發現就在我身邊,就有好幾個徹底瘋了或者近于瘋了的昔日“女神”。
去年我突然接到一個老友的電話,她告訴我她想來看我,因為病好了。我問什么病?她說她這幾年進出精神病院多次。我們曾經是少年時代的好友,她非常美麗,非常有氣質,也非常有才華,曾經是我文學道路上的引路明燈。但是后來因為一些瑣事早已不聯系多年,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赤裸裸地直面我的同齡人“瘋”的問題。與此同時,我的另一位老友在飯桌上告訴我,她的大學同學瘋了,那位女同學我也曾經有一面之緣,那時她是手擒愛馬仕目下無塵的貴婦,穿著一雙性感到極的黑色羅馬鞋,讓我印象頗深……
昔日女神是怎么從風光無限的華麗人生掉到黑暗瘋狂的深淵里去的呢?她們的起點實在太高了,能讀上重點大學外文系的女生絕對是萬中挑一。只是許多貌似不經意的人生選擇,一步一步把“女神”們逼上了“崩潰”這條路。你可以說是她們自己選的,但是不能否認,這是時代與際遇的合力——她們一帆風順地長大,家長說“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學習上”,要“做好女孩”,她們從千軍萬馬里殺出來考上眾人艷羨的大學,在別人眼里她們前途不可限量,她們進的是當時最好的單位,嫁的是當時覺得最好最牛的男人,她們的青春有一個雷霆萬鈞的開場,但沒想到二十年后卻全盤崩落。
崩潰來自兩個方向,首先是內在世界的崩潰。
愛情和婚姻,男人和孩子,不是作為衡量女人價值的天平——這些我們后來熟知的常識,在七○前女性的生活里幾乎都是空白。她們是沒有經過任何現代性教育長大的一代人,但她們一出生又天然覺得男女是平等的,整個成長過程其實又是完全沐浴在舊式的性別觀念當中的。她們靠著看瓊瑤、三毛、金庸理解男女關系,她們仍然不由自主把愛情看作是人生唯一的救贖,她們看上去非常摩登,其實內在異常傳統,這導致了她們給自己的人生選擇少之又少。
其次是外在世界的擠壓。
受過高等教育的70后,不能說是不幸運的,他們確實是天之驕子,一出校園就碰上開放開明。整個社會處在上升期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只要稍微努努力,彎彎腰,就能拾到滿地的稻穗。當然,作為第二性,她們享受的紅利大半是被同時代的男人拾剩的。這恰恰也造成了她們的不幸,波瀾壯闊日新月異的三十年,這三十年里情感關系和社會結構的轉變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會讓人目瞪口呆,而對于擰巴的天真的脆弱的又自以為一切盡在掌握開局太順的人來說,面對這種外在世界與精神世界一再被解構和重建,實在是太難了。
身處急劇變化的世界,其實需要極其堅強的神經。
如若不然,崩潰幾乎是必然的事。
女詩人辛波斯卡說的:“沒有一塊石頭或者一朵石頭之上的云是尋常的,沒有一個白晝和白晝之后的夜晚是尋常的。總之,沒有一個存在,沒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尋常的。”
四個在重點大學讀外文系的女生把乘坐頭等艙當成了她們美好未來生活的一部分、她們勢必實現的人生理想。這當中既有少女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也有其后明顯的階層賦義。在她們最心高氣傲的季節里,理所應當地覺得自己應該得到全世界,勢必也應該成為這個社會“頭等艙”的乘客。事實上,她們中的大多數也真的實現了這個理想,她們撞中了時代,她們是受過高等教育又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百舸爭流里拔得頭籌的頭等艙幸運兒。
但是頭等艙終究不是終點,只是一段旅程,沒有人可以永遠坐在頭等艙里。總有一天,她們會從里面出來,而等待她們的是什么樣的生活?
我想寫的正是這樣一個關于劇變關于幻滅的青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