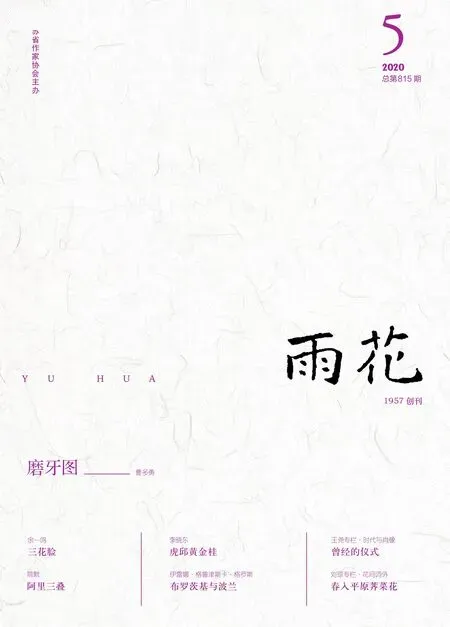好故事
啞石
劑量
惡確實像腐臭,讓人有身體反應。
惡,也可以是頑石,在某些
結構基座那里牢牢生根,甚至,
石化雛鳥數代的夢境。對于
我們這些風翼下微微搖晃的俗人而言,
唯一可寄望的是:惡,最好
成為一種鍛造,鍛造新物的雛形。
而在鍛造者手邊,除了鐵砧,
還有一木桶清洌的冷水——向必然
不稱手的月亮,彎腰挖掘。
小劑量之惡。我們是小劑量的。
永遠不要奢望眼眸中的月影,
木桶中的銀鳥,有磐石的身軀!
微涌的,淚水的光輝,緊咬著嘴唇。
門禁卡
嗶一聲,小區的鐵門被刷開。
電子門禁卡,我都還沒收好,
那個褲腿上沾滿干鳥糞、白漆點的
家裝師傅,就已從旁側搶身而出:
一股濃煙,一群群灰翅膀,
從我身后詭秘的安靜中搶身而出。
回頭望了望,驚異于自己
有一絲惱怒,又對粗疏、沉默的
蠻勇,有著云翼的理解性認同。
他們不會回頭,如獅子再回頭。
這小區,春末晚霞的一千匹
彩練和一萬種消息中,蹲伏著
喉嚨被鐵絲網死死勒緊的狂暴野獸。
歷史的清單,往往無物可替換,
遠眺者,遞來夜冰和濃煙滾滾的手。
隱秘智能
蜂群筑造新式蜂巢,以適應陌生,
假如這世界真可以陌生。
多年前你用過的蜂窩電話,此刻
收縮成一滴回旋珠淚,洇漫、
咆哮在耳聾老人鎮定自若的耳道里。
黃昏下,馬兒回頭舔自己肩胛,
一枚枚蠅卵,被潮濕舌頭
卷走,送進馬兒黑暗而溫暖的胃——
多么危險,實則是你難以了解
的新生。現實中,每人一身虹彩的
信息盔甲,翻卷著層層魚鱗:
請警惕那手握柳葉刀的悲憫先生吧,
死亡不早也不晚,長進頭頂星群。
好故事
她講的故事:
一個森林族群,濕氣和無名木紋的
洶涌,將其遷移到平原、坡地。
因擁有蜿蜒地底的復雜技藝,
他們陽光下建城池,幾千年挺立。
新國度。那潮濕、幽深的傳說,
也跟著裊升,在瞳孔微涼的花瓣里。
他接著講的故事:
當高效腦機接口可發絲樣
種植進頭皮之時,我會
負責觀察人形被落日的威嚴凝定。
冰鎮的飛鳥,雙眸,還在
細細沸騰。遠處的城市,
折疊在褲兜里;所有夜晚,
它都會邀請你來參加慶功酒會;
和你通話的植物,每天,
其人性,都有數次開花的躍升。
我們把這一切看在眼里。
當一種我們未曾得見的喜悅,
斟滿你,好奇野蠻年代
肉體竟有莫名苦痛,它那
可以解除任何莫名的寬闊的精準,
將有一絲霧氣的不解:
黑暗過往成為深海壓艙石,
某種新穎的孤獨,洶涌,透明。
我們一起講的故事:
(在你聽覺的藤蔓上摘下一粒葡萄,甜)
(星空的隧道我們共同經歷)
(月光照方舟上的一粒芝麻,散發神秘香氣)
歷史沉船剪影
站在潮汐肩頭,眼睛再專注,
也望不到月球的另一面,
那旋轉的、永不轉向你的一面——
船,從燒烤攤旁的涌流探出身來:
“不反感寫韻文,但著實憎惡
誰在夜色傷口上,刺繡出一個鮮艷。”
人性沒有給咽吞者一種恰切的
自然語言,卻替他晨昏煩憂。
烤茄子有鯨魚味,似乎無須重新加鹽。
“真的嗎?”“詞語,承擔了讓
一個個煙熏故事長久流轉……”
麻辣烤腦花,已由鐵質烤盤遞至嘴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