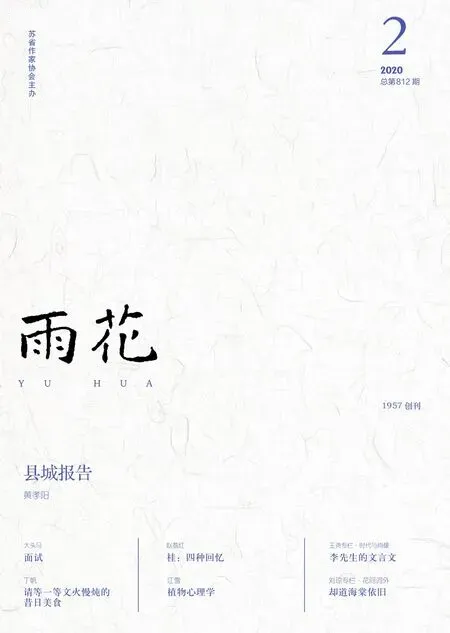“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
溫潘亞
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人人都是評論家的時代,面對任何一部文藝作品、任何一種文藝現象,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見解,每個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評論,或長篇大論,或片言只語,甚至不作一言,僅僅發一個表情,點一個贊。有的借助傳統的紙質媒體、電視影像,有的委身或隱身于當下的各種網絡新媒體。總之,與海量的文藝作品相伴的是評論的泛濫與泛化,甚至泡沫化、快餐化,面對不斷涌起的泡沫,帶給廣大受眾(包括讀者、觀眾、聽眾)的是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于是,真誠的、嚴肅的、符合批評對象特點的文學批評越來越少、越來越弱,甚至被泡沫淹沒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文藝批評褒貶甄別功能弱化,缺乏戰斗力、說服力,不利于文藝健康發展。” 要“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 “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一句樸實的語言卻極為精準地概括出了文藝批評的根本要求。我長期在高校從事文學評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目前擔任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和泰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習總書記的講話使我深切地感到,文學批評工作者必須加強學習、履行職責、踐行使命,開展批評時要深入作品、立足生活、關注社會、服務人民,要直面問題、敢說真話、善于發聲、勤于批評。至少要做到以下三點,其實這也是我的文學批評觀:
一、履行自己崇高的職責。文學批評工作者首先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和使命,高度重視文學批評,積極開展文學批評,在批評的過程中要弘揚時代的主旋律,弘揚正確的價值觀,追求真善美,鞭笞假惡丑,更多地發現和褒揚優秀文學作品。在這商品化大潮滾滾而來的時代,在這人的欲望得到充分釋放的時代,在這西方各種社會思潮包括文藝思潮不斷涌進的時代,在這崇高和偉大不斷被消解的時代,批評家們尤其需要履行自己的職責,踐行自己的使命,堅持自己的追求,保持自己的操守,面對各種批評對象,海量文學作品,要敢于發聲,敢于亮劍,不斷發聲,積極發聲,切不可同流合污,和光同塵,人云亦云,不知所云。
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當前我國文藝創作方面存在問題的概括和分析是極為精準和到位的,也是非常犀利和深刻的,他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他指出,當前我國文藝最突出的問題是:浮躁。以長篇小說為例,我國每年的產出量早已超過萬部,有的寫手每天創作過萬字,其中有多少泡沫可想而知。這使我想起了雷達先生2006年在《光明日報》發表的《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一文,他對這種現象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認為創作上的浮躁現象源于兩個尖銳的、幾乎無法克服的矛盾:一個是出產要多的市場需求與作家“庫存”不足的矛盾;另一個是市場要求的出手快與創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規律發生了劇烈的矛盾。現在我國文學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揚正面精神價值的能力;第三是缺少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性把握能力;第四是缺少寶貴的原創能力,卻增大了畸形的復制能力。面對這些問題,批評家們如果還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瞻前顧后、怕東怕西、做老好人,那么,這樣的批評必然是問題眾多、漏洞百出、胡言亂語、行之不遠的,也失去了它的時代意義、社會價值,甚至會害人害己,誤導受眾。
在網絡文學日趨繁盛的時代,在文學作品海量涌起的時代,在粗制濫造成為常態的時代,尤其需要文學批評家們履行自己的職責,踐行自己的使命,投入精力,披沙瀝金,拂去泡沫,發掘佳作,發現經典,敢于說話,勤于批評,多說真話,將好的、優秀的文學作品推薦給廣大讀者。
二、發出自己真誠的聲音。面對批評對象,文學批評家要不說假話,不說空話,不說套話,要說真話,努力發出自己真誠的聲音。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古人所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的“立言”,對今天的批評家包括我本人來說可以說是很難做到的,但這卻是每一個評論家必須一生堅持和堅守的基本追求。就我個人而言,從我1985年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評論文章,也是我的本科畢業論文——《班固及其<漢書>評價芻議》,到我最近的評張新科的長篇小說《蒼茫大地》的文章——《妙筆慰忠魂 奇文贊雨花》,近四十年來,百余篇文章,不做泛泛之言,不為人云亦云,我盡可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發出真誠的聲音。
以我對十七年歷史劇研究為例,我們若以當下純文學或經典文學的標準來衡量,那就是基本否定,就很可能失去這個批評對象,我在全面仔細深入閱讀這些作品后感到,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它們的價值,也許其文學價值并不太高,但它作為文學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歷史環鏈,它的認識價值、它的活化石意義卻是非常大的。于是,我運用福柯的話語理論進行觀照和研究,形成了我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后出站報告——《象征行為與民族寓言——17年歷史劇創作話語形態論》,由三聯書店出版,論文還入選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編的全國第一屆中國文學研究博士后論壇論文集——《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研究》,主要內容被《新華文摘》摘錄七千余字,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
發出真誠的聲音,關鍵是要遵從自己內心的感受。每一次面對批評對象,我不從已有的資料或文章入手,而是先讀作品,尊重自己最初的閱讀感受,由此出發,并以此為基礎,再收集資料,學習相關文章,再從學術研究的高度進行分析和闡釋。記得1980年到南京師范大學上學時,有一次我參加課堂討論,是關于《威尼斯商人》的。我在初讀作品時感到,對劇中人物夏洛克不應該是完全否定的,于是,我在發言時就大膽地講了出來,當時我的外國文學任課老師是許汝祉先生,他點評時充分肯定我的觀點有新意,但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他竟用近一節課的時間分析和闡釋我的觀點的偏頗之處。幾十年之后,我發現對夏洛克形象的分析,仍然有許多人的觀點與我當年的觀點是一致的。前些時候,我與當代著名的莎士比亞研究和翻譯家傅光明先生交流時,又談到這個問題,他從宗教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做了詳細分析,也認為我的閱讀感受和所提問題是有一定道理的。寫本科畢業論文時,我也是先從我的閱讀感受開始,記得在讀《漢書》時,我感到其中的許多篇章可讀性很強、文學性很高,但學術界卻只是充分肯定《漢書》的史學價值,關于文學成就都是一帶而過,甚至都不提及。但我卻相信我的感覺,于是就以《漢書》的文學價值為研究對象和論文選題。記得當時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是張瑗先生,他讓我一次次地修改,一直到臨近畢業才同意定稿,使得我非常惶惑,以為有什么問題。事后張老師跟我交流時才說出原因,他認為我的選題好,有價值,只是學術功力還不足,所以才讓我不斷收集資料、認真打磨。畢業分配時,擔任系副主任的張老師還因為我的這篇文章認為我適合從事學術研究,因而推薦我直接分配到了高校工作。回首過去,我深深地感念兩位先生,是他們從我的發言和選題中發現了創新或者有價值的東西,還充分地肯定和鼓勵我,這些創新和有價值的東西想來可能就是來自我內心最初的感受。
三、提升自己審美的能力。前面說的這兩點,如果沒有審美能力做基礎或前提,那一切也就無從談起。我在高校從事中文專業的教學工作,在長期的實踐中,我感到提高學生的文本細讀能力是提高審美能力的最重要的基礎,而文本細續的缺失恰恰是當前我國大學中文教育(其實也是基礎教育)存在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如今的中小學語文教育已經完全應試化了,再生動的美文也被大卸八塊,變成了寫作背景、作者簡介、段落劃分、課文講解、中心思想、寫作特點、作業布置、課后測驗等八股形式,包括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等這樣的美文也是如此。一篇篇內容豐富、情感生動、語言優美的文章被設計為一道道標準化的可以用機器判分的考試題,是那樣的枯燥乏味、令人生厭。大學的文學史教學其實就是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延伸,老師們基本先從時代背景、作家生平、創作道路講起,思想內容是重點,歸納了一條又一條,可以說是頭頭是道,分析得深入,挖掘得深刻。但是,講到文體形式、敘事技巧、抒情方法、語言特色、審美風格等這些能夠提升學生審美能力的形式要素時,常常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言之無物、照本宣科,僅僅歸納出幾點條條杠杠讓學生死記硬背、應付考試,因為有些從事文學史教學的老師沒有接受過關于文本細讀和文本分析的專門教育和審美訓練,自然也就不具備傳授的水平和能力。加之我國的幾千年文學傳統多強調文藝的載道功能,這樣的文學訓練何談提升審美能力和鑒賞能力?這也就造成我們今天許多文藝批評文章的先天不足,即不擅長或者不會進行文本細讀和形式批評,不會帶領廣大受眾從作品中領略和感受抒情意味、藝術真諦、審美力量。這就需要我們廣大的文藝批評工作者盡快補上這一課,不斷提升自己的審美能力。
我在寫作博士論文和博士后出站報告時,以福柯的話語理論為批評武器,堅持從文本細讀和文本分析出發,尊重自己的閱讀感受,將十七年歷史劇的形式研究作為文章的重點,論文共五個板塊,涉及文本形式的就占了四個:激情形態、結構形態、語言形態、藝術風格就占了四個,在答辯時受到了專家們的一致好評。回想起來,我的這種能力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我對作品的大量閱讀、認真體味、仔細感悟,以及接受馬列文論、中國古典文論、西方文論等的長期滋養。可見,提升審美能力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長期堅持和學習。
需要說明的是,從事文學批評工作,需要具備的素質很多,我從我長期的批評實踐和藝術追求出發,自感這三點最重要,謹供大家參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