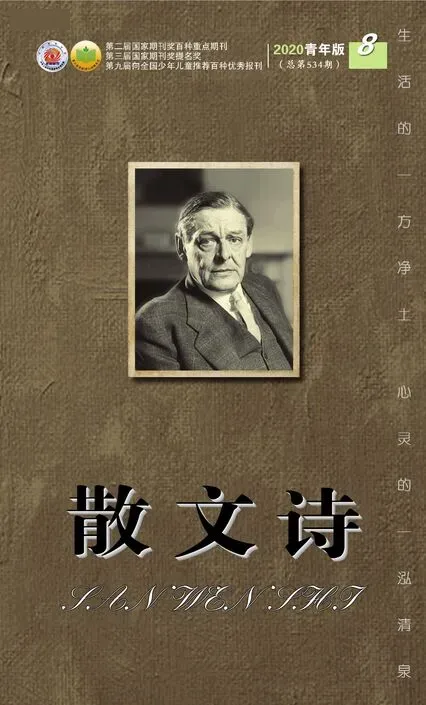土地里端坐著一龕人(外一章)
2020-11-22 15:15:22燁水珠華
散文詩 2020年16期
燁水珠華
我不與莊稼對視,因為那些搖晃的植尖,似乎沾染盡祖輩的血與汗,而愈發威嚴。包括那一個個微小的墳塋,在遼闊的藍天下,抵御四季的流光與風寒。我聽任一百種生物途經夜色,奔波在月影里,神秘,慌亂。聽任田鼠家族的聚會,令村民的夢鄉更加喧鬧。大家共同享受收獲帶來的喜悅,挽起手,像蒜瓣一樣緊緊擁抱。
大地一歲一枯榮,多少耕田的人就葬在他們生長的地方。村民會老,村子會舊,唯獨田野的風,刮過鄉間,撞擊一代代人的胸腔。活著,血液中土性奔涌,死后,墳尖也要銳利。
縱然一生負重,但絕不彎腰。
我始終不敢與莊稼對視,因為那溫暖的土地里端坐著一龕人,也只容得下一龕人。他們失去具體的形狀,已變得模糊不清。但你去任何一個村子走走,或許就能從那些渾濁的眼睛里,看見那人的影子,不屈而又堅毅。一如往常。
風 箱
村莊上立著一個老風箱,青灰,落寞,如鐫刻古老印記的墓碑。
它的推手上邊,還保留著奶奶的指紋。往日的爐火,化作燃燒的太陽,煨暖陷入回憶的人們。爐膛里的紅薯有一顆滾燙的心臟,照亮我黑漆漆的少年。老風箱又呼哧呼哧拉響,帶著饑餓誘發的恐懼,纏繞住每一條試圖蹚河靠岸的魚類。銀杏樹瘦弱,無花果被大狗咬斷,我腦子里的畫面,一塊塊被斑斕渲染。
風箱放縱通紅的火焰,舔舐沉默的鏊子。一群人熄滅,一群人點燃。燭光搖曳,窗外密雨斜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