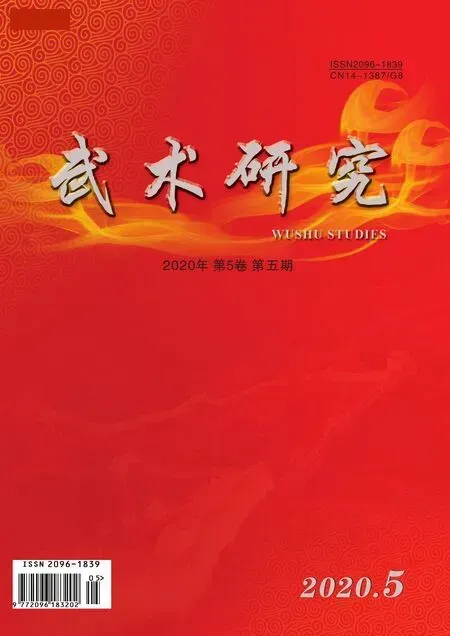厘革與創(chuàng)新:當(dāng)下校園武術(shù)回歸再思考
馮 劍
成都體育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自清末民初以來,中華武術(shù)扎根校園已有百年歷史,在這百年的演變進(jìn)程中校園武術(shù)經(jīng)歷了重重曲折,于是近代進(jìn)步人士將興國運(yùn)強(qiáng)民體的身體教育重任希冀于傳統(tǒng)武術(shù),進(jìn)而中國開始將傳統(tǒng)武術(shù)列入學(xué)校體育教育的范疇。當(dāng)下學(xué)校武術(shù)教育的諸多優(yōu)秀成果,多是由民國武術(shù)教學(xué)所啟發(fā)。因此,對民國武術(shù)教育的再認(rèn)識無疑對當(dāng)今學(xué)校武術(shù)教育的發(fā)展具有審時度勢的作用,“重新審視民國武術(shù)教育的經(jīng)驗(yàn),以謀當(dāng)時學(xué)校武術(shù)之所需。”[1]
1 賦魅——校園武術(shù)的入駐與本真
1.1 民族危機(jī)呼喚武術(shù)轉(zhuǎn)戰(zhàn)校園
“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2]溯源民國武術(shù)教育需從近代內(nèi)外交困、變亂頻仍的政治格局中出發(fā)。社會危機(jī)與文化沖突引發(fā)深層教育思潮,面對舊式教育造就的手腳無力、柔軟至極的青少年,中國的教育家深刻意識到國民體質(zhì)的強(qiáng)弱嚴(yán)重關(guān)乎著民族的興衰與危亡。于是,在近代思潮席卷中國局勢下,中國開始尋求富強(qiáng)之路,在增強(qiáng)國民體質(zhì)方面中表現(xiàn)為引進(jìn)西方的軍國民教育,隨即頒布《奏定學(xué)堂章程》并引進(jìn)西方兵事體操改造極弱的國民體質(zhì),無疑是中國近代學(xué)校體育的開端。但由于受“土洋體育之爭”的影響以及中外民族矛盾的加深,有人開始質(zhì)疑西方體育能否適應(yīng)中國社會現(xiàn)實(shí)需要,加之兵操動作僵硬,難以調(diào)動學(xué)生的積極性等原因,隨后就由武術(shù)代替兵操成為學(xué)校體育的主要內(nèi)容,賦予武術(shù)強(qiáng)國強(qiáng)種、重塑國民與國家形象的崇高使命。
1.2 民間武術(shù)為民國學(xué)校武術(shù)添磚加瓦
正由于“武術(shù)的體悟性、模糊性特點(diǎn)更使其傳承中存在著談玄授道貴乎有師的文化律令。”,[4]加之早期的學(xué)校武術(shù)中缺乏成熟的武術(shù)教師,進(jìn)而開設(shè)武術(shù)課程的學(xué)校在早期的師資來源大多來自民間聘請的拳師,如南洋公學(xué)聘請李存義作為該校的武術(shù)教員,劉殿圳先后任教于北洋政法學(xué)堂和清華學(xué)校,民間拳師在早期學(xué)校武術(shù)的發(fā)展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后隨著學(xué)校武術(shù)的成熟加之南京政府將中央國術(shù)館開設(shè)專門的體育師范專業(yè),其培養(yǎng)的學(xué)生成為后期武術(shù)師資的主要來源,有力補(bǔ)充各地學(xué)校武術(shù)在師資上的空缺。
民國時期學(xué)校武術(shù)的教學(xué)內(nèi)容無疑是民間武術(shù)對于學(xué)校武術(shù)的貢獻(xiàn)。如成立于1920年的北京體育學(xué)校規(guī)定其術(shù)科的教學(xué)內(nèi)容為徒手與器械,其中徒手練習(xí)中便囊括了太極拳、形意拳、少林拳以及擒拿法等,這些拳法即為該校的教育內(nèi)容,同時也隸屬于中國民間武術(shù)的范疇。民間武術(shù)充盈著早期學(xué)校武術(shù)的體系架構(gòu)。
1.3 “西學(xué)東漸”推進(jìn)武術(shù)入駐校園
“文化影響技術(shù),技術(shù)反映文化”[5]傳統(tǒng)武術(shù)由于深受宗族制的影響其傳承方式是依靠血緣關(guān)系或者模擬血緣關(guān)系的師徒制,又加之其傳承在傳承過程中的傳承對象相對較少,進(jìn)而在傳承方式上采取口傳心授,單獨(dú)授徒。但傳統(tǒng)的教學(xué)方式面對人數(shù)較多的集體或者班級就難施拳腳,進(jìn)而就導(dǎo)致出現(xiàn)“致使初學(xué)者,常有望門興嘆,興味索然之感”。[5]于是,民國的武術(shù)教員吸收西方教學(xué)思想,采用班級授課制并在教授的過程中通過口令將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內(nèi)容教授給學(xué)生。
由于傳統(tǒng)武術(shù)在習(xí)練方式以及其知識體系是借鑒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思想,同時受近代義和團(tuán)運(yùn)動和白蓮教等影響,民間武術(shù)一度被國人視為愚昧落后的行為,就造成當(dāng)時國人對于武術(shù)還存在一定的芥蒂,對武術(shù)還存在一定的誤解。近代的教育家借助西方的醫(yī)學(xué)知識、生理學(xué)知識對向國人解釋傳統(tǒng)武術(shù)的成為學(xué)校教學(xué)內(nèi)容的合理性。
2 祛魅——武術(shù)教育的困境與失語
2.1 學(xué)校武術(shù)難以突破競技武術(shù)的藩籬
當(dāng)前學(xué)校武術(shù)課程的內(nèi)容設(shè)置主要是根據(jù)學(xué)齡年級設(shè)計即小學(xué)三年級以武術(shù)基本動作、基本功、組合動作、初級拳、武術(shù)操為的主要內(nèi)容,中學(xué)階段主要以初級拳(第二路)、青年拳及對練、武術(shù)攻防動作為主,而大學(xué)階段主要以簡化太極拳、初級三路長拳、初級刀、初級劍、初級槍等、初級棍為主。反觀學(xué)校武術(shù)項(xiàng)目的設(shè)置雖然遵循循序漸進(jìn)的教學(xué)原則,但仍是以競技武術(shù)為藍(lán)本,進(jìn)而導(dǎo)致其嚴(yán)重的體操化現(xiàn)象,這與中華武術(shù)的內(nèi)容是有所背離的。中華武術(shù)是中華文化的衍生,競技武術(shù)在習(xí)練的過程中過多追求武術(shù)動作的“高”“難”“美”“新”,忽略了對學(xué)生武術(shù)中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與傳承導(dǎo)致學(xué)校武術(shù)失去其文化根基。再者,當(dāng)前學(xué)校武術(shù)的師資隊(duì)伍大多由師范類院校的武術(shù)專項(xiàng)生或者部分專業(yè)隊(duì)的退役運(yùn)動員組成,師范院校的武術(shù)專項(xiàng)生則是學(xué)校武術(shù)下培養(yǎng)的,這些教師大多常年習(xí)練競技武術(shù),因此,其在教學(xué)內(nèi)容則是以競技武術(shù)為主,如此傳遞培養(yǎng)學(xué)校武術(shù)的傳統(tǒng)文化就會缺失。沒有文化滋養(yǎng)的武術(shù)根基是不牢固的,實(shí)現(xiàn)長久的發(fā)展相對較難。
同時,學(xué)校武術(shù)的缺乏趣味性是阻礙校園武術(shù)推廣和開展的又一壁壘。由于學(xué)校武術(shù)的教學(xué)大綱其大致來源于競技武術(shù),尋本溯源,進(jìn)而導(dǎo)致其教學(xué)內(nèi)容與競技武術(shù)的內(nèi)容大相徑庭。對競技武術(shù)的“拿來主義”學(xué)校武術(shù)直接將競技武術(shù)的整套訓(xùn)練體系直接運(yùn)用于中小學(xué)武術(shù)教學(xué),過多追求“高、難、美、新”的競技價值,同時在教學(xué)過程中對于武術(shù)教材以及武術(shù)教學(xué)內(nèi)容的處理不當(dāng),進(jìn)而使武術(shù)的趣味性下降。再者校園武術(shù)的“競技化”側(cè)重于對學(xué)生身體技能的培養(yǎng),而忽略了武術(shù)作為彰顯民族文化,傳承民族精神的主要職責(zé)。“中國武術(shù)成為一項(xiàng)‘運(yùn)動的體育武術(shù)’,而遠(yuǎn)離了蘊(yùn)含著豐富人文思想的‘文化的武術(shù)’。”[6]
學(xué)校武術(shù)教學(xué)過程中武術(shù)文化的離場導(dǎo)致武術(shù)僅僅成為一項(xiàng)簡單的身體運(yùn)動。
2.2 學(xué)校武術(shù)的校園場域較狹隘
反觀當(dāng)前學(xué)校武術(shù)的現(xiàn)狀,深究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小學(xué)生課業(yè)壓力過大,學(xué)生的業(yè)余時間大多數(shù)用以增進(jìn)文化成績的提高,對體育的重視程度還有待提高。縱使部分學(xué)校重視學(xué)生體育鍛煉重視對學(xué)生體質(zhì)的增強(qiáng),但采用的鍛煉方式一般為非武術(shù)的之外的體育項(xiàng)目,以致于武術(shù)在校園的生存空間相對狹隘,即使政府層面大力提倡武術(shù)進(jìn)校園,但在具體實(shí)施中卻差強(qiáng)人意。分析此原因可從武術(shù)本身考慮即學(xué)生家長對于武術(shù)本身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誤解,競技武術(shù)難度高對身體素質(zhì)的要求高,對訓(xùn)練的年限要求高,而且難以取得成績導(dǎo)致武術(shù)難以突破競技體育的束縛。而對于傳統(tǒng)武術(shù)由于其缺乏其生存空間狹隘導(dǎo)致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傳承人逐漸減少,又加之傳統(tǒng)的體悟性、模糊性等特點(diǎn)與學(xué)校體育的教學(xué)原則有所背離進(jìn)而傳統(tǒng)武術(shù)回歸校園困難重重。
當(dāng)前學(xué)校武術(shù)老師由于受其培養(yǎng)模式的影響大多習(xí)練競技武術(shù),其教學(xué)內(nèi)容多是以競技武術(shù)動作為主,西方體育思想影響下的怪胎,表面上看學(xué)校武術(shù)是中國武術(shù)在學(xué)校體育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實(shí)則是具體量化的中國式體操動作,其背后的支撐并非純粹的中國本土文化亦或是校園武術(shù)中的西方體育文化占主導(dǎo)。因此,學(xué)校武術(shù)中過多的競技化教學(xué)或者只注重學(xué)生身體動作的練習(xí)削弱了武術(shù)文化的傳承以及對學(xué)生進(jìn)行武術(shù)文化的熏陶,學(xué)校武術(shù)則難以實(shí)現(xiàn)其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重任。
3 返魅——學(xué)校武術(shù)的回歸與重塑
3.1 學(xué)校武術(shù)回歸的具體路徑
“反觀當(dāng)前學(xué)校武術(shù)教育的價值邏輯,有著與民國經(jīng)驗(yàn)一脈相承的歷史演進(jìn)。”[7]武術(shù)項(xiàng)目與其他項(xiàng)目相比,最大的特點(diǎn)就是其囊括了豐富的傳統(tǒng)文化、蘊(yùn)含多元的民族精神,具有鮮明的民族特性。因此,可將校園武術(shù)視為民族傳統(tǒng)文化載體。傳承民族文化、弘揚(yáng)民族精神成為其教育價值的主要導(dǎo)向。即通過學(xué)生自身對武術(shù)的習(xí)練和體悟以及教師在教學(xué)過程中言傳身教,培養(yǎng)青少年對民族文化的認(rèn)知與認(rèn)同。當(dāng)前學(xué)校武術(shù)的發(fā)展?fàn)顩r,是學(xué)校承載傳承民族精神的重任,應(yīng)當(dāng)對當(dāng)前的武術(shù)教育反思。在幼兒武術(shù)教育中,由于幼兒學(xué)齡前的學(xué)生對事物的認(rèn)知能力較弱,應(yīng)當(dāng)以學(xué)生的武術(shù)啟蒙為主。可通過一些情景教學(xué)的方法讓學(xué)齡前兒童對武術(shù)有一定的了解,便于以后武術(shù)教學(xué),同時增加一些關(guān)于武術(shù)項(xiàng)目的趣味性如武術(shù)親子比賽。在武術(shù)段位制考試中可以增加關(guān)于考查武術(shù)基本知識的內(nèi)容,讓學(xué)生加深對于武術(shù)的了解。其次,對于大學(xué)生群體來說,可豐富武術(shù)課堂的內(nèi)容,如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將民國時期校園武術(shù)中的短兵運(yùn)動加入到武術(shù)課堂中,以還原武術(shù)的技擊性,同時激發(fā)學(xué)生對于武術(shù)的積極性。在學(xué)校武術(shù)競賽方面,可以適當(dāng)?shù)脑黾右恍┪湫g(shù)的功力比賽,進(jìn)一步加深學(xué)生對于傳統(tǒng)武術(shù)的認(rèn)識。
3.2 傳統(tǒng)武術(shù)回歸校園具體借鑒
針對學(xué)校武術(shù)陣地長期以來被競技武術(shù)占據(jù)這一狀況,可將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內(nèi)容納入學(xué)校武術(shù)的范疇。傳統(tǒng)武術(shù)進(jìn)校園首先應(yīng)當(dāng)解決的問題的便是師資問題,教師是教學(xué)活動中的中最為重要的一環(huán),因此增加教師的傳統(tǒng)武術(shù)知識儲備是實(shí)現(xiàn)學(xué)校武術(shù)教育傳承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實(shí)現(xiàn)體育院校武術(shù)專業(yè)學(xué)生課程內(nèi)容由競技武術(shù)向傳統(tǒng)武術(shù)中心的轉(zhuǎn)移是根本途徑。我國學(xué)校武術(shù)教育的師資來源主要來自專業(yè)體育院校或者綜合類院校的體育系,現(xiàn)代競技武術(shù)是其主要的教學(xué)內(nèi)容,這就導(dǎo)致學(xué)校武術(shù)的課程內(nèi)容束縛于競技武術(shù)體系。對于學(xué)校武術(shù)師資培養(yǎng)偏于競技武術(shù)這一癥結(jié),可在師資培養(yǎng)中增加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內(nèi)容或者根據(jù)學(xué)校的地域優(yōu)勢增加當(dāng)?shù)靥厣拇硇匀N,如河北體育學(xué)院將八極拳、披掛、苗刀等地方特色拳種加入到本校武術(shù)專業(yè)學(xué)生的教學(xué)內(nèi)容中并且為了保證拳種的正宗性還聘請民間武術(shù)家參與武術(shù)教學(xué)過程和校本武術(shù)教材的編寫。
武術(shù)教師下民間“采風(fēng)”也可作為高校傳統(tǒng)武術(shù)進(jìn)入校園的一種途徑。“真正的武術(shù)在廣闊的民間”,[9]學(xué)校武術(shù)教師應(yīng)當(dāng)主動與民間的師傅交流并虛心向他們請教,采集民間武術(shù)的長處,彌補(bǔ)自己的短處,長善救失,改進(jìn)自己的教學(xué)。如浙江海洋學(xué)院教師將民間拳師學(xué)到舟山船拳、七星對子等具有實(shí)戰(zhàn)技擊的傳統(tǒng)武術(shù)作為該學(xué)校的武術(shù)課教學(xué)內(nèi)容,通過“說招”“拆招”“喂招”等環(huán)節(jié)將傳統(tǒng)武術(shù)進(jìn)行條件性的攻防和對抗練習(xí)傳授給學(xué)生。經(jīng)過一學(xué)年的磨合,學(xué)生明顯喜歡上富有積極意義的舟山船拳和七星對子。由此可見學(xué)校武術(shù)教師通過自己深入當(dāng)?shù)孛耖g采風(fēng),虛心向一些身懷絕技的老拳師求教,并將傳統(tǒng)武術(shù)引進(jìn)學(xué)校并使學(xué)生喜歡上傳統(tǒng)武術(shù),這一模式可作為一條現(xiàn)實(shí)可行的途徑。
學(xué)校管理部門要重視武術(shù)師資的再培訓(xùn)。改變學(xué)校武術(shù)教學(xué)的現(xiàn)狀是一項(xiàng)系統(tǒng)工程,需要得到多方努力才能得到真正的改觀,這其中就包括學(xué)校教學(xué)管理部門對此的重視。在當(dāng)前強(qiáng)調(diào)“文化立國”、倡導(dǎo)“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的時代背景下,學(xué)校教育應(yīng)當(dāng)更加重視對中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和弘揚(yáng)。學(xué)校教學(xué)管理部門應(yīng)充分認(rèn)識到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載體的傳統(tǒng)武術(shù)在這方面所做出的的巨大貢獻(xiàn),真正把它提升到“弘揚(yáng)國粹”的高度去對待,因而重視起對武術(shù)教師的再培訓(xùn)教育使得為重要。傳統(tǒng)武術(shù)攻防技法的奧妙要求長期練習(xí)才能學(xué)到其精髓,其“身體性感知”的特點(diǎn)又要求手把手的現(xiàn)場教學(xué)方能領(lǐng)悟到真諦。這就需要學(xué)校制定相應(yīng)的鼓勵政策,提供一定的支持力度和條件,是教師有時間精力去拓寬自己的知識面,提高自己的業(yè)務(wù)水平。另外,一些老拳師受宗法、門派觀念的影響,不愿將自己的終身所學(xué)傳授與人,這也需要相關(guān)部門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