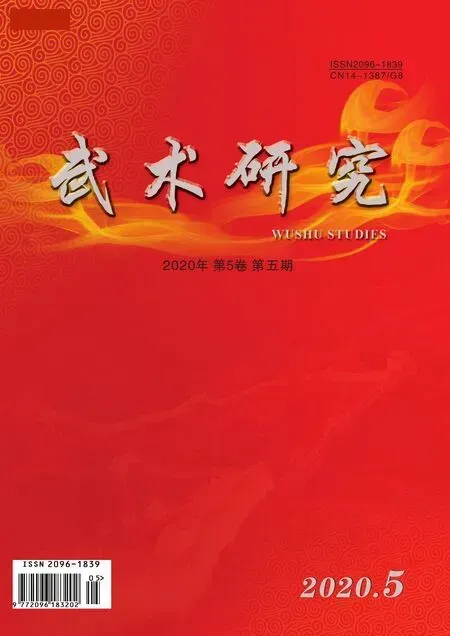英雄觀視閾下劍文化時代價值探驪
陳 希
成都體育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劍是武術兵器中一個重要的門類,被譽為“百兵之君”。劍是古代俠客行俠仗義的物質憑仗,更是彰顯“俠”英雄豪氣的 憑借。在春秋末期論劍、佩劍之風盛行,文人墨客論劍以示高雅,士吏佩劍象征身份,均勢佩劍以彰軍威,庶民佩劍以效 國法,當時佩劍論劍已超出其本身的物質范疇,上升到文化層面。在當代亦是如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中華民族 邁入新時代,而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牢固基石,其所涵帶的精神價值在新時期有其相應的表現(xiàn)形式,劍 亦然如此,為當代英雄在不同境遇下的優(yōu)異表現(xiàn)做出卓越貢獻。劍的精神對新時代文化傳承活體在育德、修身、文化交流 與傳播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劍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時代英雄觀的視域下予以探略,解釋者賦予劍更加豐富、更具時代特征的內涵,其形式亦會有相應的嬗變,但其精神文化核心不會異變,始終是以期冀當代社會積 極向前,使社會和諧蔚然成風。
1 劍的歷史溯源與象征意義
1.1 劍的歷史溯源
劍在發(fā)軔于原始農耕時代,始為勞動生產(chǎn)器具,隨原始氏族間因婚姻、領地問題而出現(xiàn)了原始戰(zhàn)爭,劍由勞動工具演變?yōu)?戰(zhàn)爭武器,加快了劍的衍化過程。劍的形制發(fā)生重大變化,現(xiàn)代我們將劍的外形定義為“劍是一種平直、細長、帶尖、兩 面有刃的短兵器。”[1]劍是一種尖銳的武器,在舊石器時期尖狀器物的出現(xiàn),到新石器時期“尖狀器已經(jīng)分化為多種器具,如石刀、石匕首、石刺刀、石矛、石戈”[2]等器物,夏商周時期青銅兵器的出現(xiàn)劍的本體功能逐漸顯現(xiàn),從1965年陜西綏德縣焉頭村出土的商代青銅蛇頭劍可以得知,劍在當時已經(jīng)參與軍事戰(zhàn)爭,并且由較短的匕首和較長的復合器械矛、戈 演變?yōu)殚L度適中的一體化武器。到“春秋戰(zhàn)國時,劍才正式發(fā)展成為一種重要的兵器,劍的擊刺技術也才正真臻于成熟 ”,[3]出現(xiàn)了一大批歷史名劍:吳王光劍、吳王夫差劍、越王勾踐劍、越王州句復合劍等,這一時期的劍與夏商時期的劍又有所差異,夏商之劍劍柄較長,劍身較細,然戰(zhàn)國時期劍劍柄短,劍身寬且厚,亦有短劍,如魚腸劍、秦夫人匕首,但其制作精良,便于藏匿與攜帶。春秋末期,佩劍論劍之風盛行,文人俠士都要佩劍與探討劍理,甚者全民佩劍,《史記 ·秦始皇本紀》記載:“其七年,百姓除帶劍”。漢代擊劍之術長盛不衰,“自天之至百官無不佩劍”,[4]隋唐五代也要佩劍,但是佩戴的劍由等級區(qū)別,劍的形制與材質也是區(qū)別身份的重要標志。宋元時期出現(xiàn)了十八般兵器排行,劍就一直在榜,從未掉落。今天的劍發(fā)展呈現(xiàn)多元化的格局,有的學者推崇“為推進武術入奧,提高中國武術的標準化進程與全球適應性,武術器械作為武術文化的代表性作品,也責無旁貸地需要進行標準化改革與嘗試,”[5]相反的觀點也不勝枚舉,批判之聲四方涌來,如呂艾文就言:“粗制濫造、低沉本的武術刀劍,在當今運動員嚴重儼然成為一種‘舊了便換,壞了便仍’的‘武術道具’。”[6]厘清劍的發(fā)展史,更好的為現(xiàn)代文化的發(fā)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1.2 劍的身份象征
劍作為一種符號,“伴隨著歷史的前進和傳統(tǒng)文化的浸淫,它已成為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文化負載力的文化存在形式 ”[7],在漫長的歷史中被解釋者賦予不同的內涵,在隋唐時期劍就被予以身份象征的意義。如尚方寶劍象征著至高無上的王權,且劍的不同形態(tài)材質意味著不同的身份地位。在《隋書.禮儀志》中明確記載:“一品,玉具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五品,并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 則象劍”。明確的指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佩劍是不相同的。地位較高的人佩劍材質與劍的裝飾自然要高人一等。文武分途后,出現(xiàn)了武士,他們是低級的貴族,或是已經(jīng)沒落的貴族,到了后期,武士大多來自與黎明百姓。他們學習武藝,擁有一定的才能,期冀躋身于上層社會,所以皆佩一柄好劍,用以與上層社會的士族發(fā)生來往,借人之勢,作己之事,同時完成社會階層的跨越。
2 劍的文化精神與當代英雄觀的內在關系
2.1 英雄坎坷——鑄劍精神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是千錘百煉的堅忍不拔,是千難萬險后的傲視群雄,是英雄的涅槃重生,是不畏坎坷的英雄氣概。在考古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中國古代許多名劍,代表性之一如越王勾踐劍,歷經(jīng)2500多年的歷史,出土時任然 “劍面如新,仿佛昨日才鑄成一樣”,[8]閃著寒光,16張白紙稍一用力就劃破了,足以見其鋒利異常。在如此長時間的氧化下,竟然不是銹跡斑斑,仍可吹毛斷發(fā),可以窺其當時工藝的精湛。然而在科學技術并不發(fā)達的古代,竟可以鑄造出如此高水平的劍,可能的解釋就只有鑄劍師將千錘萬擊的鑄劍精神溶于劍身之中了。鉻工藝可以防止氧化,是現(xiàn)代工藝的新生兒,是在科學技術強盛的現(xiàn)代被萃取出來的技術。鉻的提煉需要4000攝氏度的高溫,這是古代難以企及的工藝條件,然而我國古代就擁有這鬼斧神工般的技藝,靠的是工匠精神,這種迎難而上的精神對于當代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仍具有高度的引領作用。英雄謂之為英雄,是由于英雄不怕千錘百煉,不懼艱難困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有工匠精神,做事上要求極致,不被現(xiàn)實條件所打到,英雄并非天生就是英雄,其也有一個歷練的過程,要完成英雄的蛻變,需以烈火煉神、寒水淬心、萬錘磨身方可成之。岳飛的武藝不是與生俱來的,馮子材不是天生的軍事天才才可護關大捷,鄧稼先不是神童下凡成就兩彈元勛,王繼才不是生而孤僻專為孤島戍邊,袁隆平不是紙上談兵研發(fā)雜交水稻,這些人誰不是平凡人,他們只是做了自己鄰域的守望者,才成就了英雄偉業(yè)。這也許就是鑄劍精神對人格的影響,對英雄的鑄造吧。
2.2 英雄禪境——礪劍精神
磨礪是劍的最后一道工序。“一把好劍要經(jīng)歷粗磨、細磨、再到精磨,依次磨礪,直至平整光亮,脊線筆直,槽線標準,最后開刃的過程。”[9]磨劍還要配一個磨劍石,鑄劍師用其對寶劍萬般打磨方可所向披靡。雖然說起來鑄劍好像易如反掌,但是就其磨劍一項就足以難倒大多數(shù)人。古語講十年磨一劍,便是對磨劍的時間要求,這與佛家所講的“入禪”有異曲同工之妙。即要有平靜的心境才能磨出平如鏡、硬如鐵的劍鋒,鑄劍工匠內心的禪境就決定了劍的鋒芒與否。“禪”講心性,將心融于自然,融于清澈的泉水,不染世俗的塵埃。內心的靜噪反應與外便是對事物的處理方式的異同,或是寵辱不驚,或是患得患失。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亦能看出君子內心是不摻雜外物的。君子與英雄在人格與內心上是有所交融的,人格上“是道德的先覺者和踐行者”,[10]心境上二者都以理想的人格與道德來規(guī)訓內心。換言之,英雄的內心是平和的、不摻雜念的,是心無旁騖地對一件事的專注,這正是當下浮華社會所亟待的一抹輕靈。在大多數(shù)學者都在追求院士等級、文章發(fā)行量的科研領域,每年關于科研的文章不甚枚舉。但正如屠呦呦所言,她是一個三無科學家,沒有博士文憑,沒有留洋經(jīng)歷,沒有科學院士頭銜。但她腳踏實地,不求名利,潛心專注于困擾了人類病痛藥物的研究,最終屠呦呦找到了青蒿素。老人家在獲得諾貝爾獎后也并沒有心高氣傲,仍然是原來的那個小老太太,仍然搞自己的研究。這就是英雄的內心——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淡薄名利,是自緣身在最高層的英雄視角。
2.3 英雄霸氣——亮劍精神
狹路相逢勇者勝是遇見強悍對手敢于亮劍的精神體現(xiàn)。《亮劍》對其解釋為“古代劍客們在與對手狹路相逢時,無論對手有多么強大,就算對手是天下第一劍客。明知不敵,也要亮出自己的寶劍。”[11]英雄佩劍需勇于亮劍,此乃英雄俠客的氣魄與膽識,是對己的信任,亦是對來敵的尊重。亮劍精神在當今作用也非同尋常。當今世界格局動蕩不安,暗潮涌動,四面八方對我國虎視眈眈,我無心犯敵,敵人卻刻意制造摩擦,唯有亮出寶劍彰顯國威。面對四方威脅,我國一帶一路帶動沿路經(jīng)濟體快速發(fā)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全球意識,亞太經(jīng)合組織使得區(qū)域經(jīng)濟一體化,2010國慶閱兵“東風”最新型高精尖系列武器的亮相,更是大國雄風的呈現(xiàn)。這不就是亮劍精神,不就是實力與底蘊的展現(xiàn),民族精神的彰顯嗎。
2.4 英雄度量——回劍精神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說明英雄的氣度不在于一劍封喉,而在于點到為止。古代劍客劍指十惡不赦之人,又不斬手無寸鐵、手無縛雞之力弱者,突顯了高尚的俠義精神。現(xiàn)代擊劍項目也具有其回劍精神,即“所謂擊中即停,”[12]是擊劍運動武術 精神打典型呈現(xiàn),它要求運動員在競賽的過程中點到為止,盡量保證運動員雙方的人身安全。這不正是武術人謙讓的典范嗎?收劍彰顯的氣度,不是咄咄逼人,是傳統(tǒng)文化浸潤下“禮讓”品質的顯現(xiàn)。宋代《西溪叢語》記載:“道人有詩云:‘爛 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jīng)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13]英雄博大的胸懷與瀟灑的氣度就是在優(yōu)勢明顯得以凸顯時,對對手的尊重。一個不會尊重別人的人其成就也不會登峰造極。在當代,隨《區(qū)域全面經(jīng)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 》的深入,應對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將于日本實現(xiàn)貿易貨幣直接互換,不會再過度的依賴于美元,這就是我國彰顯大國風范,體現(xiàn)英雄氣質的典例。迂回的環(huán)節(jié)和鄰國之間的關系,不是我們忘記歷史,而是應該以大局為重,以和諧發(fā)展為時代主題,促進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建立,把各股力量匯聚一起,共同面對全球經(jīng)濟的浪潮。
3 新時代劍的價值體現(xiàn)
3.1 培養(yǎng)愛國主義情懷
“擊劍練武能陶冶情操,培養(yǎng)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14]辛棄疾失意作:“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將劍與報國情懷相統(tǒng)一,寄情于劍。唐代杜甫“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把劍和山河并論。古時還有許多詩人將劍于愛國聯(lián)系在一起,劍在戰(zhàn)爭前期作為征戰(zhàn)的武器,是將士建功立業(yè)的象征。將劍看作是男人建功立業(yè)的符號,如李白一樣,將劍是為破樓蘭的利器,實質是為抒發(fā)心中的愛國情懷。《晉書·祖逖傳》記載祖逖和劉坤二人練劍為報效國家,聞雞起舞,足以展現(xiàn)其愛國主義的堅定意志。古代文人武將以劍表其心,賦予了劍豐富的文化內涵,在“中國傳統(tǒng)的劍文化所倡導的愛國、俠義有異曲同工之妙。”[15]對當代的激發(fā)愛國主義精神依然有相當?shù)膯⒌闲в谩?/p>
3.2 寓情于劍,寄托人文情懷
傳統(tǒng)劍文化是武術文化的承載體之一,武術文化以傳統(tǒng)文化為母體,在千百年的滋潤下不斷豐富其內涵,使之成為現(xiàn)代文明的代名片。作為文化傳承活體的社會主體,在其發(fā)展演變過程中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傳統(tǒng)儒家“人本”思想,以“尊重個體、強調個性化的思維方式。”[16]去感悟劍對社會主體的人文關懷,同時劍作為一個器物承載著人的情感。劍與人是相互作用的過程,其蘊含的文化也是相互的結果。而文化終歸要回到人的身上,這樣的文化才會有傳承的活力,才會推成出新。 人本情懷還應該是個人情感的宣泄,予情于劍,寄托個人的思想感情。《詠荊軻》中“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陶淵明借荊軻仗劍出京,為精忠報國而舍生取義的精神,以此來感嘆自己未建軍功,而且身處黑暗 政治統(tǒng)治之下的憤懣之情。《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中,杜甫在觀看公孫大娘弟子舞劍時回憶當初公孫大娘舞劍時的盛況,從一言一行可以探究公孫大娘在大唐盛世時舞劍的愉悅心情與一種身處家國盛世的驕傲。
3.3 促進文化的傳承與發(fā)揚
文化在隨社會發(fā)展嬗變過程中,為適應新時代的內涵需求其形式會略有變化。不同時期文化價值在當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均有所顯現(xiàn),如劍文化在古代價值效用凸顯在“王者舞政治‘劍花’,人們以佩劍舞社會‘劍花’,同時,武術人利用自己的身體舞出新的技術性‘劍花’,大眾持武術劍舞‘健康’的‘劍花’”。[17]不同的社會階層對于文化的利用層次自然 迥異,但這是劍文化在歷史流變的進程中的應有之義,是文化傳承的應變之法。現(xiàn)實生活中佩劍的情況寥寥可數(shù),一般人們在活動鍛煉時可能會佩戴劍。但是劍的現(xiàn)代文化含義并不是要求人們配劍出行,而是將劍的精神內涵“與藝術聯(lián)系,與教育攜手,與生活鑲嵌,與健康交織,形成具有較大開發(fā)價值和開發(fā)空間的文化形態(tài)。”[18]對于文化的傳承方面,我們還要摒棄近代“師之長志以制夷”以西學為師的心態(tài),要做到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主流文化放在同等平臺平等對話,將傳統(tǒng)文化“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19]使得傳統(tǒng)文化具有大眾性與 普及性。 當然,文化的傳承還需要當代每個人自覺踐行,方法途徑各有不同,或融于體育,或結合生活,亦或者置于時代空間,然而無論形式如何,最終都應是積極做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揚者和踐行者。通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相互交融,使傳統(tǒng)具有時代特點,努力把傳統(tǒng)的做成民族的、國家的、世界的,為傳統(tǒng)文化的推廣鋪開一條廣闊的道路。
4 結語
劍文化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子基因,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如何發(fā)揮好劍文化在當下的作用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研究立足于倡導英雄觀的新時代背景下,探析傳統(tǒng)文化中劍文化在當代的現(xiàn)實意義。從梳理劍的歷史起源與時代象征,進而由英雄坎坷、英雄禪境、英雄霸氣、英雄度量四個方面淺析劍文化與新時代英雄觀的內在傳承關系。從而剖析劍文化的時代價值。將劍文化相融與社會生活,從實處弘揚劍的當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