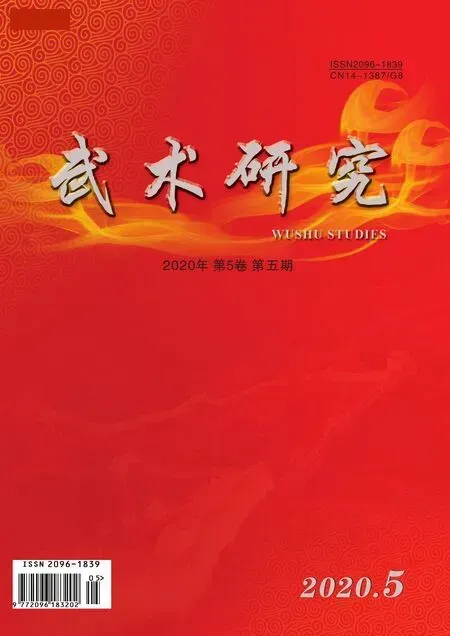文化層次視野下傳統武術的文化形態管窺
張 波
成都體育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在文化全球化的現代社會,存在著許多的機遇與挑戰,文化的研究對于促進社會發展的意義由此凸顯而出。傳統文化延續著傳統優秀慣習,承載傳統文化因子,是社會形態以及社會存在的學理表述。傳統文化以不同的社會需要踐履著不同的社會形式,而架構于傳統文化地基之上的傳統武術,則以相似的文化適應來踐行自己理應扮演的社會形態,可能該范式下的文化層次在傳統武術領域中,有著自己對于各層次的詮釋和論譯。但從宏觀維度上探究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其無論是在傳統武術領域還是其他社會領域,都理應遵循由低到高的社會發展過程,或許可以說這“是對中國武術文化數千年傳承延續內在規律的現代彰顯。”[1]探索傳統武術文化內在的層次邏輯以及其在社會中的演繹形態發現,在對其存在形態方面的研究還有較為廣泛的空間尚未涉獵,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挖掘,期冀為傳統武術現代存在及發展奠定應有的時代內涵。對文化層次的分化為視角進行傳統武術的社會形態淺析,以文化嬗變與發展的思維探尋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思考傳統武術為何首先是“安生立命”的本質追求,蘊含何種精神文化。
1 安生立命:傳統武術的社會生存文化
生,是個體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命,則是社會個體生的必須,即安生與立命是兩個相互依存的二元實體。拆之,表現為個體對自我的動態期冀,合之,呈現出個人存在對社會生活的現實需求。“生,進也。”[2]代表動態的生長嬗變,是對于個人發展的期望,同時還體現了人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即驅使命運的過程。社會個體在社會群體中的社會生存,離不開對環境的適應,環境改變又是社會發展的自變量,而個人在社會環境中的變化是隨其變化而逐步嬗變,但人作為擁有獨立意識的高級存在,僅在“變”的邏輯中討論其自主意識,理應占據社會變化的主體地位,這是人對于生的本能追求。進而在由生而命的價值追尋中,表述了文化意義的現實本質體現,即人對于個人“命”發展的訴求。如果說“命”是對于文化發展的過程,那“生”在此過程中則扮演了文化意義原點的角色。安生立命在傳統武術中的整體價值追求中,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看作是社會選擇的伊始,亦或說是人選擇傳統武術內在默契的緣由,因為這對于選擇者言,是為了在現實社會競爭中不被淘汰;從側面講,這或許是傳統武術在眾多傳統文化中凸顯而出的一個重要元素。
安生立命是傳統社會對于個人在社會中的基本要求,是傳統文化浸潤下思維的具體呈現。同時武術這一技擊活動是征戰沙場的現代藝術化社會形態,人們在戰亂環境的場域下,自然進化出尚武基因,“‘強健體魄’與‘尚武圖存’是武術產生與傳承的重要動力”,[3]在傳統武術針對身體維度進行育化效果下,社會主體為了本我的社會基本安全屬性,選擇傳統武術這一技擊與健身皆具的活動或許是可靠的選擇。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利弊考量之后,便形成了一個較為安全和保守的思維體系,即“武術成為了傳統時期人們維護本體性安全的工具, 同時也作為保身強身的身體活動成為人們’忙時種田, 閑時造拳’的生活方式”。[4]不僅如此,安生立命還是社會空間中的生存常態,這是由于傳統文化規約之下的“出世”理念熏染,他與儒家思維邏輯中的不偏不倚有著相似的現實表現。首先,出世與中庸都是中國土地育化的傳統文化哲學,其次,二者都講究不爭的處世之態,在傳統武術的社會現實呈現中,以安生立命來表現它的文化思想以及現實形態似乎再恰當不過了。
2 多維呈現:傳統武術的社會文化形態
社會生存是傳統武術立身之本,但在伴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以及文化全球化沖擊,倘若傳統武術仍停留在簡單的社會生存維度,這樣或許連基本生存都將難以維系。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恰如其分的詮釋了傳統武術的現實境況,可能探尋傳統武術的現代化多維文化形態能為傳統武術發展厘清一條出路。
2.1 物質文化的武術裝束
武術人的著裝標識著他所代表的文化群體,武術服裝則是較為鮮明的標識符號之一,同時武術服裝也具有民族文化象征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講,武術服裝更是重要的武術儀式。武術服裝伊始于古代戰爭時期的軍事服飾,隨著武術與軍事的逐漸分離,使得武術服裝也與其脫離,演變為娛樂表演的活動。手工業的發展使得武術裝束風格發生嬗變,“同時適應民間娛樂的需要, 既務農又習武的現象十分普遍,”[5]并在武術娛樂功能逐漸顯現的進程中將其普及,這就致使武術服裝在民間社會得以流傳,并形成民族文化符號。“新中國成立后, 武術運動得到了順利開展,作為表演項目,其技術、規則得到了完善,同時期,現代武術服裝的概念才逐漸產生, 在武術的服裝上也開始進行規范。”[6]武術服裝的嬗變過程則呈現出一部歷史演化歷程。
在現代的武術競賽和武術表演中,都要求表演者身著傳統武術服飾,這是傳統文化的宣揚,也是文化自信的現實表達。除了對傳統文化的意象聚集之外,“武術服裝在表演場或競賽場上要方便武術技法的展現,更指其在日常生活中也要適合穿著,甚至能夠引起非習武者的興趣, 使穿著武術服裝成為一種時尚。”[7]它對于身體的護衛取向是傳統倫理的自在之辯,體現為傳統筋脈的溫寒有序,又內隱著身體哲學的身體深層的真正意蘊,正由于種種文化現象,或許才可以探驪武術服飾的傳統文化形態,并在此基礎上理解的一種中國式的“一切以身體為準繩的絮矩之道”。[8]如傳統武術服裝的長袖上衣,不僅體現出傳統的中國式紐扣設計,還加入了中國獨有的水墨文字,更為重要的是寬松的衣物將身體至于一個較為舒適的環境之中,以“麻”為材質使得武術人有一個迥異于“絲綢”柔軟感觸的身體體驗。不僅如此,中國人講究風寒入體,而較為封閉式的裝束則將外界的濕氣和寒氣阻隔在外,由物質的本能屬性為身體的本質屬性構建一個具有文化內涵的健康形態。
2.2 行為文化的點到為止
點到為止是傳統武術技擊理念的處世哲學,它有別于古羅馬斗獸場的殘酷,也不同于西方地下拳擊的招招致命,他更趨向于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儒者風度,從另一層面講,它或許可以看作是止戈為武的技擊體現。點到為止的行為哲學是武者之間行為的外化,由點到止是身體技擊范式的德行育化,到傳統武術的整體文化感知,開顯了一種人文主義情懷以及武者與武者之間的技擊默契。有點觀止亦是一種自我修養的彰顯,點是武術技擊本質的身體表現,而止則是大道歸途的深層內斂,二者是一張一弛的文武結合,同時還是由外及內的心靈修養。傳統武術中交手的情況屢見不鮮,但卻少有聽聞武術交手而出意外的言語,他與西方擂臺格斗大相徑庭。文之,可以比武招親,這是其武的野蠻行徑為文的文明行為所用,它是武者文斗的典例;武之,亦可為家為國,戚繼光用武術創建戚家軍,為捍衛國土立下汗馬功勞,少林棍僧救唐王亦是一段歷史佳話。
點到為止在武術技擊理念中還呈現出較為復雜多維的特性,它既有“學重對試,搏中要害”[9]的特征,也具有適可而止的靈活應變,這是傳統文化不落窠臼的智慧圭臬,呈現出感性行為與理性思考的辯證結合。感性技擊行為不等同于對技擊的褒貶,反而是對技擊本能的禮贊,“在古代,武術主要是以一種技擊技術而存在,它的主要社會價值是技擊”[10]則是對其凸顯。而在感性身體接觸的技擊中融合理性的思考,即在身體接觸的時候或減小力道、或淺嘗則止、或以鈍器代利器都是傳統禮讓的多維范式。這在傳統文化浸染下生成的君子品行,不會因他者文化的沖擊而發生質變,其點到為止的君子禮讓是文化智慧和自我能力的綜合形態表現。
2.3 制度文化的抱拳禮儀
拳與掌的結合不僅可以是攻與防的招架,更是“武林中共同通行、約定俗成的禮儀規范,”[11]抱拳禮在武術人之間得到應有的禮贊,師傅與弟子之間、同門之間以及武林同道之間都以抱拳禮來表示尊重。而單論抱拳,它是武者在社會活動中技擊意識的身體意向,它是不動而動的先發制人,同時又是欲動不止的靜觀其變,即一個簡單的抱拳就將對戰的格局優勢引到自己的一方。在古代行走江湖時,抱拳這一動作是為了避免兩人的肢體接觸而形成的獨特的問候方式,源于古人對于人性的朦朧認知,得出了防人之心不可無經驗化結論,即抱拳禮應運而生。同時,在混亂的武林之間,確實有少數行為未必光明之人,這時抱拳禮就是儒雅的自保行為,這都是歷史現象以及應對復雜社會現象的傳統文化智慧顯現。
抱拳禮是武術人特有的文明禮節,“由于它的充分發展和完備的形式,使它在形式上成了一種特殊的負載工具,”[12]其承載了武術人的文化傳承,繼承了傳統文化基因,蘊藏了武術人所獨有的儒俠氣節。它的意境內涵和現實踐履是難以隔離的面線維度,如在現代武術競賽演練中,上場、下場以及侯分都要行抱拳禮,現實要求的身體規訓使其對個體禮的教化層累,從而使得個體沐浴于傳統文化的場域之中,為傳統文化中的謙遜與禮讓得以流傳與延續。抱拳禮只是傳統武術文化中的一個代表,僅是武術文化的一個意向符號,除此外,還有武器之禮,如習練的槍要有紅纓,刀要有刀彩,劍要有劍穗等,這都是武術禮儀的具體現實形式,表現為武術人對于武術“伴侶”的認同。無論是對人之禮,亦或是對器之禮,理應都回歸于對人的育化,彰顯的是傳統文化的謙遜之風。
2.4 精神文化的授者如父
師父是一個中國文化中獨有的稱謂,傳統武術上講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它是“以宗族和血緣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傳統武術文化傳承體系的根本源于我國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社會生產方式”,[13]雖然不是血緣的天然延續,但卻是在社會關系之中生成的類(似)血緣的親子模式,師徒是和父子是相等同的社會關系。這種仿血緣關系的出現或許是宗法制度下的團體利益聚集,如傳授者要將所學的全部武學毫無保留的傳授予徒弟,以免徒弟在外行走江湖時壞了自己的名聲,同時也有對傳承者的期望,希冀所傳之人能將自己全部武學發揚光大,這種無私的傳承同樣是傳承者對于其師父的承諾,亦是傳承人為傳承傳統武術的一腔熱血與奉獻。這是師徒之間的一個默認傳承機制,它與傳統武術的習練一般,無需話語的重復警醒,更多的是師者內在的標榜意識遷移。同時,師父在對徒弟的言傳身教中,無意識間便產生了師徒情感的跡化,使得師徒關系以及師徒傳承變得自然得體。這種情感的代際流動,則是武術精神的延續。
在傳統文化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傳統武術的傳承將師徒這一宗族與血脈體制的系統納入其中,不僅僅為技擊之術的發展具有重要功效,而且為傳統武術的精神文化傳承同樣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如霍元甲在不戰而勝俄國大力士之后,武術精神就得以凸顯,其弟子在霍元甲去世后就將精武精神保留下來,這就是傳統師徒間的精神文化傳承,同時這也是傳統文化氤氳下的文化傳統慣習,因為“傳統本身就是一種文化。”[14]這種師徒的精神傳承就是傳統文化內涵的繼承。無論是情感的連結,還是師徒的類血緣關系,無非就是將武術文化在社會之間傳遞下去,換言之,情感與師徒關系都是精神文化的承載體,二者皆旨趣與傳統武術的精神傳承。
3 結語
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之下,傳統武術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或許此時應該厘清傳統武術的現代文化形態,希冀為傳統武術的發展做出一點幫助。由是觀之,文化分層而呈現出的文化社會形態,以安身立命的社會生存基本需求出發,連結了“生”與“命”的人生發展邏輯哲思,構建了生與命的辯證依存體系。同時在安生立命的生存需要之后,則是傳統武術現代社會的文化多維形態,彰顯于物質文化上的傳統武術裝束、行為文化上的點到為止、制度文化上的抱拳禮儀、精神文化上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精神文化傳承。對傳統武術的文化形態的理解與認知,或許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因為對于發展的文化而言,文化形式亦是不斷變化的,探究傳統文化核心的永恒以及外顯的變化,或許才能更好的傳承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