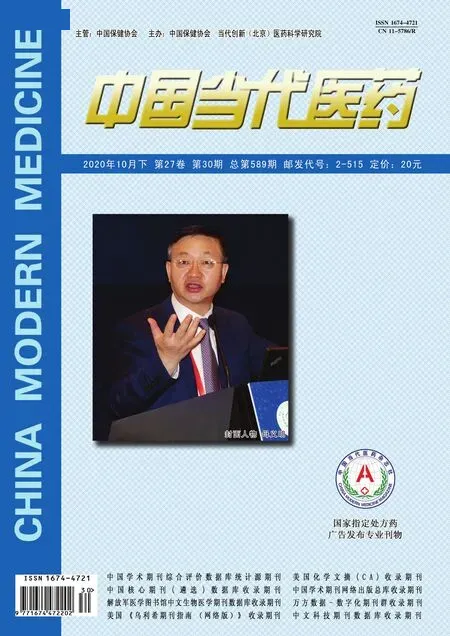3D打印模型在脊柱外科疾病教學中的應用效果
程曉非 徐 辰 干耀愷 楊二柱 黃澤楠 趙 杰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骨科,上海 200001
我國目前已逐步步入老齡化社會,各類脊柱疾患的病例逐年增多,在骨科主要疾病的教學過程中,脊柱外科也是授課重點之一。在脊柱外科學習中,熟悉脊柱結構的解剖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當前醫學教學過程中,解剖學通常安排在前期學習[1-4],同時骨骼標本相對缺乏,使得進入臨床專科學習階段的學員對于脊柱解剖沒有直觀的感受,這直接影響了教學的效果[5]。在當前臨床工作中,影像學檢查是了解脊柱組織結構異常變化的主要手段,雖然目前的CT 重建可以較為直觀地呈現脊柱的三維結構,但其本質仍是一種偽立體模型,需要在頭腦中構建一個3D 結構模型,完全基于個人理解和經驗學識。而對于沒有基礎的學員來說,需要的是全面和直觀地觀察脊柱結構。而3D打印是一種全新的快速成型技術,具有制作快、成本低、精度高等優勢,目前在醫學、工程、材料等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6]。特別是在骨科臨床應用中,使用3D打印技術將病患的骨骼CT檢查數據轉化為實體模型,便于對病變部位的形象化觀察,彌補臨床教學中的不足[7]。本研究選取在我院進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32名學員作為研究對象,探討3D打印模型在脊柱外科疾病教學中的應用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9月~2018年9月在我院進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32名學員作為研究對象,采取抽簽法將其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16名。實驗組中,男9名,女7名;年齡24~27歲,平均(25.94±1.48)歲;進入基地前理論考試成績(78.54±5.12)分。對照組中,男8名,女8名,年齡24~28歲,平均(25.56±1.32)歲;進入基地前理論考試成績(77.18±6.32)分。兩組學員的性別、年齡、進入基地前理論考試成績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納入標準:①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在上海第九人民醫院規培的15級碩士研究生;②學員年齡24~28歲;③學員進入規培基地前理論考試成績為70~85分。排除標準:①外校及八年制規培學員;②年齡<24歲或>28歲者;③進入規培基地前理論考試成績<70分或>85分者。本研究經過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本教學所涉及的典型病例的患者及其家屬對本研究知情且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兩組學員均由我院同一名老師以小講堂的方式進行授課,授課內容為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教學大綱要求的“腰椎椎管狹窄癥的診斷與治療”。該老師為已經獲取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指導老師資格的高年資主治醫師,具有多年豐富的臨床經驗,以及能夠獨立完成三級手術,能對教學過程中學員提出的相關問題給予準確、通俗的回答,并且可以最新的指南或者文獻舉一反三進行拓展。
1.2.1 實驗組 實驗組學員在傳統教學的基礎上,輔助以3D打印模型加深對腰椎解剖以及神經走行的印象,掌握腰椎椎管狹窄癥的診斷和治療方法。選取典型腰椎椎管狹窄病例,調取腰椎CT 薄層掃描的原始文件,數據錄入Mimics 17.0 軟件(Materialise公司,比利時)進行數字化模型建模,以3D打印設備三維重建影像轉換為三維實體模型,同時使用正常腰椎模型進行對比參考。老師提前將授課內容“腰椎椎管狹窄癥的診斷與治療”告知學員,按要求先課前預習(閱讀相關文獻,對疾病的診斷,治療及進展有初步的認識)。然后規培指導老師根據教學大綱,通過幻燈片講述腰椎椎管狹窄癥的發病原因、起病機制、臨床表現、影像學檢查、診斷及鑒別診斷、治療及預后等重要知識點,在講授幻燈片的過程中老師根據打印出來的脊柱模型講解腰椎的正常和病理解剖、發病機制、影像學特點以及手術治療要點,同時課后將模型交給學員,進一步加深其對腰椎解剖形態知識等內容的理解,便于課后復習。學員分組進行教學查房,對典型患者進行病史采集,體格檢查,影像學資料分析,然后討論治療方案。老師予以點評并做相應演示及總結。最后進行考試。
1.2.2 對照組 對照組學員采取以幻燈片展現理論知識為主進行講解的教學方法。授課前將授課內容“腰椎椎管狹窄癥的診斷與治療”告知學員,按要求進行預習。規培指導老師根據教學大綱,通過幻燈片講述腰椎椎管狹窄癥的發病原因、起病機制、臨床表現、影像學檢查、診斷及鑒別診斷、治療及預后等重要知識點,然后進行教學查房,學員分組對典型患者進行病史采集,體格檢查,影像學資料分析,討論治療方案。老師予以點評并做相應演示及總結。最后進行考試。
1.3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比較兩組學員的理論考試成績和教學總滿意度。①理論考試成績:學習2周后,對兩組學員的教學掌握情況進行摸底考試。理論考試內容包括專業知識考核。專業知識考核為臨床專業理論,考核內容根據大綱而定,包括腰椎管狹窄的定義,發病機制,解剖知識,癥狀及體征,影像學表現,診斷依據,治療方法,研究進展等,滿分100分。②教學總滿意度:采取發放教學滿意度自制量表的方式,量表內容包括學員的個人信息和教學滿意度評測。教學滿意度包括對教學形式及內容的滿意度,總分100分,分為滿意(≥90分)、較滿意(60~89分)、不滿意(≤59分),總滿意度(%)=(滿意+較滿意)人數/總人數×100%。本研究共發放調查問卷32份,回收32份,回收率為100%。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 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Fisher 精確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學員理論考試成績的比較
實驗組學員的理論考試成績為(85.69±8.15)分,高于對照組的(77.06±5.19)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909,P<0.05)。
2.2 兩組學員教學總滿意度的比較
實驗組學員的教學總滿意度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兩組學員教學總滿意度的比較[n(%)]
3 討論
隨著我國醫學教育模式的不斷發展,在全國范圍內已經掀起了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熱潮。從長遠的發展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能夠有效培養一批又一批醫學人才。但是,這同時對規培老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接受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醫師不僅是畢業的醫學生,更多的是在基層醫院已經工作的醫師,這對于培訓的要求不僅僅是理論學習那么簡單,更多的是需要對疾病的診斷及治療有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對解剖要有充分的理解。特別是對脊柱外科而言,掌握脊柱的解剖結構是學習脊柱疾患的基礎,在傳統的臨床教學中,通常是通過解剖圖譜結合影像學檢查來講解。在既往教學過程中,學員普遍反映脊柱結構較為復雜,非常依賴于個人的三維空間想象能力,即使正常的脊柱解剖結構也不容易辨別,對于不熟悉解剖的學員來說,很難理解脊柱疾病的發病原理。學員很難在短時間內掌握復雜的脊柱結構,由于脊柱手術學習曲線較長,所以臨床實際手術中很難上手,這就造成“教師講不透,學生不理解”的被動局面。因此,為了培養出能夠處理復雜臨床工作的優秀醫生,就必須克服這種現狀。
當今醫學教育方法已經從框架性知識結構記憶轉變為基于臨床問題、以學員為中心的教學,教師根據臨床實際提出問題,通過具體病例進行教授。在此過程中,3D打印技術具有獨特的優勢[8]。隨著3D打印技術的成熟和推廣應用,已有大量報道證實了3D打印模型教具在醫學教學領域的有效性。應用3D打印技術制作的高精度脊柱3D打印模型進行教學[9-11],可以給學員提供立體的脊柱結構信息,較傳統的二維影像更直觀、生動有效地將脊柱解剖細節展現在學員面前,幫助學員建立更生動和客觀的三維立體思維,有助于理解椎體、椎間盤和神經結構之間的毗鄰關系,更好地理解疾病的病理基礎。本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員的理論考試成績和教學總滿意度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通過模型學習的學員對疾病的掌握程度更佳。對于解剖知識基礎不強或空間想象力略有欠缺的學員,模型作為教學工具的價值可能更大,有助于他們對脊柱結構和脊柱疾病的理解。個體化的3D打印模型有助于整合脊柱手術、影像和病理解剖等不同學科,成為將抽象理論轉譯成具體形象的關鍵工具[12-13]。
CT 三維重建技術雖然也可以顯示脊柱的立體結構,但這種屏幕上虛擬的三維結構無法通過觸碰形成直接反饋。3D打印模型基于具體的病患制作,可以實現對脊柱骨結構的高度還原,通過模型不僅可以講授疾病的疾病知識,還可以進行模擬操作,在技術探索中發揮更好的作用,有效提高學員的理論及實踐能力[14-15]。另外,解剖標本存在保存困難、長期使用后形態學變化、具有刺激性氣味等缺陷,對于較為少見的脊柱疾病如脊柱重度畸形,無法獲得脊柱標本,3D打印模型則可以克服解剖標本的缺點,并可長期保存及重復利用[16]。同時,其制作相對方便快捷,易于按需要重復制作多個模型以提高教學效率,增加學員的實踐機會。
3D打印技術作為學習教具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7],如3D打印的模型只能重建骨性結構,沒有肌肉、韌帶、神經等軟組織,在打印精度和造價之間很難平衡等。隨著臨床教學需求增加和技術的發展,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本研究由于研究樣本有限,研究不夠全面和深入,研究結論對其他課程的普遍適用性尚待進一步驗證。
綜上所述,采用3D打印技術對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學員進行臨床教學,可以有效提高學員對于臨床疾患的理解和認識,從而提高其理論考試成績,同時能夠激發學員的學習興趣,學員教學滿意度較高,因此具有積極的臨床教學應用和推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