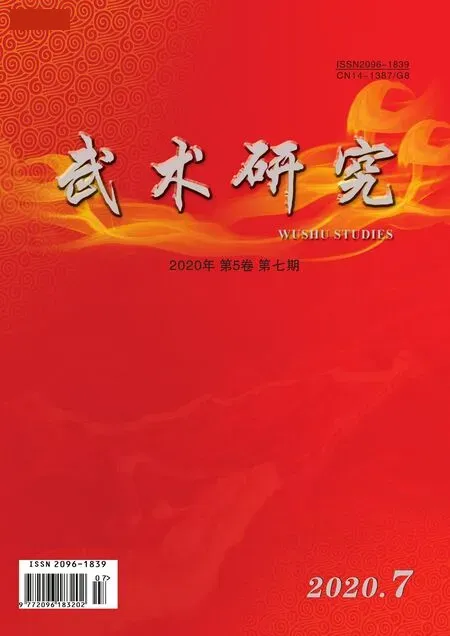師徒制下武德教化的歷程及形成
戎 杰 周吳超
上海體育學院武術學院,上海 200438
人的動物屬性,[1]決定了人自身需要不斷地被完善。“教化”便是對人性本質的完善,如董仲舒所言“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黑格爾也認為“個體的教化乃是實體本身的本質性環節”,[2]因此教化乃是對人生命整體的提升和人性完善的活動。[3]“教化”一詞,其意是在先秦的道德實踐中孕育,其概念在漢代成立并興盛起來,通過經典傳習、禮樂教化、家庭教育等方式來教化民眾,以達到育人成才、端正民風、維護社會秩序。“道德”教化乃是教化活動的中心,是對人的本身進行著引導、規范、改造與提升,[3]重在育人育德,如《漢書·董仲舒傳》中所言“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對人非理性的性情予以修正,以減少“奸”“邪”這樣的品質的出現。
中華武術在優秀的傳統民族文化中孕育而生,其重要價值外顯于攻防技法、內隱于武德修養,其中武德便是“在習武群落中形成的對習武者的行為規范要求”。[4]傳統武術門戶對弟子的武德培養存在著一種道德教化的方式,以儒家文化理論來理解,是在“知”與“行”中對弟子的品性進行著熏陶;以福柯的身體規訓理論來理解,是對弟子的“無處不在的監視”[5]與內在人性品格的規范與改造。因此,武德的教化不僅是對弟子品性的熏陶,還是對行為的規約,使弟子把武德“內化于心,外在于行”,是對弟子心性品格的不斷完善。但是門戶弟子如何得以實現武德教化,弟子把武德“內化于心,外在于行”又是怎樣的形成過程,關于這方面問題雖有學者進行部分探究,但還未建立在師徒傳承制下予以分析。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展現師徒制下武德教化的歷程,及武德教化的形成過程。而現如今,在學生的道德素養培養體系中,武德教育價值也被學者積極認可,但武德教育卻在學校教育體系中逐漸流失,[6]因此,反觀在傳統師徒制下武德教化歷程及其形成,以期待能夠對現代武德教育給予借鑒,以追求武術“德技兼修”完美育人的理想目標。
1 師徒制下的武德教化的歷程
在傳統社會中,建立在非血緣關系中的師徒制,是傳統武術傳承的一個重要途徑,而這種師徒關系則在社會中被“血緣化、倫理化”,形成了“以模擬血緣關系為特征的師徒傳承”。[7]因此,師父作為一個“授業者”,正如“澆花要澆根,教拳要教人”,不僅傳習本門的拳法技理,還承擔著對門徒子弟武德培養的重任。在師徒制下,武德教化貫穿于弟子習武生涯之中,主要包括拜師入門前以“擇徒”為手段的教化、拜師儀式中的教化、拜師入門后以完善弟子為目標的教化。
1.1 拜師入門前:以“擇徒”為手段的教化
在中華武術的發展歷程中,“師徒傳承制”是傳統武術傳承的關鍵所在,也是一個拳種流派、武術門戶發揚廣大的“命門”所在,所以“談玄授道,貴乎擇人”是每個門戶擇徒的文化律令,關乎著門戶拳種輩嗣的繁盛。每個武術門戶都有各自的“門規戒律”,都將其作為擇徒依據,其中道德考察是擇徒的首要標準,如著名的梅花拳傳人楊丙所訂《習武序》中“凡傳教之師斷不可重利輕藝。茍授匪人,敗名傷德,……敬者當如是耳”。[8]以“德”為入門標準,推動了有意拜師之人自為的加強自己道德的修養、塑造自己的心靈、規范自己的行為,以達到步入師門的基本標準。因此在拜師入門前,擇徒以“德”為之標準,存在對“未入門”弟子的道德教化。
“未入門”弟子又有“未授藝”和“已授藝”之分。因此以擇徒為手段的教化,還體現在對“未授藝”之人和“已授藝”之人的教化。一方面,門規之中列有“不傳”是對未授藝之人的教化。例如在《內家拳法》中有“五不可傳:心險者、好斗者、狂酒者……”;清代《楊氏傳鈔太極拳譜》中列有“八不傳五可授”,[9]對不忠、不孝、不恩、不禮的人不予傳授;《昆侖劍箴言》也有明確規定十種不傳之人,其中有“人品不端者不傳”“不忠不孝者不傳”。“不傳”雖然看似是對于品行不端之人的限制和排斥,但作為入門前對拜師之人倫理道德的考察與篩選,[5]在師父傳承拳藝的角度上,是對未入門弟子的一種規訓;在有意拜師之人的角度上,則是對其自身的引導和規范,依據“不傳”的標準,自覺地以“忠、孝、仁、禮、行”等勸化自己的品性、約束自己的行為。所以在授藝之前,以“不傳之人”的規定進行擇徒,對有意入師門之人在忠、孝、仁、行和禮等方面的具有教化之意。
另一方面,門規之中列有“考察”是對已授藝之人的教化。如《少林拳術秘訣》中說:“師之授技,須先考察其人之性情、志氣、品格,經三月之久,始定其收留與否,蓋以師擇人最嚴”,[10]雖然弟子的道德在未授藝之前得到了肯定,允許習練拳藝,但又有“三月之久”的進一步在性情、志氣、品格的考察。之后又有“雖其人之性情良、志氣堅、品格高潔,茍無恒久耐苦之心,專一不紛之概,師必不收矣”[10]對意志品質的考察。不論是“三月之久”的性情、志氣、品格的考察,還是意志品質的考察,以“心性品質”為擇徒標準的確立,成為誠摯的拜師者所認同的價值目標,成為一種所追求的武德范式。因此,真誠拜師之人浸染于以“武德”建立的拜師標準之中,以一種內在的自制和自治,建構自己的品性和克服自己的行為,而獲得武德教化。
1.2 拜師儀式中的教化
涂爾干認為“儀式是集合群體之中產生的行為方式,他們必定要激發、維持或重塑群體中的某些心理狀態”。[11]在儀式中蘊含的文化理念,即通過日常生活中的習俗和樣式,把文化信息融入到人體的活動之中,從而形成對人的精神世界教化的作用。拜師作為“中國藝人求師學藝的一種禮儀”,[12]是弟子“未入門”與“入門”之間的一個身份轉化過程。在武術的拜師儀式中,存在著新進弟子需向師父行“跪拜之禮”、送“拜師貼”“簽約立誓”以及“列族譜”等禮節,身份也逐漸由“為入門”轉向“入門”。拜師儀式中所體現的禮節,以一種約定俗成的程序和行為方式教化新進弟子要尊師敬長、嚴于律己,具有一種潛移默化的規約性,形成弟子立約無畏“身體之苦、心靈之苦”以從師學藝的激勵作用。在這樣的“拜師禮儀”之中,激發、維持以及重塑著拜師的弟子的心性,具有教化之意。
首先,行“跪拜之禮”映現教化之意。中國傳統社會自古對“跪拜”非常重視,有“男兒膝下有黃金”之說,一般用于跪拜父母,表示對父母的敬重之情、順從之意。在拜師儀式之中,弟子需向祖師爺、師爺、師父行“跪拜之禮”,以示自己內心的誠摯的敬意,如菏澤定陶梅花拳拜師詞中“虔誠唯有三叩首”。[13]因此,向師父行“跪拜之禮”,猶如師父身份向父母身份的“嫁接”,把非血緣的師徒關系深化為“似血緣而非血緣”,形成“待師如待父”的武德理念,潛移默化的產生對師父的敬重之情、順從之意。
其次,送“拜師貼”和“簽約立誓”映現教化之意。拜師貼是弟子入門的標志,其內容在不同門戶之見有所差異,但最終是要弟子“遵師命、守師訓、嚴律己”,如梅花拳16代宗師韓其昌先生的“拜師貼”上的誓言:當嚴守門規,謹遵師命,勤奮克己,弘揚風門。今立此誓,永不反悔,如有食言,甘愿依門規受罰。[14]“誓言”是對自己所負義務的約定,其背后是對自身所負義務的認同。[15]因此,送拜師貼及立誓中暗含著弟子對門戶的一種信仰,在拳場、社會空間中形成一種隱形的約束力,對弟子在仁、禮、信、勇方面進行教化,形成尊師敬道、自強不息的心性品格。
再次,“列族譜”映現教化之意。弟子完成拜師之禮節后,其姓名便會被列入族譜之中并獲得具有武德涵義的字輩。如六合門有二十字輩“仁厚尊家法,忠良報國恩,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真”,[16]倫理道德鑲嵌、滲透、內化于每一個族譜的字輩之中,寄寓“道德教化”的思想,具有教化育人之意。
最后,在拜師儀式的場域之中,對在場的已入門弟子也有教化之意。涂爾干認為“儀式是社會群體定期重新鞏固自身的手段”,[11]562“維持或重塑群體中的某些心理狀態”。[11]11在拜師儀式中,進行的“跪拜之禮”、送“拜師貼”“簽約立誓”以及“列族譜”等,可以強化門戶群體的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鞏固對本門戶的認同;對于已入門弟子,可促使以門規戒律再次審視自己的行為,努力做到“德行一致”而獲得教化。
1.3 拜師入門后:以完善弟子為目標的教化
“拜師禮儀”的完成是結束了對弟子入門標準的考察,也形成了對弟子基本品性的肯定和身份的認同,使弟子進入了以模擬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群體,與師父正式確立了師徒關系。師徒關系的確立,即標志著弟子開始承擔在武術門戶中應有的責任與義務,也標志著師父承擔對弟子“授業解惑”的職責,其中不僅包括拳法技理的傳授,還有對弟子道德品質的完善。
在入門之前的擇徒和拜師儀式中雖已對弟子進行武德教化,但弟子還未達到武德之理想的道德意識形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所以在拜師入門后,通過“門規戒律”“習俗禮儀”“經典傳習”“言傳”“身教”等形式,使弟子在“明德”“習德”“執德”的過程中而“立于德”,以促進弟子心性品質的完善。
第一,“明德”之教化。柏拉圖認為人的行為得以善良是建立在知識的引導之下,[17]因此道德的教化必須建立在個體“知”的基礎之上。[3]201武德教化便是通過門戶的門規律令和武術諺語,讓弟子知曉何為“武德”,并以“武德”引導著其自身行為。其一,在中華文化儒、佛、道為主體的倫理體系影響下,不同武術門戶其門規雖存在差異,但基本圍繞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形成的“仁、義、信、勇”等武德思想,形成了弟子應做之條約,如少林寺的“規約十二條”和“十愿”、萇家拳《初學條目》有“學拳宜以德行為先,凡事恭敬謙遜,不與人爭,方是正人君子”;[18]弟子勿做之條約,如少林寺“十不許”、受佛教“五戒律”影響而產生的武僧“十禁約”、六合拳的“三慎五戒”。通過規定“應做之事”和“勿做之事”,讓弟子知曉武德有“尊師”“孝悌”“保國”“仗義”“勇為”等內容,形成對武德內容的基本認知。其二,在武術諺語中滲透著武德規范,如“三分保平安”“比武走手,點到為止”“拳不傷人,械不取命”等,讓弟子明白行走江湖禮讓三分、武藝切磋點到為止、習武防身不傷人等武德理念,展現習武之人的心性修養和道德理想的追求。所以,門規律令和諺語這些外在的規約,以社會之中普遍認同的道德理念而建構一種價值導向,在弟子“明德”的過程中,形成對武德內容的認知與認同,自為的產生一種道德標準,以涵養心性、規約行為進而產生教化之意。
第二,“習德”之教化。“習德”,即通過不同途徑把武德內化于心。其一,通過懲戒使弟子把武德規范牢記于心。在少林寺的門徒規條中,讓弟子對“規約十二條”熟記于心,以免責罰;對“十不許”勿犯,不然遭殺身之報;對“十愿”跪神位、師傅面前口讀,并發誓口是心非,會不得好死。既以責罰為懲戒的手段,實施行為的規訓,如“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又出于傳統社會對“天命”的信仰,促使弟子虔誠地把武德內化于心。其二,通過拳法的習練把武德內化于心。“拳雖小技,其道存焉”,“道”不僅包含拳法的技法理念,還有武德的存在,如拳有“八打八不打”“四打四不打”。[19]“八不打”“四不打”是對人的致命之處主動規避,在武藝切磋中達到以武會友、交流情感,即使偶遇險情置身于危險之中,也只為達到防身自衛之效,而非殺人。因此,把友愛、仁義的武德思想貫穿于拳法技理之中,把厚道的人道主義精神融入弟子身體活動之中,讓弟子在修煉后內化成為一種高尚品格。其三,通過師父口授把武德內化于心。師父作為“傳道授業解惑”者,十分重視武德品格的培養,據李仲軒口述“唐師教育我:‘別人的好,一輩子不忘;別人的不是,轉頭就忘’”。[20]“知恩圖報,為人大度”是唐師教育李仲軒的武德思想,李仲軒內化并形成了“年輕人,心胸要大點,不要做‘與惡狗爭食’的事”[20]的思想,轉化為一種待人處事之大度涵養。
第三,“執德”之教化。“執德”是道德教化所追求的結果。通過“執德”能把抽象的意識觀念、道德價值映現出來,即“內化于心”的武德思想“外在于行”,外顯于言行舉止之中,使弟子“可觀、可感、可知”,[21]潛移默化的受到道德內容的灌注而獲得教化,如老子所言“行不言之教”。一方面,弟子“以身體道”展現教化之意。在儒家文化的渲染下,以禮教化形成了“重禮受禮”的社會風俗。武術門戶同樣如此,如李仲軒口述“形意門規矩大,民國社會上廢除跪拜禮,但形意門一直是見了長輩要磕頭,說話要帶稱呼”,[20]256這里的“規矩”便是行為禮節,含有尊師敬道之意,是武術門戶對弟子內心武德教化而轉化為行為的結果,如費孝通認為“禮并不是靠外在的權利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的個人敬畏之感”。[22]“執德”是以身體活動展現的“內在品質”與“外在行為”的結合,如武術的“抱拳禮”,在尊敬師長的行為表現中,凝結著一種的尊師重道的氛圍。另外還有拜場地禮、器械禮等,使門內弟子既在師門長輩的“執德”行為氛圍中感化,又在自身“體道”中浸染。但是行為若有背禮節、違反門規,并因此受到懲戒,以儆效尤,對其他弟子也具有教化之意。唐維祿一弟子,在唐師教其習拳時,對唐師突然襲擊,爾后被逐出師門;另一弟子,一次心生惱怒之時,將其兒子打死,而被逐出師門。[20]186唐師兩位弟子,一是無尊敬之心、一是無仁愛之心,受“逐出師門”的懲戒,對門內其他弟子則有警醒作用,轉化為自我行為的約束。另一方面,師父“以身示范”展現教化之意。師者不僅在“傳道授業”中教授弟子技藝,也能以自身學識、道德和行為在以身示范中對弟子熏染,如《四書訓義》中“師弟子者以道相交而為人倫。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在武術中有“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之說,習練武術本是就是體驗“身體之苦”,便有張文廣對弟子說“咱們一起練好不好”、孫祿堂以身示范一口氣翻300個跟頭,以讓弟子克服身體疲勞,塑造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意志品質。另外還有尚云祥手把手保護學生以體悟技擊動作,讓弟子形成師門之內相互禮愛、互幫互助;在民族危亡之時,李存義率弟子與八國聯軍對決,讓弟子形成保家衛國之情懷。
2 武德教化之形成過程
“教化”一詞中西方雖存在差異,但“教化”都是關涉到人的本質的獲得。如理查德·羅蒂認為教化是推動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轉變,[23]伽達默爾認為教化最終是為了心性的“保持”。[24]黑格爾則認為人類所創造的政教倫理制度在社會活動中具有普遍性本質,而教化便是在政教倫理制度下,把人存在的盲目沖動狀態的非理性狀態上升至理性狀態。[25]換句話說,通過異化自身本質存在的精神活動(如暴力、欲望),而獲得普遍性的理智素質,達到如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狀態。因此,把“轉變”“保持”“普遍性”相結合,我們便可更加全面地理解武德教化所形成的過程,即武德教化是以武德為標準,使弟子獲得內化于心的“轉變”,并達到外在于行的“保持”,進而達到心性品質的“普遍化”。
2.1 內化于心的“轉變”
教化過程中人所形成的心性品性“轉變”,既是《五行篇》中的“形于內”,也是理查德·羅蒂所言“脫離舊我,成為新人”的過程。在武德教化三個歷程中——拜師入門前、拜師儀式、拜師入門之后,通過不同的方式把武德思想融入到弟子整個習武生涯之中,對弟子不完善的心性品質進行引導和熏陶,以內化武德的核心價值之“仁”、基本要求之“義”、處世原則之“信”等,[26]使弟子由非理性向理性、他律向自律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中塑造著弟子內心品格和意志。
2.2 外在于行的“保持”
教化的形成“必筑基于內而發行于外”,[27]即在內心獲得轉變后,并自然發之于行為,才能說明教化的內容得以保持,教化才具有實意。道德教化的結果并非是孤立于內在性,而要見諸于實體,有一種“肉身化”的體現,正如《孟子·盡心上》提出“踐行”之說:“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踐行”。“踐形”即“外在于行”,是品性由內而外的展現,付諸于實踐之中。同樣武德教化也是如此,即在武德思想“內化于心”,使心性品質獲得完善的基礎上,要長久地呈現于行為之中。武德教化的保持則體現在“抱拳禮、器械禮、場地禮”“對父母之孝、子之仁愛”“點到為止、不打致命之處”等行為禮節之中,分別在拳場、家庭、社會不同的場域中展現武德風采,武德教化才得以形成并實現弟子心性品質的不斷完善。
2.3 心性品質的“普遍化”
以儒家、道家、佛家文化為主導,中華傳統道德文化不斷地被創造和選擇,普遍的存在于“禮樂文明”之中,如喪、祭、昏、冠、喜、射等,滲透在社會各個階層成為普泛的生活樣式。武德既來自傳統社會的普遍倫理觀念,又是對這一普遍倫理觀念的擇取和凝練,形成了“仁、義、信、勇、禮”等內容,并融入到“門規戒律”“行為禮節”“拳法理念”“武術諺語”等之中,成為廣大習武群體中所認同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理念。在師徒傳承制下,不論是用以擇徒為目標的教化,還是對弟子品性的繼續完善的教化,把普遍性的武德理念滲透到門徒子弟的日常行為之中,潛移默化的規約和熏染著弟子的思想,使弟子獲得內化于心的“轉變”,并達到外在于行的“保持”,最終拋棄自身個別未完善的沖動狀態向普遍性心性品質的提升。
3 結語
自先秦以來,中國傳統社會就有道德教化的思想。從社會精英的角度,道德教化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對百姓生活移風易俗,在有形無形中建構著普遍的社會道德理念,形成良好的社會公約。師徒制下,武德教化與傳統社會道德教化存在緊密的聯系,在“拜師入門前、拜師儀式、拜師入門之后”三個階段中,以門規戒律、跪拜之禮、拳法技理、以身示范等不同的方式對弟子進行著武德教化,把在社會中具有普遍性質的武德理念內化于弟子精神品質之中并展現于行為之中,使弟子心性品質達到普遍性的狀態。所以,武德教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培養武術門戶需要之人——不僅是傳承拳種技法之人,更是具有完善的武德修養之人。
如今,道德素養作為學生這一“時代新人”的核心素養的關鍵一環,不可缺失,而武德教育對于學生道德培養具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因此,對待傳統師徒制下的武德教化,我們應挖掘其精華,擇取其有實踐意義的教化方式,如“傳習經典”“以身體道”“以身示范”“行為禮節”等方法,融入到現代武德教育之中,既能豐富武術教學中的文化趣味性,又能促使學生把武德“內化于心,外在于行”,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獲得道德素養的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