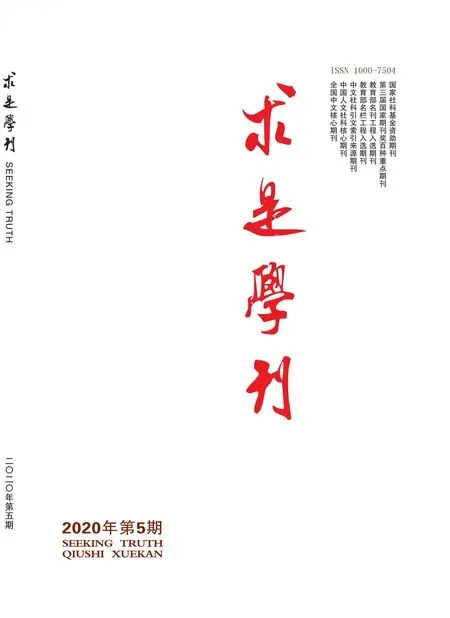作為物質型人格權之“基因權”的理論證立與法律保護
郭少飛
生物科技突飛猛進,推動基因分子水平的人體研究利用快速發展,人體生理結構及運行機理逐步得以揭示。基因技術對人類生命的操控愈加深入純熟,如2000 年美國誕生全球首個“救命寶寶”,①See Susan M.Wolf et al.,“Using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to Create a Stem Cell Donor:Issues,Guidelines &Limits”,in Journal of Law,Medicine and Ethics,2003,Vol.31,No.3,pp.327-335.2016年4月世界首例“三親嬰兒”出生,2018年11月我國誕生世界首位“基因編輯嬰兒”,引發巨大的倫理爭議。在基因映射下,作為生命高階形式的人類與其他生命形態同質化,人類生命的神秘性、崇高性及魅人光輝正在消解,“人的自然體在迄今無法想象的程度上變成了可以通過技術加以支配的東西”。②庫爾特.拜爾茨:《基因倫理學——人的繁殖技術化帶來的問題》,馬懷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288頁。我們需要構造基因權利制度,重塑其倫理性,發現并強化其人格價值。學界主張的人類基因權利保護進路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傳統身體權、健康權保護基因,由于局限明顯,僅為少數學者主張;二是,新設權利,單獨保護基因,為眾多學者所采,亦為本文贊同。后者存在“基因人格權”“基因財產權”及混合權利說,而人格權又分出“基因隱私權”“基因信息權”等。現有基因權利說概念用語蕪雜,理論體系不一,尤其對作為物質的基因保護不周。對此,本文主張創設以物態基因為客體的新型物質型人格權“基因權”,詳論權利確立的正當性基礎,并結合我國《民法典》基因法律制度,闡述后民法典時代“基因權”法律保護的理念及進路。
一、“基因權”的提出及理據
“基因權”的提出奠基于對基因物質性的科學認知,但是否足以作為獨立單一的權利存在,尚須從科技、倫理、制度等多個層面予以論證。
(一)基于物態基因之“基因權”提出
基因作為一種物質,不僅分布在人體及與人體分離的組織器官中,而且存在于復制的人體細胞中。由于科技發展,物態基因已經在分子層面自人體析出,自然人對其基因的占有支配已非現有權利可以保障,需要一種以基因為客體的新型權利。
在生物意義上,基因(gene)是遺傳物質的基本單位,通常由編碼蛋白質或核糖核酸(RNA)鏈的脫氧核糖核酸(DNA)片段組成。但特殊情況下,基因可能以RNA 形式存在。基因組(genome)是生物體攜帶的全套遺傳信息,包含蛋白質編碼基因、非蛋白質編碼基因、基因調節區域及功能未知的DNA 序列。①參見悉達多·穆克吉:《基因傳:眾生之源》,馬向濤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42—544頁。基因主要分布于細胞核與線粒體上,呈線性排列。基因可經由精子、卵子傳遞給胚胎,然后由胚胎進入生物體的每個細胞。人類基因組共編碼約20 687 個基因。編碼基因的序列在基因組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基因組序列的98%是由大量散布在基因之間或基因內部的DNA 片段組成,它們不編碼RNA或蛋白質。
基因是“承載著肌體的信息、生命的藍圖、運行程序的生命終極因子”。②張春美:《DNA的倫理地位》,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57頁。人類基因與個人生理發育、心理健康、生命狀態關系密切。基因變異可能導致生長遲緩,器官組織不健全,健康狀況惡化,甚至死亡。基因與人的生命進程有關,但并非生命本身;基因關系人的生長發育,與人肉身的完整度相關,但身體無法涵蓋基因,只是基因表達的結果之一;基因影響身體器官的功能發揮,致病基因或基因變異會導致不健康。生命、身體、健康受基因形塑,但無法等同。尤其與人體脫離的組織器官或人體生成物中的基因,非屬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客體范疇。
總之,基因作為一種化學物質,關乎人的生老病死、人的身心狀態,意義顯著;且已非人體可涵蓋,成為一種新型獨立的主體利益,有必要從基本的物質層面對其賦權保護。仿照民事權利“客體+權利”的慣常命名方式,應稱為“基因權”,即權利人直接支配基因,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乃絕對權的一種。
(二)“基因權”提出的正當性基礎
承認“基因權”不僅在于基因生物性或物質性,還在于基因對人的價值與意義重大。“基因權”確立具有顯著的科技、倫理、制度等綜合基礎,作為獨立權利條件成熟。
其一,基因技術深度進階,基因物質需要單獨權利保護。基因技術令人類能夠從分子水平認知自身生命現象。通過基因技術,人類開始掌握本體命運,不再完全受制于生物人生命規律。至今,基因篩查、檢測、診斷、治療等已廣泛運用;人類基因組測序完成后,個人基因測序簡便易行,成本大幅下降;基因優化、增強、編輯、克隆等技術逐漸成熟,雖然存在潛在的倫理風險、社會風險,一旦法令準許,大規模應用可期。無論如何,當下深度進階之基因技術對個人、族群乃至整個人類產生巨大影響,而所有基因技術皆系作用于基因之手段方法,須取得、占有、利用基因。為此,就基因本體,應取得有關主體的同意或授權。當發生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時,有關主體享有法定權利防御或主張侵權救濟。這些均需賦權于個人,承認個人占有支配其基因的權利。獨立的“基因權”能夠充分發揮上述功用,實現良好保護效果。
其二,基因獲得獨立權利保障,有利于強化人類尊嚴保護。技術理性的張揚、現代性的深化及結構化,使得人的客體化趨勢加劇。基因技術在分子層級解構人,預測人,試圖把人的生理心理狀況與基因勾連起來,①參見威廉·賴特:《基因的力量:人是天生的還是造就的》,郭本禹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頁。歸結為基因,導致身心俱在之人降解為物質之人。在社會認知層面,基因與特定的社會文化密切相關,人們普遍認為“基因關乎人類自身,與個人的自我意識深度關聯”,②Sonia M.Suter,“The Allure and Peril of Genetics Exceptionalism:Do We Need Special Genetics Legislation?”in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2001,Vol.79,p.669.相信基因決定人的樣態、特征,能夠解釋人的差異。這也帶來了基因歧視。而人們追求以基因技術設計、改造、轉換生命。生命不再神圣,只是不同的基因組合,可人為操控。人物質化、原子化,引發人的異化,人的尊嚴自由不斷消解。對此,應認識到,基因為生命提供了自然基礎,蘊含生命潛能,道德意義顯著,應賦予道德權利。在法學視閾中,面對人被基因技術透析之境地,考量基因盜取或掠奪、基因標簽、基因歧視、基因商業利用等現狀,應將道德權利轉化為法律權利,明晰個人在基因分子層級自我決定、自我控制的地位,賦予個人對基因本體的權利,即“基因權”,從而凸顯基因的法律地位、之于個人的本體意義,強化基因之上人類尊嚴保護。
其三,國際宣言及域外立法實踐為承認“基因權”提供制度鏡鑒。1997 年《世界人類基因與人權宣言》第1章“人的尊嚴與人類基因組”第2條規定,(a)每個人都有權使其尊嚴和權利受到尊重,不管其具有什么樣的遺傳特征。(b)這種尊嚴要求不能把個人簡單地歸結為其遺傳特征,并要求尊重其獨一無二的特點和多樣性。這表明基因之上存在人格利益,應受權利保障。第2 章“有關人員的權利”第5 條規定,(b)在各種情況下,均應得到有關人員的事先、自愿和明確同意。(c)每個人均有權決定是否要知道一項遺傳學檢查的結果及其影響,這種權利應受到尊重。《法國民法典》③《法國民法典》,羅潔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頁。1994 年新訂第三章“對人之特征的遺傳學研究以及通過遺傳特征對人進行鑒別”第16-10條規定,對人之特征進行遺傳學研究,僅限于醫療與科學研究之目的。在實施此種研究之前,應當征得當事人的同意。第16-11條規定通過遺傳特征對人進行鑒別,明確“鑒別之前,應征得當事人的同意”。上述國際宣言及立法均要求,對基因進行研究、鑒別前應取得當事人同意,實則承認個人的基因權利。基因研究、鑒別皆需獲得基因,當事人同意至少包含提取占有基因之許可,此乃個人支配控制其基因的權利的彰顯,即本文主張的“基因權”。國際社會及有關國家立法表明,“基因權”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間。
綜上,基因技術蓬勃發展,在基因分子層面透析利用人,超越過往以器官組織細胞為對象的超分子認知范疇。作為人的生物身份證,基因可揭示個人生物特征,在社會系統中頗具獨特的社會文化意涵,關乎人的尊嚴自由,利害關系重大。當下,基因已然成為一種新型主體利益,當配之以獨立的“基因權”,保障權利人對其基因的自我控制、自主支配。
二、“基因權”作為物質型人格權的學理分析
基因具有物質與信息雙重屬性,“基因權”指向物質性基因,以物態基因為客體。現有研究就基因權利數量、性質爭議較大,存在明顯不足,缺乏對基因物質性這一根本屬性的聚焦。本文立足物態基因,基于權利特性及實證法,厘定“基因權”性質。
(一)現有基因權利說難敷物態基因保護之需
1.現有基因權利主要學說
就基因權利種類、屬性等,存在各種學說。按所主張的基因權利數量及權利之間是否彼此獨立,分為單一權利說、二元權利說與權利束說;按權利性質,可概括為財產權、人格權及混合權利說。
(1)單一權利說
該說認為,基因之上僅存在一元權利,按單一權利屬性,分為人格權說與財產權說。前者主張,人類基因是一種信息或隱私,應以基因隱私權進行保護。①See Guido Pennings,“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One’s Genetic Origins”,in Medicine and Law,2001,Vol.20,pp.1-15;Graeme Laurie, Genetic Privacy:A Challenge to Medico-Legal Nor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42-50.還有大量英文文獻可參考。美國大多數州制定了個人基因隱私保護法。聯邦層面,2008 年頒行《基因信息反歧視法》。而承認基因財產權的趨勢漸強。有些州如馬薩諸塞、南達科他、得克薩斯、阿拉巴馬,立法議案要求把基因信息、DNA 或DNA 樣本等界定為專有財產(exclusive property)或獨占財產(sole property),賦予財產權。實踐中,個人基因財產權為基因公司承認,在服務條款或聲明中包含“財產權放棄”或“DNA 和DNA 數據所有權”之類的表述。學界也有基因財產權專論。②See J.W.Harris,Property Problems:From Genes to Pension Fund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td.,1997,pp.92-114;Jessica L.Roberts,“Progressive Genetic Ownership”,in Notre Dame Law Review,2018,Vol.93,p.3.
(2)二元權利說
該說主張,基因之上并存兩種單一權利,即基因人格權與基因財產權。我國有學者論道,基因上人格法益與財產法益交融共存,應區分基因財產權和基因人格權,前者包括承認基因資料提供者捐贈、轉讓基因和獲取相關回報的權利,知情同意、利益分享等權能。③參見劉紅臻:《人體基因財產權研究——“人格性財產權”的證成與施用》,《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 年第2 期,第22—23 頁。基于兩種權利進路,有學者認為,“人對其基因享有人格權,包括對尚在人體內的基因的身體權、對與人體脫離的基因的自己決定權及對基因信息的隱私權。其次,人對其基因享有財產權,包括對其基因物質的所有權及決定對基因的研究與商業化運用并獲得財產利益的權利”。④李燕:《論人對其基因的民事權利》,《東岳論叢》2008年第4期,第171頁。還有學者主張,基因無形財產權加上隱私權,賦予個人自主控制領域,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合理排除政府或社會對私人空間的侵入。⑤See Adam D.Moore,“Owning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Gene Enhancement Techniques:Why Privacy and Property Rights May Undermine Social Control of The Human Genome”,in Bioethics,2000,Vol.14,p.2.
(3)權利束說
該說認為,基因權不是單一權利,而是多項權利的集合,包含各種性質的權利。這種觀點在我國較為普遍。顏厥安教授認為,人對于他的基因擁有:基因隱私權或基因資訊自主權、基因人格權(知情權、自主決定權)、基因財產權一(與身體分離之基因物質的所有權)、基因財產權二(與基因專利相關的財產權利)、基因保育責任。⑥參見顏厥安:《鼠肝與蟲臂的管制——法理學與生命倫理探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34—135頁。張小羅教授主張,“基因權利是一束權利”,“是一項綜合性權利,主要包括基因平等權、基因隱私權、基因人格權、基因財產權、基因知情權等內容”。⑦張小羅:《憲法上的基因權利及其保護機制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0—71頁。王康教授認為,在私法意義上,“基因權是指自然人基于自己的特定基因而享有的人格權利”,包含基因平等權、基因自主權、基因隱私權、基因公開權等子權利。它是一個積極的、新生的、兼顧財產性的具體人格權。⑧參見王康:《基因權的私法規范》,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32—133、136—138頁。
2.物態基因視域下基因權利定性檢討
自作為物質的基因本體角度,現有基因權利說對基因的定位模糊,在物質與信息之間搖擺,導致定性失準,與物態基因保護不適配,與我國主流理論不符,學說自身的理論自洽性亦不足。
其一,基因財產權應當否棄。該說在英美法系國家較為流行,亦符合其法治傳統。但與我國遵循的大陸法系人格權理論存在違和之處。基因首先是人體組成部分,蘊含生命潛能,標識個人身份,關乎人的尊嚴。基因本體直接作為財產,乃人的客體化商品化,有損人格尊嚴,不合我國主流理論。當然,基因之上附有財產利益,但依據我國《民法典》以人格權一并保護人格財產利益的規范方式,并不承認獨立的人格財產權。①參見郭少飛:《新型人格財產權確立及制度構造》,《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48—49頁。基于此,物態基因尤其體內基因在我國不宜界定為財產,有關權利亦非財產權。
其二,基因隱私權或信息權偏重基因信息保護。隱私權涉及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信息權乃個人對其信息享有的自主控制決定的權利。基因隱私權或信息權,指向基因的信息形態,即通過一定技術手段對個人生物樣本檢測分析獲取的,與該個人先天或后天的遺傳特征有關的信息。基因信息來自物態基因,是后者的信息表達。基因隱私權或信息權無法涵蓋、也無法周全保護作為物質的基因本體,如第三人取得基因(材料),但不提取基因信息。何況,基因信息提取后,可與基因本體分離,自由流動。此種分離性決定了基因精神人格權難以一體保護物態基因與基因信息。
其三,混合權利類型混雜,缺乏統一理論基礎。權利束說承認基因多元利益,試圖以多元屬性權利構成的一束權利保護基因,但權利范疇不清,各種主張差異較大;權利關系混亂,非同一層級、上下位權利并列,如基因隱私權與基因人格權;未能建構翔實的基因權利體系。而如基因平等權,到底是私法權利或憲法權利,值得斟酌。
(二)“基因權”應定性為物質型人格權
基因是個人生物身份證,能夠用于識別個體身份,預測身心健康狀況,揭示家族、種族等社會關系,蘊含生命潛能,與人的尊嚴關系重大。“基因權”無疑應歸入人格權,并因符合物質型人格權的本質特性,且具有法律基礎,應定性為物質型人格權。
1.物質型人格權的本質特性
物質型人格權的概念用語有別,如物質性人格權、人身的人格權、身體的人格權,但內涵基本一致。主流理論認為,物質型人格權與精神的人格權相對而在,“是自然人對于物質性人格要素的不可轉讓的支配權”,②張俊浩:《民法學原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2頁。“是指對具有人的身體屬性的生命、身體、健康等擁有的權利”,③五十嵐清:《人格權法》,鈴木賢、葛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頁。旨在保護存在于人身的人格法益。④參見王澤鑒:《人格權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9頁。就物質性人格權要素的范圍,張俊浩教授認為包括生命、身體、健康、勞動能力;王澤鑒教授主張包含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及貞操。綜合而言,生命、身體、健康作為物質性人格要素乃共識。
物質型人格權與精神的人格權類型劃分奠基于人作為物質實體與精神存在的雙重屬性。人當然并非純粹的肉身之物,還具有心靈、意志、意向性等精神能力及活動,應當說是“身”與“心”、“肉”與“靈”的統合。物質型人格權指向人的物質屬性,精神的人格權關涉人的精神屬性。人活的狀態,肉體的完整度,人生命過程功能的正常健全,均系人身物質層面的重大人格利益,關系人的生存、尊嚴,在法制史上也最先得到承認與保護。而精神的人格權注重保護人的心理利益、精神利益,“是人的正當心理利益在法律上的定型化”。⑤張俊浩:《民法學原理》,第146頁。
與精神的人格權相較,物質型人格權特性鮮明。其一,客體的物質性。物質型人格權以物質性人格要素為對象,通說包括生命、身體、健康。以實體論,即以人體或身體為基礎的物質性存在。此類實在具有客觀性,不以人的意志或認知為轉移。無論權利人或他人的認識能力如何,其生命、身體、健康等物質性人格要素皆在。而精神的人格權客體乃心理性或精神性要素,如名譽、榮譽、隱私等,均與人的精神心理活動直接相關,具有典型的主觀性。其二,與身體直接關聯性。物質型人格權以身體或人身為載體。生命是人身活的狀態,身體指向肉體的完整,健康注重人體功能健全正常,無不與身體直接密切相關。這也是被稱為人身的或身體的人格權的重要原因。精神的人格權也與身體有關,畢竟心理精神活動基于人體及器官,但精神的人格權主要涉及人體精神活動而生的精神性人格利益,而不直接指向精神活動所依賴的物質條件,即人體及組織器官,它與身體僅有間接相關性。其三,侵害后果的客觀性。物質型人格權遭受侵害,在客觀世界中表現為物質變動,人們能夠通過技術手段測量或一般經驗觀察獲悉。如權利人死亡、身體完整性被破壞等,皆可在客觀意義上呈現與感知。而精神的人格權侵權后果主觀性強,缺少客觀化計量方法,標準富有彈性,當事人易生爭端。
2.“基因權”契合物質型人格權
“基因權”是權利人支配控制其基因本體的權利,符合物質型人格權本質特性,應定性為物質型人格權。這在我國也有相應的實證法基礎。
(1)“基因權”符合物質型人格權特性
第一,就客體物質性而言,基因是人體中的DNA 分子片段、一種化學物質,其物質屬性毋庸置疑。基因作為實在物,存續于客觀世界中。雖然在“心”“靈”層面,基因與個人心靈塑造,與個人智力、性格、精神狀況、行為傾向等有一定聯系,但深受教育、文化、環境等諸多外在因素的影響。應當說,基因功能主要表現為遺傳特征的表達,控制個體性狀,與人身、人體等物質性人格要素關聯更加直接緊密,與人的生命身體健康具有重大利害關系。“基因權”客體物態基因具有顯著的客觀性、物質性。
第二,“基因權”與人體直接密切相關。物態基因通常分布于人體各個角落,也蘊含在與人體分離的組織、器官或細胞中,如脫落的人體毛發、皮膚碎屑、指甲。基因此種遍在性特點雖然不同于完全以人體為邊界的傳統物質型人格權,但與人體分離部分仍然是人體的生成物,與人體關系密切。“基因權”旨在分子水平保護人,但基因與人體的分離性高于超分子的器官、組織,為周全保護考量,權利客體勢必擴展到與人體分離的物質中的基因。無論處于體內抑或體外,物態基因來自人體,“基因權”與身體直接關聯。
第三,“基因權”遭受侵害,主要表現為未經權利人同意非法取得、利用權利人基因等。從后果狀態看,加害人占有控制權利人的物態基因,顯然可以通過技術方式予以檢測,客觀化地確定受侵害物態基因的種類、范圍、用途等。
(2)《民法典》為“基因權”作為物質型人格權奠定法律基礎
《民法典》人格權編第2章“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中,第1006條規定可無償捐贈人體細胞、人體組織、人體器官等;第1007條規定禁止買賣。禁止人體細胞買賣在于細胞中的基因,可用于器官再生、組織再造甚至人類克隆等,關涉人格尊嚴,倫理風險、社會風險非常高。第1008條規定為研制新藥、醫療器械或者發展新的預防和治療方法,開展人體試驗的規則。其中,必須經受試者或其監護人書面同意。該條也指向基因藥物、基因療法以及人體基因試驗。在此意義上,為試驗而收集利用受試者基因,當經其同意。第1009條規定,從事與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有關的醫學和科研活動,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不得危害人體健康,不得違背倫理道德,不得損害公共利益。該條直接規定人體基因,未能言明基因所屬主體的權利,但從守法要求、禁止性規定分析,取得基因主體同意乃基本前提。
《民法典》雖未明確規定自然人對基因本體的權利,實則承認主體對其基因享有某種權利,否則自然人如何處分(捐贈)其基因,基因的取得占有利用也不必其同意授權。可以說,《民法典》為人體基因保護留下了巨大的制度空間。再者,四個法條處于“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這三項典型物質型人格權的規范部分,依體系解釋方法,人體基因規定在以物質性人格要素為調整對象的規范中,至少表明人體基因的物質性得到立法者認可,進而經法典解釋,基于上述條文,可構造出以物態基因為客體的“基因權”。
概言之,“基因權”符合物質型人格權的本質特性。客體物態基因具有物質性,關乎人的尊嚴,乃物質性人格要素;指向處于人體內外的基因,與身體直接關聯;損害后果印刻于客觀世界,可以一定方法測量。而《民法典》物質型人格權條文,直接或間接指涉人體基因,明確承認基因的物質性,隱含自然人基因權利,為解釋明定“基因權”留有制度空間。
三、后民法典時代“基因權”的法律保護
《民法典》基因立法具有鮮明的制度特色,但也存在籠統間接、過于原則、體系化不足等問題,亟待補充完善。后民法典時代,“基因權”私法保護需要法典解釋與特別立法并重,秉持特定理念,遵循相應進路,周全保護物態基因。
(一)《民法典》基因制度特色及不足
《民法典》作為民事基本法,以少量條文對人體基因做出原則規定,系我國首度基因民事基本立法,具有顯著的制度特色。其一,較之前草案視野限于人體細胞、人體組織、人體器官等,《民法典》更加貼近基因技術前沿及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感更強。其二,統合法律與倫理。包括基因在內的人體不得買賣的禁令深植道德倫理,關系人性尊嚴。人體試驗需同時由主管部門批準與倫理委員會同意,共同發揮法律與倫理作用。與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有關的醫學或科研活動,既要守法,也要遵守道德倫理。其三,發揮私法公法協同作用。轉介條款如第1009 條“應當依法經相關主管部門批準”,“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指向公法規范及特別法。在人體基因等領域,共時涉及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必將是私法公法協同調整的規范格局。
此外,基因制度尚有明顯缺憾。其一,因循固有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框架,不足以應對基因社會實踐發展。如上文所述,物態基因權利,非現有物質型人格權所能涵蓋。至于第1009 條,與基因直接相關,卻語焉不詳,完全交由公法及特別法調整,而未言明私權基礎,難謂完滿。其二,制度體系不周延。人體細胞、人體組織、人體器官,可捐贈,不許買賣,但未解決與身體分離后,在基因層面被他人利用侵權問題。如術后拋棄之人體分離物,無身體權、健康權適用,亦無物權適用,個人沒有提起侵權之訴的有名基因權利基礎。若純粹科研之用,難言違反倫理道德,極易陷入爭議。其三,未能直面基因技術挑戰。基因之上人性尊嚴、物質性人格利益需周全保護。臨床試驗局限于人體試驗,而人體分離部分、人體基因試驗等,涉及諸多法律及倫理問題,亦需規制。《民法典》未能直接明定自然人基因權利,面對基因技術對人的沖擊,回應力度不夠。
《民法典》剛剛頒行,作為民事基本法須保持權威性及穩定性,短期內不會修改,“基因權”目前難以在法典中具名化。后民法典時代,人格權編成為現實后,應從立法論邁向解釋論,①參見姚輝:《當理想照進現實:從立法論邁向解釋論》,《清華法學》2020年第3期,第46頁。一方面可通過法律解釋,構造“基因權”;另一方面亟需特別立法,在《民法典》統領下,遵循特定理念,建構基因權利及保護體系。
(二)當下“基因權”法律保護理念
迄今,基因技術迅猛前進,產業不斷拓展,倫理風險日益劇增,社會影響巨大,紛爭激烈。“基因權”法律保護,必須立足基因技術現狀,直面復雜的社會實踐,發揮多種主體、多元力量、多樣規范作用,此需秉持如下理念。
第一,自由與管制并重。“基因權”乃私權,在法律保護時仍應遵循權利本位,尊重權利人的意思自治及行為自由。但同時,“基因權”涉及家族成員的合法權益,關系特定群體利益,甚至對人類基因資源亦有重大影響。為保護他人權益、公共利益,預防各類風險,平衡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社會安全的關系,須與賦予“基因權”同步,實施相較于傳統私權更加嚴格的管制,約束權利人的自治范圍,限定行為類型,特別要嚴格管理“基因權”許可利用行為或生命潛能開發行為,“堅持在全面立法模式下的嚴格規制、法定許可的立場,保持行業主管和審查機構的中立性,提高機構倫理委員會的獨立性,實行個案審批制度”。①王康:《人類基因編輯實驗的法律規制——兼論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的法律議題》,《東方法學》2019 年第1 期,第19頁。
第二,倫理與法律共治。基因技術確能助益人類,但也蘊含巨大風險,面臨深重的倫理困境。現行技術已經開始超越人類的預測能力,很難確切認識其未來社會影響及后果,不確定性加劇。我們需要新的技術倫理保障技術不會偏離為人類服務之根旨;須以法律來規范技術開發運用,防范不當后果。這樣“一種旨在控制不可預測的后果的、預防性的倫理與法律”,“必須偕行:法律提供控制與遏制的主要客觀手段,而倫理則提供這樣做的內在道德理由”。②何懷宏:《構建一種預防性的倫理與法律:后果控制與動機遏制》,《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2期,第11頁。此種倫理與法律并置的規范格局在基因領域已然生成。國際社會基本達成基因技術倫理共識與規則;許多國家立法規制基因技術或保護基因權利。而倫理在引導基因技術發展過程中必然具有不確定性與軟弱性,單純依賴倫理無法確保技術的安全性,無法確保該技術不會對人類的生命健康與生命尊嚴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③參見劉長秋:《“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與生命法學之證成》,《東方法學》2019年第1期,第26頁。“基因權”倫理與法律共治,根植于倫理,重在明晰基因權利的法律規則,發揮法律調整作用。
第三,私法規制應審慎必要。面對蓬勃發展、尚不穩定、風險未知的基因技術,保持審慎的態度并不為過。立法者非全知全能,其理性也有限。故“基因權”法律保護,除了明確基因權屬規則外,基因積極利用尤其生命潛能開發高度依賴基因技術,倫理及安全風險高,應當更加審慎,既不能完全由當事人自治,也不宜過于嚴格,影響技術進步、產業發展。為此,在私法領域,首先在于建構完整的“基因權”制度,為物態基因提供系統的私權保護;在利用方面,私法供給底線規則,而制度細節尤其基因技術規制,可容讓于公法。同時,為自律留下制度空間,細節性、體系性的技術標準、行為規則,可由基因技術研發團體、所屬行業在法律框架下自給,發揮行業自律作用,最終實現他律與自律統合。
(三)后法典時期“基因權”法律保護進路
基因權法律保護分為公法進路與私法進路,前者注重規制基因技術,間接保護基因權利;后者直接明定基因權利。我國現行法側重以技術規制為中心的公法模式,存在立法層級低、倫理準則薄弱、權利視角缺失、行政管理中心、調整效果不佳等弊端。基因技術涉及多元主體甚至未來世代,多重利益交錯,多樣風險疊加。此種挑戰已超越單一法律部門、特定法律制度,需要全面系統的制度構建。為此,在法律層面,公私法應協力,既要供給基因權利制度,也要國家監管,公法干預。
在私法層面,長遠來看,適宜采取《民法典》規定一般條款、特別法構建制度細節的協同立法體例。《民法典》體系龐大,具有抽象性、權威性,不宜隨時修訂。那些指涉重大價值、規范形態穩定的條文適宜納入民法典。特別法主要調整鮮活、生動、變化快的事務領域。“基因權”一般條款旨在確認自然人控制支配其基因的物質型人格權,以法典宣示其重要性。如上述,“基因權”在短期內于法典中難以有名化,可通過法律解釋,典外構造“基因權”。本文引述有關條文論證“基因權”作為物質型人格權時即已開展此類活動。
在具體領域或特定基因技術條件下“基因權”的享有、行使等需要特別立法,系統規定“基因權”的基本結構、得喪變更等運行規則、保護制度。建議以《基因權利法》規定以物態基因為客體的“基因權”以及以基因信息為客體的基因隱私權或信息權等基因權利體系,明確各種基因權利要素、行使、運行、救濟等基本規則。同時,單立《基因技術法》,與《基因權利法》并列,協同調整基因科研、醫療等技術事務。或者,融合基因權利與基因技術,構造公私法混合屬性的《基因權利保護法》或《基因法》。
還應開展框架式、實驗立法。基因技術的快速發展及潛在風險,令制度構造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對此,必須深入了解新技術,全面掌握新型社會關系,做好立法預測。鑒于立法者能力有限,在未成熟領域,應采取指引性框架式立法,以簡約規則化約復雜世界,為社會進步保留彈性制度空間,為技術和產業發展提供導引。框架式立法時,應實行實驗立法。“實驗法”應設定期限并伴有評估措施,用于風險治理。①參見王貴松:《風險社會與作為學習過程的法——讀貝克的〈風險社會〉》,《交大法學》2013年第4期,第175頁。可制定臨時性、開放性條款,根據新技術、新領域具體狀況,隨時檢討立法成效,針對存在的問題,適時調整修訂法律,進行動態規制。尤其基因特別立法時,面對技術、倫理、安全等諸多風險,在特定領域、小范圍內開展實驗立法最為妥當,可把風險后果降至最低,并最大限度地保護各方權益。
結語
基因科技令人類對自身的認知進入分子水平,圍繞基因的醫學、科研、商業利用等活動已蔚為大觀。基因是個人的生物身份證,關乎人的尊嚴。基因之上存在獨立的人格利益,已非傳統民法物權、物質型人格權所能涵蓋。創設“基因權”有利于加強人的尊嚴保護,維護倫理道德,平衡技術變革、產業發展與社會安全之間的關系,最終深度推動社會文明進步。而在后法典時代,在《民法典》現有規范格局下,應發揮法律解釋作用,構造“基因權”;同時,開展特別立法,以特別法系統規定“基因權”,建構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此一過程應注意私法與公法協同、倫理與法律共治、自律與他律統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