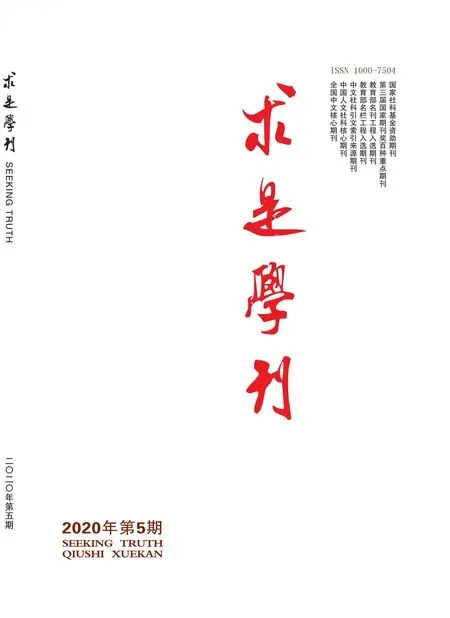禮樂視域下王安石性情論重構研究
吳遠華,王 偉
錢穆曾言:“荊公思想,對當時有大貢獻者,舉要言之,凡兩項。一為王霸論,二為性情論。”①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5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6頁。性情論是王安石平生特所究心的話題,其寫作了多篇探討性情的文章,如《性論》《性情》《性說》《揚孟》《原性》等。這些文章創作于不同時期,且前后持論頗不一致,從中大致可以歸納出王安石的性善說,性為情本、性有善有惡,性無善惡、善惡由情三種主張。既有研究普遍認為,王安石的性情論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演變,至于其學說演進的思想歷程則是學界頗多爭議的話題。②賀麟:《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第99—104 頁;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36—259頁;胡金旺:《王安石人性論的發展階段及其意義》,《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第22—28頁;張建民:《王安石人性論的發展演變及其意義》,《孔子研究》2013 年第2 期,第57—65 頁;張培高、詹石窗:《論王安石對〈中庸〉的詮釋——兼論與二程詮釋的異同》,《哲學研究》2016年第2期,第54—60頁。進一步看,王安石數易其說的意圖及其思想推進的內在邏輯仍有待闡釋。劉豐曾撰文揭示王安石的心性論與其禮樂論之間的關聯。①劉豐:《王安石的禮樂論與心性論》,《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2期,第93—100頁。本文進一步提出,王安石性情論的問題意識、深層意涵與思想歷程,都可以通過對其禮樂論的分析得到解釋。從禮樂論的角度出發,可以對王安石的性情論展開更深入的重構,亦將重新回答荊公思想如何貢獻于當時。
一、《禮論》《性情》《揚孟》《性說》與王安石性論的轉向
王安石對性論問題的關注早自慶歷年間(1041—1048),他在這一時期寫作的《淮南雜說》被視為是對北宋道德性命之學興起具有開創意義的作品。《淮南雜說》今佚,宋人語云,“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云”,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后志卷二,以同書卷四“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下引文字校正,淳祐九年(1249)衢州刊行本,第594頁。“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③馬永卿:《元城語錄解》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7冊,第263頁。可以推測,《淮南雜說》中的性命學說當與孟子相近。除《淮南雜說》外,王安石論性一主孟子者,又有《性論》一文。其與《淮南雜說》當為同一時期的作品,代表了王安石早期的性善主張。《性論》云: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于《論語》。子思、孟軻之說,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學者,見一圣二賢性善之說,終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于《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與?噫,以一圣二賢之心而求之,則性歸于善而已矣。④王安石:《性論》,《圣宋文選》卷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476頁。
《性論》體現了王安石性善說中的尊孟與道統思想。如所熟知,王安石好《孟子》,《孟子》在宋代升列經部,正是通過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主持下的科舉改制實現的。《性論》對孟子性論的闡發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孔子、子思、孟子的相關表述加以統合;二是對漢唐性論作出回應。王安石的思路是區分“才”“性”概念,以“五常”論性,作為人的本質之性,將現實經驗中的人性差異歸于“才”之美惡。《性論》指出,荀子、揚雄、韓愈等人的謬誤在于混淆了才性之別:“性者,五常之謂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其才品,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是也。”“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揚雄、韓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⑤王安石:《性論》,《圣宋文選》卷十,第476頁。要之,王安石早期的性善說,是其尊孟與道統思想的組成部分。
王安石性論的第一次變化約始于嘉祐、治平年間(1056—1067),他先后在多篇文章中表達了自己的性論主張,尤以《禮論》《性情》《揚孟》《性說》最為集中。這四篇文字闡發的性論思想一致、彼此勾連。王安石不再以“五常”論人的本質之性,而是以生之自然論性,認為性有善有惡。如何理解這一變化?由于四篇文章寫作的具體時間及其先后次序無法精確推定,以下對王安石寫作意圖與問題意識的闡釋,將主要基于文本分析和理論重構的方法,其次再結合歷史語境進行討論。
首先分析《禮論》《性情》兩篇。《禮論》并不專論性,它主要是一篇論禮的文字,篇首旗幟鮮明地反駁荀子禮論,云: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圣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于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圣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圣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⑥王安石:《禮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98頁。王安石認為,圣人制禮,因應人性之善惡,既有節制欲望的一面,也有成就其善性的一面,非如荀子所說,僅為制欲治惡而已。且王安石在《禮論》后文中提出:“夫民之于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于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①王安石:《禮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第1198頁。表明百姓施行禮節并非個人主觀意愿,而是出于恐被高地位之人厭惡、進而用刑罰懲戒自己的擔憂。因此,王安石認為,荀子所提倡的用法度節奏脅制百姓遵守禮節,只能換得百姓表面的順從和遵守,是荀子禮論的過失。嚴格說來,王安石對荀子禮論的理解并不準確。事實上,荀子禮論亦有養人之善情的一面。《荀子·禮論》曰:“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②荀子:《荀子·禮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7頁。荀子以人的自然情性為禮的基礎,并不否定人情中的善端,如論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荀子指出,父母之愛、喪親之痛,是世間最自然的情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故有血氣之屬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親也,至死無窮”。③荀子:《荀子·禮論》,第227頁。三年之喪以喪親之痛為基礎。親死而遂忘,固為圣人所禁,而君子遂之至于無窮,亦不合乎中道,“故先王圣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④荀子:《荀子·禮論》,第227頁。荀子肯定人情中的善端,但并不視之為“善”,他稱之為善的,是與自然情性相對的圣人制作。⑤學界在荀子的人性論上存在爭議,本文認同唐君毅的觀點,他指出:“荀子所以言性之惡,乃實唯由與人之偽相對較,或與人之慮積能習,勉于禮義之事相對較,而后反照出。故離此性偽二者所結成之對較反照關系,而單言性,亦即無性惡之可說。”“此中性偽所結成之對較反照關系,實即在人之慮積能習所依之禮義文理之理想,與此理想所欲轉化之現實間之一對較反照關系。唯人愈有理想,乃愈欲轉化現實,愈見現實之惰性之強,而若愈與理想成對較相對反;人遂愈本其理想,以判斷此未轉化之現實,為不合理想中之善,為不善而惡者。故荀子之性惡論,不能離其道德文化上之理想主義而了解。”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唐君毅全集》第17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91頁。漢唐間流行的人性論,雖不同于荀子,但禮樂教化的基本理念則大體本之。漢儒論性善情惡,強調善、惡皆為人性的本質構成,以此作為禮樂教化的人性論根據,“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⑥董仲舒:《春秋繁露·實性》,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7頁。禮樂與自然情性的關系,不僅有治惡的一面,還包括基于人性善端的善之養成。在這一點上,《禮論》篇末云:“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于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⑦王安石:《禮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第1198頁。反映了王安石對荀子“圣人化性而起偽”論述的批判和反對,認為禮乃始于天性而成于人為。王安石理解的“荀子”與上述分析之間存在的歧義,姑且另當別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反對的是一種“禮唯制欲”的思想。有跡象表明,禮唯制欲論是北宋前期有影響的一種學說。如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便是持這一主張的代表性學者。胡瑗曾著《原禮》一篇,全文今佚,主要觀點在李覯的文集中有所引述,李覯《與胡先生書》載:
竊觀《原禮篇》曰:“民之于禮也,如獸之于囿也,禽之于紲也,魚之于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強而制爾。民之于侈縱奔放也,如獸之于山藪也,禽之于飛翔也,魚之于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云云。”⑧李覯:《與胡先生書》,《李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17頁。
由李覯的轉述可知,胡瑗《原禮篇》認為,禮是約束百姓自然情感、欲望的治惡之制。李覯進一步批判了胡瑗禮論的情惡論背景,李覯言:
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悌,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后患,是謂獸之于山藪,鳥之于飛翔,魚之于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為罪辜,為離散,窮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于囿,鳥之于紲,魚之于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①李覯:《與胡先生書》,《李覯集》,第317頁。
胡瑗禮論以“情惡”為人性論前提,視禮為情欲的對治與約束。如前所述,由漢以來,主流禮論包括通過禮樂教化實現欲的約束與善之養成,胡瑗禮論之所以會導向情惡論的單純對治,是緣于中唐以來儒家在性情學說上的重要變化。李翱《復性書》曾云:“人之所以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②李翱:《復性書》,《李文公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頁。李翱以性善為人的本質之性,“情者,性之邪也”,惡由情所生,滅情以復性。基于此,李翱認為,禮樂的功能就在于制欲,“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③李翱:《復性書》,《李文公集》卷二,第6頁。
王安石又有《性情》一篇,專為反對性善情惡說而作,他所批判的正是中唐以來的性善情惡論,而非漢人所講的性善情惡,《性情》云: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④王安石:《性情》,《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七,第1218頁。
王安石論性、情關系的方式不是漢人式的以陰陽論性情,而是同于李翱以性為情之本原、情為性之發動。與李翱不同的是,王安石又以“喜、怒、哀、樂、好、惡、欲”等情之自然論性。以生之自然言性,正是《禮論》篇的人性論背景,《禮論》曰:“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又言:“今人生而有嚴父母之心,圣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⑤王安石:《禮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第1198頁。王安石以生之自然言性、以欲言性,性兼包性情二義,有善有惡。他所理解的“性”,在內涵上近于漢儒。換言之,《性情》實質上是站在漢人以生之自然言性的立場上反對中唐以來的性善情惡論,但在理解性情關系的方式上,卻又深受李翱等中唐思想家影響。《性情》又論:
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
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⑥王安石:《性情》,《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七,第1218頁。
王安石認為“喜、怒、哀、樂、好、惡、欲”七者皆人生而有之之性,有善有惡,善惡在所養而已。王安石接受了揚雄的性論,觀點已不同于早年的一尊孟子。為兼顧尊孟立場,王安石調和孟、揚,將性之善惡解釋為后天養成的結果,這便形成了《揚孟》一篇的主題。《揚孟》云: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且以羞惡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也。⑦王安石:《揚孟》,《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四,第1167頁。
王安石指出,孟子之所謂“性”為“正性”,揚雄所言兼性之不正者,要之皆以“習”論孟子、揚雄所言之“性”。王安石對孟子、揚雄的曲解,事實上是其自身主張的反映。王安石又有《性說》一篇,謂“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專以習論性之善惡:
習于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于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于善,一習于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①王安石:《性說》,《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第1235頁。
在王安石看來,人性善惡的實現取決于后天的熏習培養,孔子所謂“上智”“中人”“下愚”言說的皆是后天“習”的結果,而非人的生之之性。生之之性有善有惡,是為“性相近也”,但人的自然之性“非生而不可移”,人性善惡的成就取決于后天的熏習,是為“習相遠也”。
由以上分析可知,《禮論》《性情》《揚孟》《性說》是針對同一論題不同側面的討論,表明王安石的人性學說已較早年的性善論有了根本轉變。王安石早年的性善論帶有強烈的尊孟背景,嘉祐、治平年間,王安石的尊孟立場并沒有改變,他的人性論之所以會發生變化,與他對宋初性善情惡論的批判有關。王安石之所以反對性善情惡,基本的出發點則是為了反對情惡論背景下的禮唯制欲說。
王安石反駁情惡論流衍下的禮樂論,在當時并非孤例。如前引李覯對胡瑗的批判,在李覯看來,禮以治惡的禮治教化論極大地削弱了儒家禮樂教化在善性培養上的正面效用,“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圣君賢師為仇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②李覯:《與胡先生書》,《李覯集》,第317頁。劉敞的性情論同樣需要放在這一語境下解讀。劉敞《論性》曰:“不知性之善者,不知仁義之所出也;不知情之善者,不知禮樂之所出也。”“肅然恭者,禮之本也;歡然樂者,樂之原也。故情者,禮樂也。故圣人以仁義治人性,以禮樂治人情。未有言禮樂而非善者也。”③劉敞:《論性》,《公是集》卷四十六,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550、549—550頁。劉敞認為,人的道德情感構成了禮樂的內在基礎,其性情論同樣針對性善情惡、禮惟治惡的思想而發。以上學說的背后,蘊藏了北宋儒家對作為性情論后果的禮樂教化問題的深切關注。
二、《原性》“性無善惡”說的提出及其意義
《原性》提出的性無善惡、善惡由情說,通常被視為王安石性情論的又一大轉變。關于《原性》的寫作時間,說法不一。胡金旺認為,《原性》是王安石晚年退隱金陵時的作品,依據是《原性》中的性無善惡說與王安石退居金陵時所作《答蔣穎叔書》中的佛教性空思想相似,當為同一時期的作品。④胡金旺:《王安石人性論的發展階段及其意義》,《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第26—27頁。張建民指出,劉敞曾在《公是先生弟子記》中引用《原性》中的觀點,而《公是先生弟子記》為嘉祐、治平年間作品,因此《原性》應為嘉祐、治平年間所作。⑤張建民:《王安石人性論的發展演變及其意義》,《孔子研究》2013年第2期,第61—62頁。從內容看,《原性》以“性”為“五常之太極”,言“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⑥王安石:《原性》,《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第1234頁。此性無善惡說與佛教性空思想實不相同,不宜用《答蔣穎叔書》論證《原性》的寫作時間。劉敞卒于熙寧元年(1068),《原性》之作必不晚于此,張建民之說可從。仍待進一步解釋的是,王安石因何寫作《原性》,并提出性無善惡說?
《原性》約作于嘉祐、治平年間,與《禮論》《性情》《揚孟》《性說》的寫作時間接近,可以算作同一時期的作品。對于善惡產生的原因,王安石在《性情》開篇中闡述:
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動焉。動而當于理則圣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⑦王安石:《性情》,《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七,第1218頁。性情本身無善惡之別,善惡為七情的已發狀態與事物結合后的發生作用,適于理為善,反之為惡。細繹《原性》文本可以發現,《原性》中提出“故有情然后曰善惡形,然則善惡只為情之成名”。其認為善惡因情而后天形成,性本身則不具備善惡之分,這一性無善惡論與《性情》中的善惡產生機制一脈相承。相較前期對性善情惡論的批駁,王安石事實上并未從根本上放棄他的性論主張,性無善無惡說的提出是其本體論立場決定的必然結果,其本質依然是對禮惟制欲說的反對和批判,不過是出于理論考慮,對性情的意涵作了概念上的調整,將二者的邏輯關系進行梳理,是對性論說的重新闡釋和二次構建。《原性》云,“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惡形焉”,性情的本末關系與《性情》是一致的。但在《性情》中,“性”兼包性、情、欲,言“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因此只能謂“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以外在行為論情,這與通常將情作為心理狀態的理解有所不符。對此,《原性》篇對情的概念做了調整,將“喜、怒、哀、樂、好、惡、欲”皆歸于情:“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欲情者乎?喜、怒、愛、惡、欲而善,然后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欲而不善,然后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惡形焉。”①王安石:《原性》,《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第1234頁。
《原性》將《性情》中屬于“性”的內容歸入“情”的范疇,進而又提出了一個作為“情”之本原的“性”的概念,《原性》言:“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又言:“夫太極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情之本體不可以善惡言,從而形成了性無善惡、善惡由情的性情論說。《原性》避免了《性情》論“情”的缺陷,相比《性情》《揚孟》等篇以情說性、以習說性,在概念層次上更為清晰。王安石對性情實質意涵的理解本與漢儒相近,卻必為此論者,乃是受到中唐李翱以來以性作為情之本原這一理解性情關系的方式之影響。《原性》篇結尾道:“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圣人之教,正名而已。’”“或曰”問孟、荀、揚、韓人性學說的提出是否都有特定的教化指向,實即問王安石“性無善惡”說有何教化意義?王安石回答,其學說的意義在于“正名”。之所以會有這樣一段問答,是王安石意識到自身性情論背后本有的教化關切,而《原性》其實是一篇辨析概念、從理論層面對學說加以嚴整、系統化的文字。正因如此,王安石才特于篇末云:“圣人之教,正名而已。”②王安石:《原性》,《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第1234頁。
《原性》以“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此吾所以異于二子……楊子之言為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③王安石:《原性》,《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第1234頁。等論述,明確表明王安石對孟、荀、揚、韓人性學說的質疑和反對。王安石認為,情由性生,性無善惡情卻有善惡之分,情之善惡乃人后天行為所育,其性論強調善性的后天習得,并將其作為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且達到了一定效果。縱觀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發展歷程,古代人性說在經歷了孟子、荀子各自的反復論辯后,“性善”與“性惡”成為后人理論的思想前提,王安石對性的論述與中國古代思想傳統的主流層次保持了一致,但其并不贊同孟子的性善說,也反對荀子的性惡說,選擇了兩者之間的中間道路,始終以“生”言“性”,回歸先秦時期生以言性、性善惡相混的傳統,以“性無善惡”說實現了對儒學人性論傳統的超越,形成了其性論思想主張的內在張力,實現了對戰國時期儒家人性思想觀點的傳承、接續、探索和創新,為傳統性論說注入了新的思想內涵,成為中國傳統性論史上的重要發展環節。
三、禮樂與成圣:《禮樂論》的寫作時間及其思想探微
《禮樂論》是王安石探討禮樂與心性關系的重要文獻,前人對其學說性質的理解存在分歧。張建民將《禮樂論》歸為王安石早期的性善說。①張建民:《王安石人性論的發展演變及其意義》,《孔子研究》2013年第2期,第57—65頁。劉豐的分析指出,《禮樂論》體現了王安石的禮樂論與其道德性命學說之間的密切關聯,其中闡述的修養學說是對儒家傳統修性養生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此外,劉豐還提到南宋黃震對《禮樂論》道家性質的論斷。②劉豐:《王安石的禮樂論與心性論》,《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2期,第96—98頁。如何看待《禮樂論》的學說性質,下面先從分析它的寫作背景與意圖入手。
將《禮樂論》與《禮論》比較,不難看出二者關心的問題存在根本不同。《禮樂論》寫作的核心要旨是論述如何通過禮樂實現養生修性、以至成圣,《禮樂論》云:
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圣人之域。
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于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③王安石:《禮樂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第1199頁。
養生修性本非漢唐傳統禮樂教化的固有職能,“成圣”也非禮樂教化的目標所在。董仲舒言:“善過性,圣人過善。”④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第97頁。“圣人所以能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⑤班固等:《白虎通義》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67冊,第1116頁。禮樂教化以中人之性為基礎,以成王教之善,圣人則是生有異表、通于神明之人,超然于禮法之善。雖然在荀子那里尚有以“成圣”為學禮的終極目標,但自漢以下,圣人不可學、中人循禮法以成教化之善,已漸漸成為中國本土思想界更普遍的看法。⑥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00頁。王安石論證由儒家禮樂可以修養成圣,固然符合荀子學禮成圣的舊義,但直接應對的乃是佛教、道教的挑戰,“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基于儒家禮樂生活的修養成圣理論突破了漢唐傳統禮樂教化的意義與功能,基于此,王安石在《禮樂論》中也提出了新的心性學說。《禮樂論》云: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不能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圣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于性,性生于誠,誠生于心,心生于氣,氣生于形。⑦王安石:《禮樂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第1199頁。
王安石以“心”為知覺思慮能力的總稱,“誠”是知覺能力充分實現的狀態。“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這類超越感官限制的能力,被王安石認作是“性之所固有”,并可以通過感官知覺能力的充分開掘而實現,“神生于性”,借此又可進一步通向神明之境。達至神明的境地也就是《禮樂論》所認為的成圣。神明之性為常人所固有,是常人成圣的內在根據和基礎。關于如何成圣,接下來,王安石提出了養生保形與心性修養相因循的修養方法:
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于保形,充形在于育氣,養氣在于寧心,寧心在于致誠,養誠在于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⑧王安石:《禮樂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第1199頁。
在這一過程中,禮樂的作用不在于“養生保形”,而是“盡性養神”:
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
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
圣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①王安石:《禮樂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第1199頁。
王安石指出,圣人制禮作樂的原理是“體天下之性”,作為禮樂存養對象的“性”同時也是通達神明之境的基礎。禮樂具體如何作用于人性?王安石認為,禮樂的至高境界在于“簡易”:“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禮樂存養人性的具體方式就是通過“簡易”使人“去情卻欲”以修神養性,最終達至神明的境地。《禮樂論》云:
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圣人之域。
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齋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②王安石:《禮樂論》,《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第1199頁。
在此,王安石面對情與欲的態度可謂迥異于他在《禮論》《性情》中的觀點。情不是人性本質性的構成,不是節制、存養的對象,而是性的障蔽,是摒除的對象。不難看出,《禮樂論》對禮樂與修性關系的論說與李翱非常接近,《復性書》嘗言:“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③李翱:《復性書》,《李文公集》卷二,第6頁。如前所論,情惡論及其影響下的禮唯制欲說恰恰是《禮論》《性情》等篇極力反對的主張,《禮樂論》很可能在創作時間上要早于《禮論》《性情》等篇。在《禮樂論》中,王安石希望建立儒家禮樂本位的修養成圣學說,但其理論卻并未脫離李翱等中唐思想家之軌轍。正如《復性書》深厚的道教背景,④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第290頁。《禮樂論》當中的心性概念以及寧心養氣、養生保形、修神致明等相互因循的思想都帶有道教痕跡。情惡論下的禮唯制欲說,其思想后果是削弱了儒家禮樂在善性培養上的積極意義,這有悖于王安石以《禮樂論》申張儒家禮樂價值的初衷。正因如此,嘉祐、治平年間,王安石轉而開始批判情惡論及其流行下的禮唯制欲說,這一轉變又使王安石的禮論不再能夠回答他早年所關切的禮樂與成圣的關系問題。王安石的思想困境經由張載的“知禮成性”學說才得以真正化解。
張載通過“知禮成性”這一提法將知、禮與天地之成性相貫通,認為知、禮二者通過德性和功業的成就推動生命存在及其價值的全面實現。其中“知”被張載分為通過耳目之官接于物而生的經驗知識即見聞之知與通過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的方式獲得的德性所知。張載認為德性所知是以見聞之知為基礎,而其更強調德性所知:“聞見不足以盡物,然又須要它。耳目不得則是木石,要它,便合得內外之道。”⑤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207—219頁。在張載的“知禮成性”這一學說中,相比禮是儒家教化之本、修身之要來說,他更偏向于“禮制”。他提出禮是天秩天序的體現,是本出于性的體現,除此之外,他還特別重視在現實的躬行踐履中變化氣質,不斷完善自我。張載的禮學,結合強調“德性之知”,為王安石的“性情論”以及當時的思想困境找到突破口,禮制不再僅僅是出自于本,而更是需要在天性中不斷教化與修養得取。
結語
王安石的禮樂論可以大致區分為前后兩期,經歷了從“禮惟制欲”到“制欲養善”的轉變。王安石性情學說的調整與其禮樂論的轉向密不可分,究其實質,同樣應區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即從性善情惡向性情有善有惡的變化。王安石前期的禮樂論大體接續了中唐李翱以來情惡論背景下的禮樂思想,奠基于情惡論的禮惟制欲說,其思想后果是消解了儒家禮樂教化在善性培養上的積極效用。嘉祐、治平年間,王安石在禮樂論與性情論上的轉向,意圖重新捍衛儒家傳統禮樂教化的固有價值,卻又不再能夠回答禮樂與成圣的關系問題。張載知禮成性學說的出現為這一困境的解決找到了出口,禮樂教化與修養成圣之學的成功圓融,構成了理解理學興起不可或缺的一環。王安石在禮樂論與性情論上的不懈探索,既根源于古代儒家性情論與教化思想的密切關聯,又始終貫穿著王安石對于時代問題的關切與回應。他的性情論為理解北宋前期儒家思想進程提供了重要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