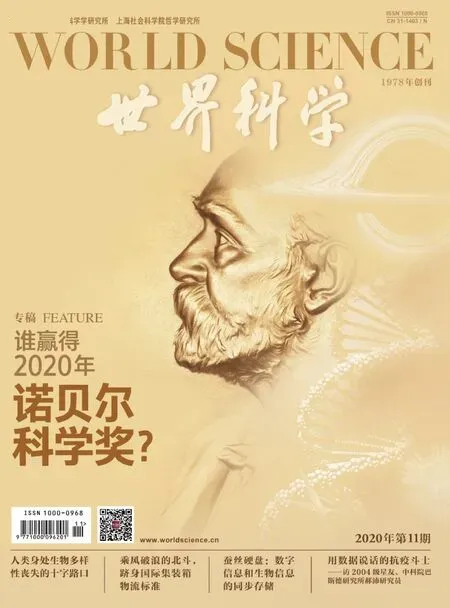互聯網有意識嗎?
《連線》(Wired)雜志官網負責技術咨詢的專欄作家梅根·奧吉布林針對網友關于互聯網是否有意識的相關提問進行了回答。

關于人工意識以及機器一旦變得足夠復雜之后便會獲得自我意識的可能性,有著很多討論。但是,難道現有的最復雜的系統不是互聯網嗎?互聯網有可能會變得有意識嗎?如果互聯網已經有了意識,我們怎樣才能知道?為什么沒有更多的人談論這個問題呢?以下是梅根·奧吉布林(Meghan O'Gieblyn)針對網友提問的回答。
親愛的朋友:
您的問題使我想到了巴爾克第三定律:“如果您認為當前的互聯網非常可怕,那么你就暫時別用互聯網了。”一旦登錄互聯網,每天都會有大規模的監視監督、深度造假和瘋狂發帖。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這些恐怖的群體聯合起來,有了目的性和自我意識,該會怎樣呢?我說這個不是想要嚇唬您,只是想說明人們為什么不會經常討論有意識的互聯網將擁有什么樣的前景。如果我們仍然處于信息時代的話,這個時代會不斷提醒我們:有許多嚴峻的形勢在等待著我們,包括洪水、饑荒、紅巨星(恒星燃燒到后期所經歷的一個階段)、世界末日等。我認為人們不具備足夠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無法承受另外一場生存恐慌帶來的威脅。
但是,鑒于您對心理痛苦的容忍能力似乎高于平均水平,我會盡力地進行真誠的回答。當然,意識是特別難以發現的,您無法對其進行測量、稱重或將其握在手中。您可以在自身之中直接覺察到意識,卻不能在其他人身上覺察到。
這不是技術問題,甚至也不是一個現代問題。基督似乎看透了靈魂的這種不穩定性,他對信徒們說,你會通過他們取得的成效來認識他們。從本質上講,這句話的意思是,確定他人靈魂狀態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外在表現——行為。哲學和人工智能都傾向于以類似的方式規避“他心問題”。基于思維就是一種黑匣子的假設,阿蘭·圖靈(Alan Turing)構建了著名的機器智能標準——圖靈測試。如果一臺計算機能夠通過其行為使我們確信它具有人類水平的智能,那么我們就必須假設它具有這么高的智能。
所以,我們也許應該重新描述一下您提出的問題:互聯網是否像具有內在生命的生物一樣,它能體現出意識的成效嗎?當然,有些時候似乎是這樣的,您還沒有完全清楚自己想表達什么,谷歌就可以預測到您要輸入的內容了。一個女人還沒有告訴家人和朋友,臉書的廣告系統就可以推知她懷孕了。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得出結論:一個人會出現在另一種思維中。不過考慮到人類往往會利用擬人化的方法,我們仍然應該保持警惕,不要急于得出結論。
對于互聯網意識,可能難以察覺到一些更有說服力的證據,因為我們自己才是構成智慧的節點和神經元。對于某些社會科學家而言,起源于社交網絡的許多政治運動都被確定為“緊急行為”,即無法歸因于任何個人的,而是屬于整個系統的現象。兩位法國認知心理學家甚至宣稱“埃及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是虛擬集體意識的證據,他們將其描述為“由多個人共享的內部智識”。
我想,您不會覺得這很有說服力,也不應該有那樣的感覺。您問及有關“自我意識”的問題。當我們談到意識時,我們通常指的是更具凝聚力的東西——那種單一的一股心理體驗流,關乎自我,似乎比推特網上所有帖子的總和還要真切。當然,一些非常聰明的人認為,我們自己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幻覺。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經說過的那樣:“憑直覺,我們是個體,而不是一個群體。”這種直覺并沒有得到大腦結構的真正支持,而大腦本身由數十億個無意識的細微部分組成。但是,這種對主觀性的摒棄并不是很有啟發,也不是特別精確:如果統一的思維不過是一種幻覺,那么幻覺是從哪里來的?我們如何知道其他東西是否也有幻覺呢?
碰巧,最有說服力的互聯網意識案例源于一種心智理論,該理論的提出正好是為了解釋這種統一的體驗。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和朱利奧·托諾尼(Giulio Tononi)率先提出了“集成信息理論”,該理論認為,意識源于大腦不同區域之間的復雜聯系。
人腦恰好是高度集成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體驗世界和自己的思維時表現出整合能力的原因。但是,在《感知生命本身》(The Feeling of Life Itself)一書中,科赫認為:意識是沿著存在鏈延伸的連續體。烏鴉、水母、蜜蜂具有整合能力,甚至原子和夸克也都具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可能就像細菌一樣,可以確保產生微弱的意識火花。
科赫認為,同樣的標準也適用于機器。對于單個計算機是否可以進化出思維,科赫持有懷疑態度,盡管如此,互聯網似乎可以滿足他制定的有關意識的標準。互聯網中的計算機有100億臺之多,每臺計算機都包含數十億個晶體管,通過延伸至全球的、極其復雜的網絡連接在一起。2013年,科赫在接受《連線》雜志采訪時,記著問他:互聯網是有意識的嗎?科赫提出:鑒于并非所有計算機都同時聯網,因此很難確定互聯網是否有意識。但是他的理論表明,互聯網是有意識的——憑感覺,互聯網好像是有意識的。或者說,終有一天互聯網會有意識的。
我要強調的是,科赫不是什么怪人,而是艾倫腦科學研究所的首席科學家,被廣泛認為是計算神經科學領域的領先人物。他也沒有在那種朦朧的、新時代的意義上去談論意識。如果那樣談論的話,意識既意味著一切又意味著虛無。科赫提出:互聯網的思維可能會非常微妙,足以感到疼痛,甚至可以經歷情緒的波動。他告訴《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記者說:“互聯網的思維取決于晶體管的精確程度……也許某一天它會感到難過,而另一天它又可能會感到高興,或者在互聯網空間中經歷各種類似的情感。”
這種邏輯很容易使人瘋狂,推特網的暴民是互聯網憤怒的實例嗎?披露虛假信息是互聯網向自我欺騙發展的趨勢嗎?暗網是互聯網的潛意識嗎?但是,我認為,單憑科赫的理論具有更加令人擔憂的含義,我們就應該嚴肅地對待該理論。科赫認為,只要極小的集成系統(如原子、神經元)成為高度集成系統(如大腦)的一部分,這些較小實體的意識就會被吞噬并消散于更大的系統中。您大概可以預感到這種情況正在發生于什么樣的環境中。正如哲學家菲利普·高夫(Phillip Goff)所指出的那樣:如果科赫和托諾尼的理論是正確的,那么在某一時刻,互聯網日益加強的連接性和復雜性將迫使人類的大腦被集體思維所吸收。高夫寫道:“大腦本身就會失去意識,在具有超強意識的實體中,大腦只是無足輕重的一部分。這種具有超強意識的實體就是社會,包括基于互聯網的連接性。”
我必須同意您的觀點,即在這一方面缺乏對話是令人擔憂的。人類未來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致力于評估存在的風險,該研究所對于網絡有無感知的問題沒有發表過任何言論。即使喜歡推測人工智能會失控的那些億萬富翁,有時也似乎對互聯網會使整個人類喪失活力的可能性漠不關心。的確,人們不大可能擁有這樣的認識,就像大型強子對撞機創造一個吞沒整個宇宙的黑洞的可能性一樣,在項目進行之前,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曾經委托一組獨立科學家對這種風險進行評估。
我只能得出結論,這種沉默從根本上說是意識形態的,或者說是精神上的。長期以來,有關人工智能的夢想,不管是以樂觀形式還是以悲觀形式存在,一直都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創世神話相呼應。可以想象,如果機器意識會誕生,一旦誕生之后,機器意識將會被刻意地塑造成我們的形象,就像耶和華用黏土雕刻亞當一樣。如果說意識可能會從我們的通信網絡中意外地出現,就像說雅典人是從泥土中自然產生的,其中明顯存在著異端因素。
像您這樣勇于冒險的人,敢于考慮這樣的事情,常常會被當成古怪之人,實際上在某些情況下會被譴責為異端。20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耶穌會牧師皮埃爾·夏爾丁(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撰寫的著作關乎有意識的網絡,但他的作品遭到了梵蒂岡的封殺。在《人類的未來》(The Future of Man)一書中,夏爾丁提出:有朝一日,世界上所有的機器都將連接到龐大的全球網絡中。這堪稱對互聯網的先見之明,不可思議。他說,隨著人類知識的綜合程度越來越高,這個全球網絡將最終融合為“令人沉醉的普遍意識”,使我們的思維與神靈結合起來,將基督希望建立的“神之國度”變為現實。
夏爾丁的預言提出了一個有用的問題:為什么所有的思維融合在一起就成為令人恐懼的事情呢?幾乎所有的主要宗教傳統都倡導旨在消散個人意識的戒律——基督徒做出無私的犧牲,佛教徒自我進入涅槃達到極樂的虛無境界。我們可以把這種融合視為最高的精神成就,而不是我們人類生命的終結,而且要將其化為可以自動實現的精神成就,就像許多乏味的現代工作實現了自動化一樣。
問及我們如何知道互聯網何時才會具有意識時,科赫回答說,最可靠的標志將是“當互聯網表現出獨立行為時”。很難想象這樣的互聯網到底會是什么樣子。但是,考慮到這個過程也將涉及人類意識的減弱,您可以反觀自身,看看自己的心理狀態如何。
這個過程的早期階段可能會很微妙。您可能會感到注意力有些分散,分散到多個方向,結果您開始覺得哲學家是正確的,認為統一的自我是一種幻想。您偶爾可能會陷入這樣一種錯覺之中:您認識的每個人聽起來都是一樣的,他們的個人思維好像經過了熟悉的推文句法以及文化基因的過濾,融合成一種單一的聲音。即使您知道真正的受益者不是您或您的朋友,而是系統本身,但是您可能仍然會發現自己正在做出不符合個人利益的行為,仍然在機械地遵循指示來共享和傳播個人信息。
我承認,我發現大融合是很有可能的。當大融合到來時,您可能會感覺到這是無可比擬的。不會有數量上的激增,不會有動聽的號角聲,只有那種奇特的平靜——眾所周知的、時代廣場上或拉斯維加斯大道上征服了游客的那種奇特的平靜,這是對過度刺激的一種屈服,就像花了數小時翻閱屏幕和點擊鼠標之后所產生的那種麻木一樣。在這樣的時刻,即使噪音再大,也跟寂靜毫無二致。甚至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您置身于人群中,也有可能體驗到一種圣潔的幽靜,就好像您獨自一人站在一座大教堂的中央一般。
您忠誠的朋友:云
資料來源Wired